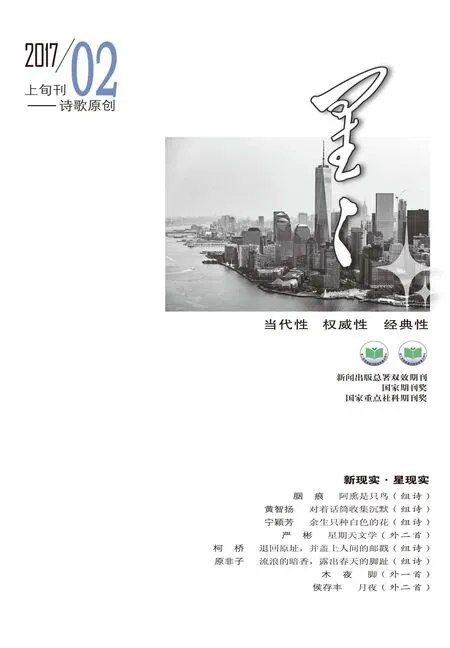康巴行,或讀阿來《瞻對》有記(組詩)
凸 凹
康巴行,或讀阿來《瞻對》有記(組詩)
凸 凹
瞻對,或鐵疙瘩
一柄劍化為一塊鐵疙瘩
元代皇帝很高興。一塊鐵疙瘩化為一脈豪酋,進而化為一個縣名
清代皇帝不高興,民國總統不高興。為了把鐵疙瘩化回去化回到原初的宮殿,化回到權杖的手心
雪化了,冰化了,路化了,人化了
縣名沒化,鐵疙瘩沒化。一個化字
讓一個國家的人馬不成體統
顏面丟了三番五次。一個化字
拿了多少將軍頭,成了多少英雄事
當瞻對一詞化回為瞻對本沖,又化回為上意,再化回為鐵疙瘩
最后化回為一柄寶劍,一位叫喜饒降澤的高人,一切就真的化了
化不去的,只能是心里的鐵器
可即使把鐵器化為齏粉,雪花樣灑向天空,它也會紛紛揚揚落下
千里萬里落在瞻對的土地上。覆蓋的雪花
無不是細細密密的鐵的含意
火,或致布魯曼官寨遺址
一場火
燃燒十七年
布魯曼和他的人民
有了根據地。十七年,不是時間
十七年,是一塊地方
是一處讓皇帝和土司上邊頭疼下邊便秘的苦穴
是一枚讓瞻對高人一等的印章
是的,這個遺址
就是一枚戳了鮮紅火焰的印章,一枚
管著康巴三千里江山——
連天上動物的飛徑也管的印章
覆蓋陰火的
是時間之火:廢墟、殘墻、碎瓦、青草、
牛羊,還有一群黑得那么干凈的小學生
正在時間的陽火中舞蹈、唱藏歌
為了平衡,來了又走永遠走不完的雅礱江
帶走了多余的火
那天是上午,太陽流著夏天最后的火
把我連同導引我們來的阿來
交給了冬天最先的火。這二火夾峙歸一的
輪轉,這火的契約,讓我歡喜、憂傷、無言
真真切切如履薄冰地觸到了
獨眼龍的火:布魯曼的火
神的部落
云罩著。還有什么可恐懼的呢
去往家園、遠方的途中
飛鷹作為云的語言
點點滴滴,傳遞出生命的骨響
云的力量多么廣大、先驗啊
為了這一路的重
竟收羅了全世界的顏色
和輕
神罩著的部落一直在前行
一直在以靜止的定力作偉大的前行
好些船只已牽涉大海
好些船只還揚帆雪山
凸凹詩觀
凡的人說出了神的話,就是詩人。凡的人說出的神的話,就是詩歌。沒說清楚?這就對了,詩歌都能說清楚,我還寫詩干嘛!不講道理?又說對了,詩歌就是不講道理,詩歌只講詩理。不跟我說了?好,那就讓我的詩跟你說。
詩歌務虛,小說向內,戲劇從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