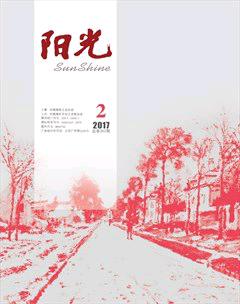《遠(yuǎn)去的背影》閱讀札記
《遠(yuǎn)去的背影》是一部近十四萬(wàn)字的非虛構(gòu)文學(xué)作品。欣聲用“我和我的家庭簡(jiǎn)史”為《遠(yuǎn)去的背影》一書(shū)做了副標(biāo)題,已經(jīng)詮釋了該書(shū)的性質(zhì)。
“非虛構(gòu)寫(xiě)作”是近年來(lái)文學(xué)界的一個(gè)熱詞。特別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予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之后,隨著她的系列“非虛構(gòu)文學(xué)”著作在國(guó)內(nèi)出版,非虛構(gòu)寫(xiě)作為更多的人所關(guān)注和喜歡,也成為傳統(tǒng)的紀(jì)實(shí)文學(xué)的新“標(biāo)簽”,抑或?yàn)樵L(fēng)靡一時(shí)的“新寫(xiě)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華麗轉(zhuǎn)身”。
欣聲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各種“主義”向來(lái)不感興趣,《遠(yuǎn)去的背影》也絕非跟風(fēng)之作。這部以家族變遷為主要線索的非虛構(gòu)作品,通過(guò)“我和我的家庭”幾代人的經(jīng)歷,從“我”本人的視角,自身的親歷、親聞與感知,映照出百年以來(lái)的時(shí)代嬗變以及大時(shí)代中小人物的悲歡,歷史潮流中的裹挾與掙扎,社會(huì)風(fēng)云中的堅(jiān)守和無(wú)奈。欣聲在《前言》中寫(xiě)道:“我覺(jué)得,即使我們只是一個(g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有責(zé)任將我們的過(guò)去記錄下來(lái),讓兒孫們知道他(她)們的前輩曾經(jīng)的生活。盡管他們的前人沒(méi)有創(chuàng)造過(guò)什么值得驕傲和夸耀的歷史,但是在漫長(zhǎng)的人生道路上,他們有悲傷、有痛苦、有快樂(lè)、有追求;他們?cè)僬鄄粨献詮?qiáng)不息;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始終對(duì)未來(lái)抱有信心和期待……讓后代從前輩人經(jīng)歷過(guò)的坎坷和曲折中,深刻地體會(huì)他們生命的堅(jiān)韌和執(zhí)著,傳承他們擁抱生活的精神和情懷。”這段話開(kāi)宗明義,概括了本書(shū)的主旨和要義,無(wú)需再作更多解讀。竊以為,這部書(shū)除了為其后代述史傳家而外,作為非虛構(gòu)作品還為我們這些被“寫(xiě)什么”和“怎么寫(xiě)”長(zhǎng)期困擾的寫(xiě)作者們提供了一個(gè)很好的范例。
關(guān)于寫(xiě)什么的問(wèn)題,我理解非虛構(gòu)寫(xiě)作的要義其實(shí)就是書(shū)寫(xiě)普通人的歷史。每個(gè)人都應(yīng)該擁有記憶歷史的權(quán)利。我們每一個(gè)人的經(jīng)歷都是歷史,每個(gè)人的苦難都有歷史的重量,每個(gè)人的歷史都不應(yīng)該遺忘。普通人的苦難進(jìn)入歷史才有價(jià)值,才是社會(huì)共同的財(cái)富,成為社會(huì)記憶才具有歷史的力量。
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非虛構(gòu)寫(xiě)作是真正關(guān)于“人”的歷史。經(jīng)典教科書(shū)上有一句耳熟能詳?shù)脑挘瑲v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可是當(dāng)我們翻開(kāi)歷朝歷代的“正史”,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人民的個(gè)體面目我們并看不到,更遑論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lè)和心路歷程。梁?jiǎn)⒊f(shuō)“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可見(jiàn)我們的封建歷史可謂“帝王史”;魯迅先生說(shuō):“我們自古以來(lái),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qǐng)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guó)的脊梁。”從這個(gè)角度看,我們的歷史也是“精英史”;或者從某一側(cè)重的方面去讀,也可以是政治史,軍事史,經(jīng)濟(jì)史……唯獨(dú)不是“人”的歷史。因?yàn)樵谒^大的歷史記述中,在主流的歷史話語(yǔ)里,“人”往往是看不見(jiàn)的,尤其是普通人在這樣一個(gè)主流歷史狀態(tài)中是完全被視而不見(jiàn)的,他們可能會(huì)以數(shù)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說(shuō)歷史記載秦始皇動(dòng)用百萬(wàn)勞力修筑萬(wàn)里長(zhǎng)城,每一位參加修筑長(zhǎng)城的人從相貌到內(nèi)心肯定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生活軌跡,各有各的悲歡離合,但他們只是抽象的數(shù)字。即使在近代史上,我們經(jīng)歷了那么多的內(nèi)外戰(zhàn)爭(zhēng)、歷史變革、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但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態(tài)也鮮有記述。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都是由一個(gè)個(gè)具體、活生生的人構(gòu)成的,而在記述歷史上某一社會(huì)階段的狀況時(shí),普通人則濃縮為數(shù)字,他們沒(méi)有面目,沒(méi)有形象,也沒(méi)有聲音。
阿列克謝耶維奇曾坦言,在她的筆下,除了關(guān)注社會(huì)日常生活,感興趣的是那些平凡的小人物,那些因苦難而偉大的人。“在我的書(shū)中,這些人述說(shuō)著他們自己的小歷史,使得大歷史在無(wú)形中也得以窺見(jiàn)。”這就是非虛構(gòu)寫(xiě)作對(duì)歷史的價(jià)值,他使歷史更加鮮活生動(dòng),使個(gè)體的記憶成為集體記憶乃至社會(huì)記憶,通過(guò)書(shū)寫(xiě)小人物的命運(yùn)折射出大時(shí)代的隱喻。
在《遠(yuǎn)去的背影》中,我們從“我”對(duì)“爺爺”一生碎片化的敘述中,可以管窺那場(chǎng)發(fā)生在上個(gè)世紀(jì)中葉的“土改運(yùn)動(dòng)”對(duì)遼西地區(qū)農(nóng)村的深刻影響乃至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歷史的根本改變。“爺爺”是土地肥沃的老哈河沖擊平原上“小孤山”村聞名的地主,是那個(gè)“高大的門樓,寬闊的院墻和四角土炮臺(tái)”的“大院兒”的少東家。“爺爺”曾經(jīng)“嗜賭和吸食鴉片”幾近癡迷,也“不怎么會(huì)經(jīng)營(yíng)土地和生意”,靠祖上的家業(yè)過(guò)著優(yōu)哉游哉的日子,當(dāng)“土改時(shí),爺爺攜全家從這個(gè)大院兒被掃地出門”,雖然“一夜之間就成了窮光蛋”,但他“從此戒掉了吸食鴉片和賭博的惡習(xí)”,“成就了他一個(gè)新的生命”。這一“千年未有之變局”改變的不僅是社會(huì)制度、社會(huì)形態(tài),而是對(duì)社會(huì)成員的重塑。解放后“爺爺”不僅成了一個(gè)自食其力的人,而且掌握?qǐng)@藝技術(shù),成了“老莊稼把式”。雖然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但勤勉勞作從不消沉,打魚(yú)捉兔、說(shuō)書(shū)講古,使貧困的生活充滿了情趣。“爺爺”經(jīng)歷滿清、民國(guó)、滿洲國(guó)和新中國(guó),他對(duì)跌宕起伏的人生和波詭云譎社會(huì)的認(rèn)識(shí),窮其一生也沒(méi)有能夠上升到“階級(jí)學(xué)說(shuō)”去領(lǐng)悟,卻歸結(jié)為命運(yùn)的擺布,而恰恰頭腦里故有的這種宿命論的“處世哲學(xué)”,使“爺爺”這一類人從心底消弭了社會(huì)對(duì)立的萌芽。這些非虛構(gòu)的情節(jié)是我們?cè)谌魏螝v史教科書(shū)中都難以看到的。
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其實(shí),歷史就是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無(wú)休止的對(duì)話,換句話說(shuō),歷史就是一個(gè)不斷重新構(gòu)建的過(guò)程。當(dāng)我們真正理解了這句話的含義后,反而使我們對(duì)歷史話語(yǔ)有了一種莫名的疏離之感。非虛構(gòu)作品關(guān)注的是普通人的歷史,把普通人個(gè)體的記憶凝結(jié)成集體記憶,使之成為社會(huì)記憶的元素,這種記述才有價(jià)值。所以,非虛構(gòu)寫(xiě)作不是雞毛蒜皮的人情世故,也不是風(fēng)花雪月的閑情偶寄,不是光宗耀祖的家族傳奇,更不是把屠夫的兇殘化為一笑的東西。而是在記述普通人在特定歷史階段生存狀態(tài)、心路歷程的背后隱含著的東西,如一滴水折射了陽(yáng)光的顏色,一枚河卵石留存了冰川時(shí)代的劃痕。
《遠(yuǎn)去的背影》里的“我”姥爺面對(duì)土改的“血水斗爭(zhēng)”、階級(jí)清算,沒(méi)有聽(tīng)從“二姥爺”對(duì)時(shí)局的判斷,也沒(méi)有像“建平縣的大地主程三東家將土地房產(chǎn)盡數(shù)變賣一空,舉家不知去向”,也不愿“舍去萬(wàn)貫家財(cái)而背井離鄉(xiāng)”,最后因負(fù)隅頑抗,大罵不止,被農(nóng)會(huì)活活打死。“我”姥爺和命運(yùn)的博弈與爺爺截然不同,他認(rèn)為自己是靠勤勞節(jié)儉掙下的家業(yè),沒(méi)有干過(guò)殺人越貨、欺男霸女的事情,甚至對(duì)伙計(jì)也不像其他逃亡地主“外有惡聲”,我何罪之有?他堅(jiān)守著自己的土地和房產(chǎn),也是堅(jiān)守著頭腦里固有的農(nóng)耕社會(huì)千古未變的社會(huì)倫理和善惡之報(bào)的信條。他哪里懂得“革命不是請(qǐng)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huà)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dòng),是一個(gè)階級(jí)推翻一個(gè)階級(jí)的暴烈的行動(dòng)”。 可以猜想,像“我”姥爺這樣的土改清算對(duì)象,他的心路歷程代表了那個(gè)時(shí)代一類人甚至一個(gè)階層的社會(huì)心理,他們中的很多人至死都沒(méi)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很快被歷史遺忘了。
非虛構(gòu)作品成為社會(huì)記憶,不僅在“記”,更應(yīng)在“悟”;不僅在“憶”,更應(yīng)在“思”;不僅在于記錄“傷痛”,更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社會(huì)記憶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為鑒的先決條件。苦難,特別是普通人的苦難,如果能夠進(jìn)入歷史被記錄下來(lái),被后人吸取,這苦難才是有價(jià)值的,才是社會(huì)共同的財(cái)富,才具有歷史的力量。《遠(yuǎn)去的背影》中關(guān)于“我”在“文革”中的親歷與見(jiàn)聞的記述,雖然著墨不多,卻震撼人心。那些身處偏僻山村和凋敝小鎮(zhèn)的人們?cè)凇拔母铩毙郎u里的種種際遇,那些施暴者的嘴臉,那些受難者的哀嚎,讓人如臨其境,更能引人思考,而這種思考比當(dāng)年讀嚴(yán)家其、高皋夫婦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讀徹底否定“文革”的官樣文章更覺(jué)深刻。頓覺(jué)“文革”之禍貽害深遠(yuǎn),要害在于對(duì)人性的扭曲、對(duì)人心的荼毒、對(duì)民族精神血脈的撕裂,流弊至今,難以正本清源。梁?jiǎn)⒊f(shuō),凡是經(jīng)過(guò)重重內(nèi)亂的國(guó)家是不可能產(chǎn)生純潔國(guó)民性的,內(nèi)亂會(huì)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yǎng)起六種傾向:僥幸、殘忍、彼此傾軋、虛偽狡詐、冷漠涼薄、茍且。此言不謬。除了“文革”之思,《遠(yuǎn)去的背影》也不乏人生真諦的總結(jié),可謂大道至簡(jiǎn)。如“我”父親一生做會(huì)計(jì)工作,“從未出現(xiàn)哪怕是一點(diǎn)點(diǎn)的紕漏”,在對(duì)政治運(yùn)動(dòng)提心吊膽的同時(shí),對(duì)經(jīng)濟(jì)問(wèn)題卻心如止水,無(wú)波無(wú)瀾。“我”父親作為社會(huì)底層的知識(shí)分子恪守的不僅僅是會(huì)計(jì)人員的職業(yè)操守,更是對(duì)傳統(tǒng)義利觀的堅(jiān)守和自覺(jué),這種近乎木訥的清教徒般的“慎獨(dú)”“慎微”,也使自己歷經(jīng)一次次政治運(yùn)動(dòng)而能全身而退,而這些又恰恰是今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所稀缺的。還有“我”母親“對(duì)于我們?yōu)槿颂幨碌难詡魃斫獭保赣H對(duì)于學(xué)習(xí)知識(shí)的重視,家庭屢遭變故、不斷遷徙,對(duì)孩子們的學(xué)習(xí)始終不放松;對(duì)于金錢的淡薄,把父親一生公私分明作為教育子女的“一面鏡子”;告誡子女對(duì)人平和,作人低調(diào),叮囑“吃虧是福”,這些無(wú)不體現(xiàn)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耕讀持家、謙恭禮讓、“君子愛(ài)財(cái)取之有道”等樸素的哲理。這些理念曾是我們中國(guó)老百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的社會(huì)公德、家庭美德的重要內(nèi)容,但今天讀來(lái)卻又覺(jué)得熟悉而陌生。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短短30年時(shí)光,隨著改革開(kāi)放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中國(guó)社會(hu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而最大的變化是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
關(guān)于怎么寫(xiě)的問(wèn)題。單純從概念來(lái)看,“非虛構(gòu)寫(xiě)作似乎涵蓋了虛構(gòu)之外的所有文體。這一概念首先被西方文學(xué)界所使用,因?yàn)檫@比較適合西方的文體分類。但根據(jù)我有限的閱讀經(jīng)驗(yàn)來(lái)看,它又呈現(xiàn)出某些獨(dú)特的文體特征。我理解非虛構(gòu)寫(xiě)作更強(qiáng)調(diào)支持作者以個(gè)人視角進(jìn)行完全獨(dú)立的寫(xiě)作行為。甚至有人主張,這一寫(xiě)作行為不應(yīng)依附或服從于任何寫(xiě)作以外的因素。它與報(bào)告文學(xué)、紀(jì)實(shí)文學(xué)的區(qū)別,在于不追求事件記敘的完整性,不強(qiáng)調(diào)話語(yǔ)表達(dá)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題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確的主觀姿態(tài)介入歷史或現(xiàn)實(shí),直接展示創(chuàng)作主體對(duì)事件本身的觀察、分析和思考。其魅力很大程度在于作家對(duì)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深度介入。這種介入,是積極主動(dòng)的,是微觀化的,是現(xiàn)場(chǎng)直擊式的。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敘事散文,不僅擁有較長(zhǎng)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現(xiàn)場(chǎng)紀(jì)實(shí)性的過(guò)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詩(shī)性的懷想。它更不同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我以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最經(jīng)典的論述還是恩格斯的一段話:“據(jù)我看來(lái),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意思是除了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外,還要真實(shí)地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實(shí)“典型化”的過(guò)程就是“虛構(gòu)”創(chuàng)作的過(guò)程,使“虛構(gòu)”的文學(xué)人物成為以鮮明的個(gè)性,充分地概括了某種范圍的共性、反映了社會(huì)生活某些本質(zhì)方面并且具有較高審美價(jià)值的藝術(shù)形象。而“虛構(gòu)”的方法雖然多樣,歸根結(jié)底就是在廣泛地集中、概括眾多人物的基礎(chǔ)上塑造出典型人物。這就是魯迅所說(shuō)的“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gè)”的方法。而非虛構(gòu)創(chuàng)作完全與此相悖,它強(qiáng)調(diào)獨(dú)特性、獨(dú)立性和現(xiàn)場(chǎng)感。無(wú)論是面對(duì)歷史還是現(xiàn)實(shí),“非虛構(gòu)”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這種現(xiàn)場(chǎng)式的介入性寫(xiě)作姿態(tài),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改變了當(dāng)代作家習(xí)慣蟄居書(shū)齋的想象性寫(xiě)作,激發(fā)了作家觀察社會(huì)的興趣,使作家能夠帶著明確的主觀意愿或問(wèn)題意識(shí),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領(lǐng)域,通過(guò)田野調(diào)查的手段,獲取第一手資料,也獲得最為原始的感知體驗(yàn)。同時(shí),它還體現(xiàn)了作家對(duì)社會(huì)歷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對(duì)某種重要問(wèn)題的深入思考。從這個(gè)意義上看,《遠(yuǎn)去的背影》也有一些欠缺,這主要是作者敘述了幾代人的生活境遇,而對(duì)于“我”爺爺、姥爺那一代人的經(jīng)歷,由于年代久遠(yuǎn),資料來(lái)源是父輩的講述,而非親歷和口授,缺少“人物訪談”或“口授歷史”的現(xiàn)場(chǎng)感。客觀上使一些事件只能略述而難以備述。再者,由于作者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為家庭寫(xiě)簡(jiǎn)史,而非主觀上去創(chuàng)作一部完全符合時(shí)下流行“口味”的非虛構(gòu)作品,從而使我們按照非虛構(gòu)創(chuàng)作的標(biāo)準(zhǔn)去評(píng)價(jià)未免有些牽強(qiáng)。可以預(yù)見(jiàn),待到《遠(yuǎn)去的背影》續(xù)集出版時(shí),這些問(wèn)題會(huì)迎刃而解,因?yàn)樽罱?0年的生活經(jīng)歷,作者有詳盡的日記資料可資運(yùn)用。這是后話。
《遠(yuǎn)去的背影》雖是家庭簡(jiǎn)史,但其可讀性、趣味性卻很強(qiáng),這得益于作者多年小說(shuō)創(chuàng)作而形成的語(yǔ)言風(fēng)格和功力。也得益于作者對(duì)有限“史料”和個(gè)人記憶的取舍和運(yùn)用。我忽然覺(jué)得,如果把司馬遷的《史記》看作中國(guó)古代的非虛構(gòu)作品,那么翦伯贊對(duì)于司馬遷剪裁史料的匠心和功力的論述對(duì)我們很有啟發(fā)。他在《論司馬遷的歷史學(xué)》一文中說(shuō):“兩千年來(lái),讀《史記》未有不盛贊司馬遷之文章者;誠(chéng)然,司馬遷的文章真是氣勢(shì)蓬勃,既沉重而又飛舞。”又說(shuō):“司馬遷的文章之好,不在于筆調(diào),而在于他善于組織史料。例如他撰伯夷,則錄其《西山之歌》,以顯其氣節(jié);撰孔、孟,則錄其言語(yǔ),以顯其大道;撰老、莊,則錄其著作,以顯其學(xué)派;撰屈、賈,則錄其辭賦,以顯其文章;撰儒林,則錄其師承,以顯其淵源;撰管、晏,則錄其政績(jī),以顯其文治;撰田單、樂(lè)毅,則錄其戰(zhàn)伐,以顯其武功;撰張、蘇,則錄其游說(shuō),以顯其縱橫;撰貨殖,則錄其財(cái)產(chǎn),以顯其富厚;撰刺客,則錄其敢死,以顯其慷慨;撰游俠,則錄其重諾,以顯其俠義;撰滑稽,則錄其笑謔,以顯其諷刺;撰佞幸,則錄其賣身投靠,以顯其下流無(wú)恥。總之,他對(duì)每一個(gè)紀(jì)傳的人物,都能夠抓住他的特點(diǎn),闡揚(yáng)他的特點(diǎn),使這個(gè)被紀(jì)傳的人物,躍然紙上,蕭疏欲動(dòng)。”由此去對(duì)照《遠(yuǎn)去的背影》我們也會(huì)找到很多具體的實(shí)例,權(quán)作一個(gè)話題留待以后交流。
趙文凱:1964年10月生于內(nèi)蒙古赤峰。1986年7月畢業(yè)于內(nèi)蒙古大學(xué)漢語(yǔ)言文學(xué)系,同年到內(nèi)蒙古紡織工業(yè)學(xué)校任教,1992年5月到平莊煤業(yè)集團(tuán)公司工作,現(xiàn)任職于平莊礦區(qū)工會(huì)。系中國(guó)煤礦作協(xié)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