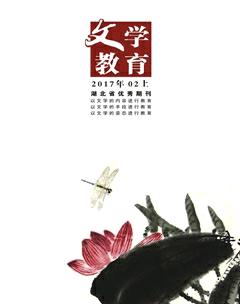淺論陳銓的民族主義文學(xué)
內(nèi)容摘要:陳銓在抗戰(zhàn)時期提倡構(gòu)建民族文學(xué),是在抗戰(zhàn)特定的歷史語境、陳銓自身受中西方文化影響下文化背景共同形成的。他倡導(dǎo)民族文學(xué)運動,強調(diào)“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試圖用文學(xué)的力量來重新建構(gòu)有“力”的民族精神、推崇“英雄”;這種民族精神,在他的文學(xué)批評觀念也直接的顯現(xiàn)出,他的思想雖然含有一定的激進成分,但試在特定時代下的產(chǎn)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時代意義。
關(guān)鍵詞:陳銓 民族 意識
隨著意識形態(tài)的逐漸寬松與思想的更加多元,學(xué)界和讀者對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擱置的陳銓創(chuàng)作的關(guān)注認識越來越多。陳銓以及戰(zhàn)國策派成員創(chuàng)作了一批作品,從民族意識的的萌發(fā),到提倡民族文學(xué)運動,乃至形成的民族文學(xué),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與自身的文化背景下的產(chǎn)物。陳銓民族文學(xué)的意義,在一定上說,其思想、社會意義大于自身文學(xué)性的意義。
一.民族文學(xué)的建構(gòu)
陳銓是戰(zhàn)國策派宣傳民族文學(xué)的主將,在40年代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天問》《狂飆》,《民族文學(xué)》《民族運動與文學(xué)運動》《浮士德精神》、以及戲劇《野玫瑰》《藍蝴蝶》《金指環(huán)》《無情女》《黃鶴樓》一系列作品。他的作品從開始的個人主義到民族主義狂飆的轉(zhuǎn)變,圍繞著民族意識進行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陳銓對于民族精神強大、團結(jié)的審美理想和愿景。
1.疏離于官方話語的民族文學(xué)
陳銓民族文學(xué)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學(xué)界。其作品主要是在校園內(nèi)進行創(chuàng)作,更為重要的是從文化思想內(nèi)容上看,他的民族文學(xué)的性質(zhì)上單純 是學(xué)術(shù)文化上的討論。1934年,陳銓從德國留學(xué)歸國,重心是在他的學(xué)術(shù)思想研究與大學(xué)任教上。正如“它所宣揚的思想與其說是有些人所指責(zé)的法西斯主義其實不如說是較極端的民主主義思想。”[1]他宣揚西方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并旨在通過這種手段來挽救中國的文化誤區(qū)以及民族危難。陳銓拒絕了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瀚邀請他擔(dān)任政府要職,可見,陳銓的民族文學(xué)的活動范圍是和政治黨派疏離的。
民族文化的宣揚不等同于政治理想。一,這些作品都是以抗日為主旋律,并無政治色彩。二、不僅僅是陳銓,一些在共產(chǎn)黨人的作品也獲獎。從陳銓發(fā)表的作品上看,只是通過作品傳達出作者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陳銓雖說過如此的言論:“文學(xué)和政治是常常分不開的,因為政治的力量支配一切,每一個民族都是一個嚴(yán)密的政治集團,文學(xué)家是集團中的一分子……離開政治,等于離開他自己大部分的思想生活,他創(chuàng)造的文學(xué),還有多少意義呢。”[2]加之《野玫瑰》引起的爭論,左翼文化人士對陳銓進行更激烈批判。但是,陳銓主張文學(xué)和政治的關(guān)系,意在于發(fā)揮文學(xué)更強的功效去強國,不代表他本身涉及任何政治團體,這只是他的文化理想。
2.民族危機下的時代背景
“文學(xué)是文化的一部分,時間空間的不同,文學(xué)就會呈現(xiàn)出各種特殊的情狀,那么文學(xué)的性質(zhì)也要受到時間空間的限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xué)”。[3]陳銓民族文學(xué)形成的背景一是現(xiàn)實社會的歷史條件,陳銓出生于光緒29年,少年的陳銓就經(jīng)歷了西方列強在經(jīng)濟政治上的侵略,社會上的出現(xiàn)了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沖擊著陳銓的內(nèi)心。1928年,陳銓開始了異國留學(xué)的路程,對比國內(nèi)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陳銓作為知識分子敏感的心深深地被刺痛。這正如郁達夫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孤寂與自卑,在《沉淪》的最后的吶喊:“祖國啊,你強大起來吧。”[4]陳銓與郁達夫的絕望相比,更多的是一份擔(dān)憂與奮進。在《戀愛之沖突》中以嘲諷批評的口吻對當(dāng)時留學(xué)生不爭氣的樣子做了描寫;“芝加哥大學(xué)的一個教室里,坐滿了七八十個留學(xué)生……拉壞梵婀林把旁邊屋子的人急的破口大罵的音樂家,跳舞把腳趾頭跳腫了……”[5]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使得陳銓的文學(xué)觀念更加側(cè)重于挽救于社會危亡。
除了社會歷史現(xiàn)實,陳銓自身的文化背景對陳銓的文學(xué)觀念起到影響。陳銓可以說是和其他同時代的文人浸泡在古典傳統(tǒng)知識中,其父是光緒六年的秀才,師從吳宓、陳寅恪中西貫通的學(xué)者,奠定了陳銓深厚的傳統(tǒng)文學(xué)基礎(chǔ)。以自身對傳統(tǒng)文化得了解,進行批判與贊揚。陳銓親自置身于德國濃厚的民族氛圍之中,不斷反思傳統(tǒng)的文化和傳統(tǒng),加之當(dāng)時希特勒大規(guī)模宣傳的民主主義,陳銓的民族意識逐漸形成。
3.民族意識是核心
民族意識具體的定義,陳銓本人在著作中也沒有下過具體明確的定義。能確定的是,陳銓的民族意識是其民族文學(xué)的根基即強調(diào)“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把民族的整個發(fā)展放在第一位。他認為:“一個民族能否創(chuàng)造一種新文學(xué),能否對于世界文學(xué)增加一批新成績,先要看一個國家有沒有民族意識,就是說它自己覺不覺得它是和世界上任何民族不一樣的人。”[6]民族意識即“意志”的顯現(xiàn)。在《偉大的將來——意志哲學(xué)》陳銓敘述到:叔本華最基本的觀念,就是“意志”。是宇宙人生的源泉,是推動一切的力量。”[7]在陳銓眼里,這種意志能夠推進中國整個民族追求獨立解除壓迫,叔本華更是認為:“意志完全是盲目的,沒有目標(biāo)的,沒有理性的。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肯犧牲一切的人,他一定是把自己看輕。個人存在的意志里解放了自己。”[8]不是陳銓完全拋棄了叔本華的思想,而是把其中的悲觀主義消解,畢竟這與陳銓追求的民族解放背道而馳。
二.民族文學(xué)視域下的創(chuàng)作
戲劇小說創(chuàng)作,無論是在主題、以及人物塑造上體現(xiàn)著他的民族意識,陳銓對于文藝?yán)碚撘仓约邯毺氐囊娊猓瑢τ谖逅膫€人主義的批判、盛世文學(xué)的認同、以及以文化作為文學(xué)批判的尺度,都是對民族意識的闡釋。
1.戲劇小說創(chuàng)作
陳銓戲劇小說主題上顯現(xiàn)著鮮明的民族意識。陳銓認為文學(xué)是求異的,構(gòu)成文學(xué)特殊的條件,一是:“文學(xué)家是一個特殊時代的人,離開時代,損壞他的文學(xué)的價值。[9]“在抗日救亡上升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時,陳銓與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一樣沒有置身事外。但陳銓的創(chuàng)作有著鮮明的特點。他雖描寫正面戰(zhàn)場的硝煙炮火,但主要將視點放在個人的革命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的個人經(jīng)歷,并未投入到廣闊的戰(zhàn)場上。另一方面,陳銓的民族主義思想,主要是力圖改變?nèi)藗兯枷氲淖兓虼耍瑢⒅攸c放在個人革命路程上是有情可原的。
陳銓的作品中的人物塑造顯現(xiàn)著民族意識。陳銓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大部分是放棄個人小我的領(lǐng)導(dǎo)者,在智力上不同于常人的。“意志的中心,是群眾的代表,是喚醒群眾的先知。”[10]陳銓塑造出樊秀云、夏艷華、尚玉琴、李鐵崖一些列有勇有謀的人物,也說出了陳銓呼吁中國人民要有英雄崇拜。
2.浪漫主義的審美和理想主義的建構(gòu)
浪漫主義運動發(fā)生于十八世紀(jì)末,流行于十九世紀(jì)初,其中德國的浪漫主義影響最大,他們的思想與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理想主義一脈相承,所以談到浪漫主義不能不談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就是理想主義,理想主義最重要的就是對真善美的無線追求。[11]德國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文學(xué)對于人類精神高遠境界的向往,從理論上說,陳銓的創(chuàng)作,尤其是“浪漫悲劇”《金指環(huán)》《藍蝴蝶》都顯示出主人翁對真善美的追求,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他的理想主義,具體到中國的具體國情就是希望國家的強盛、建立起強烈的民族意識。
這種浪漫主義通過革命傳奇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主要表現(xiàn)在離奇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的設(shè)定,情節(jié)的安排往往出乎意料。
3.文學(xué)批評的民族觀
陳銓創(chuàng)作了許多的文論,這些文學(xué)批評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更為直接的闡述他的觀念。
首先,陳銓批評的五四文文化中的不足。他認為五四運動沒有認清中國的現(xiàn)狀,把中國帶出落后挨打的局面。在《五四與狂飆》中認為:“中國的五四運動,在歷史上價值是很大的,然而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成績,卻比不上德國的狂飆運動,德國狂飆運動以后,德國民族,完全認清自己,踏上理想主義的途徑。”[12]五四運動的觀念他指出的問題有以下幾點:一把戰(zhàn)國時代認為春秋時代。陳銓認為當(dāng)時中國內(nèi)憂外患,單憑借新文化陣營的幾次運動與幾篇倡導(dǎo)和平的文章,不提倡戰(zhàn)爭的意識,是非常可惜的。再次,五四運動把集體主義的時代,認為是個人主義的時代。陳銓痛斥那些不顧民族愛國情緒個戰(zhàn)斗情緒不高的人。第三就是把非理智的時代誤認為理智的時代。
再次,陳銓把文化做為文學(xué)批評的標(biāo)準(zhǔn)。這指的是將作品能否表現(xiàn)本民族文化精神作為標(biāo)準(zhǔn)。陳銓看來,“文化是在歷史長河中結(jié)晶而成的“一個民族共同對人生的態(tài)度”。[13]他的批評標(biāo)準(zhǔn),與他的文藝觀和價值觀是不無關(guān)系的。第一、陳銓提倡民族精神,民族文學(xué)加強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學(xué)的根基,兩者互為促進。第二,陳銓認為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個性,文學(xué)是求異的。因此,中國人表現(xiàn)中華民族的文學(xué)理所應(yīng)當(dāng)也是不可推卸的義務(wù)。
陳銓他的民族文學(xué)史有且別于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學(xué),后者的目的是通過宣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鞏固自身的文化政權(quán),兩者在目的上截然不同。使陳銓有些極端,有些偏頗,但也是對于民族強大的一種鞭策。
參考文獻
【1】季進,曾一果:陳銓,異邦的借鏡.文津出版社,第61頁
【2】陳銓:《民族文學(xué)運動》,載重慶《大公報.戰(zhàn)國副刊》,第24期,1942年5月13日。
【3】陳銓:《民族文學(xué)運動》,選于《時代之波》,大東書局,1946年
【4】郁達夫:《沉淪》【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04
【5】陳銓:《戀愛之沖突》選自《野玫瑰》【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1,第43-44頁
【6】【7】【13】陳銓:《文學(xué)批評的新動向》,1943年5月版,中正書局
【8】陳銓:《野玫瑰》【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1,第235頁
【9】陳銓:《民族運動與民族文學(xué)》選自《文學(xué)批評的新動向》,1943年5月版,中正書局
【10】陳銓:《論英雄崇拜》《戰(zhàn)國策》第四期,1944年5月15日。
【11】陳銓.青花---理想主義和浪漫精神【J】.國風(fēng).1943.
【12】陳銓《五四與狂飆》原載《民族文學(xué)》1卷3期,1943年9月7日。
本文為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2016年校級一般項目,項目編號kjcx2016-12mdjnu。
(作者介紹:喬梁,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
- 文學(xué)教育的其它文章
- 吾師
- 母親
- 《魯濱遜飄流記》讀后感
- 云深不知處
- 老人與狗
- 師范生性別比例失衡問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