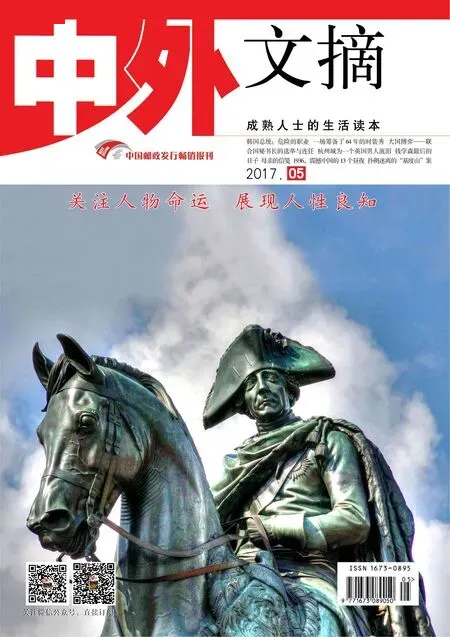無處投寄的思念
無處投寄的思念
□ 江 琴 徐 琪

傷離別
母親啟程前夜,父親母親幾乎徹夜未眠。父親試圖通過安慰母親來掩飾自己的情緒。他說:“臺灣馬上就要解放了,比你預想的要快。別擔心美國的軍事援助,國民黨的日子不多了。頂多三個月,你和孩子們就會回到我身邊,我們可以一起過上新生活。”
母親什么也沒說。她默不作聲,眨著眼睛,不讓淚水落下來。只身前往臺灣幫助家人并沒有嚇倒她,她知道自己具備生存的能力和毅力。令她心痛的是在臺灣缺少了父親在身邊的安慰與支持。他們才結婚安頓下來,現在卻不得不忍受又一次的別離。
第二天天剛亮,父親便出門安排了兩輛黃包車和一輛平板車,載著母親、外婆、母親的弟弟妹妹們及行李前往港口。在那兒,軍艦將會載著最后一批人(大多數是與國民黨有關的婦女和兒童)前往臺灣。外公的一位頗有影響力的朋友是國民黨軍隊中的將軍,他已經做了交代以確保我們此行的安全。
母親喂完我后,幫我洗了臉,給我穿上粉紅色針織套衫。然后,她讓父親到房間里檢查旅行證件和行李。早上9點鐘,外婆把頭探了進來,告訴母親出發的時間到了。
父親低聲對母親說道:“別擔心,我們很快會見面的。你到了之后,要給我寫信,讓我知道你一切安好。”
母親沉默地點著頭,又把頭低了下去,盡力掩飾她的淚水。突然間,她推開父親,抱起我,跳上正在等候的黃包車。外婆清點人數后與父親告別。她緊握父親的手,說道:“照顧好你自己和我們的房子。”
父親向外婆保證說他一定會的,但事實上,他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作為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新成員,他必須小心翼翼地行動。
父親鎖上門后,坐公交車來到碼頭,卻發現已經太遲。由于乘客少,外婆他們早已登船。母親揮舞著白手絹,伸長脖子找父親,希望能留下最后一眸。父親沒來得及走近,船已拔錨,他只能呆呆地望著船啟動時發動機所激起的陣陣白浪。很快,母親瘦小的輪廓和揮動的白手絹隨著遠行的船只漸漸消失在地平線上。父親默默祈禱他們旅途平安,也祈求他與母親能早日團聚。雖然那是八月里炎熱的一天,父親卻突然感到空氣中有一絲寒意。不知何時,地平線上出現了一團烏云,這似乎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船上的臥艙是由一條細長的通道分割成兩半建成的。這艘船原來是用來運載蔣介石軍隊的貨物的,現在用來疏散國民黨的家屬。一個瘦弱而年輕的國民黨士兵面帶謙遜的笑容大步地走了過來。他瞧了母親一眼,注意到她有身孕,母親也知道他在看她,但她沒有理會。她心情低落,心事重重。太多事情發生了,她思索著在臺灣的不確定的未來,也擔心著父親,不知何時才能重見。
她把手伸進口袋里,摸到一張父親在臨別時匆忙塞給她的紙條,上面寫著:“年輕的母親,我會永遠等著你回來。”這句話和父親的字在接下來的歲月里帶給了母親無限的安慰和力量。
旅途過程中,母親沒有與其他人接觸。家人知道她正為與父親的分離而難過,最好讓她獨處。母親在搖晃的船上發現了一塊安靜之地,在那兒可以呼吸一些新鮮空氣。為了擺脫分離的憂思,她從包里拿出針線開始編織。她靈活的手指立刻吸引了一些乘客。她們坐在母親的身邊,似乎被她飛快跳動的手指和閃閃發光的針頭碰撞所發出的節奏聲給迷住了。在船靠岸前,母親已經編織完一件完美的嬰兒毛衣。母親把毛衣收起來,然后與其他人一起等候下船。
終于,他們抵達了臺灣。母親像一座雕像似的站著,臉色蒼白,面無表情。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難民們的憂郁情緒像散不開的濃霧籠罩在船的四周。
綠墨水風波
沒過多久,母親就因為婚姻狀況陷入了麻煩。她在身份證上注明她是已婚但分居兩地。國民黨當局憑借其嚴密高效的情報網絡,迅速認定我的父親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人員。而母親因為家教常常深夜歸家,因此就有鄰里中的特務眼線開始懷疑母親參加了非法集會。母親開始在回家時變得膽戰心驚,總感覺路上有陌生人尾隨。不久之后,當地警察局便以問話為由扣留了母親,卻又因為缺乏證據不得不放人。然而,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那是一個大雨傾盆的午后,外婆沖進門對剛放學回家的我說:“有人向社區居委會舉報了你母親,說她試圖和你父親聯系。”外婆難以遏制地顫抖著,用嘶啞的聲音繼續說道:“謝天謝地,老鄭,我們的那個鄰居,是社區領導,知道你母親是無辜的。他說他不會向上頭遞交那封舉報信。天知道,你母親為了供養這一大家子人早就忙得昏天黑地,哪里來的時間去寫信啊!這事究竟是誰干的呀?”外婆怒斥道,眼里充滿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希文舅舅回家后,外婆又把事情向他復述了一遍。舅舅年輕的臉龐因為憤怒漲得通紅,他咆哮道:“我敢說這事就是他干的。”舅舅口中的“他”指的是劉某,我父母在廈門大學的同窗,也是我母親的忠實愛慕者。他從高中開始就傾慕成績優異的母親,而母親在各方面尤其是在演講上表現出的才華更是深深地吸引了他。當年母親結婚后他曾震驚絕望,但他相信此時父親與母親二人已海天相隔,正是他接近母親的大好時機。在他看來,一個拖家帶口的單身女人是不會拒絕他的示好的。但他大錯特錯了!我的母親,胡希明,可不是個普通的女人。她過去深愛著我的父親,現在也一樣深愛著。自然,母親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因為在她心中,我的父親是無可替代的,她有與父親相關的美好記憶和兩人間甜蜜深摯的愛情支持著。母親的拒絕在劉某看來是一種羞辱,所以他編造出謠言想讓母親被驅逐出島,以達到他報復的目的。如果他的陰謀得逞了,我們的家就真的要垮了,因為失去了母親的經濟來源,我們將無法生存。
那晚,希文舅舅冒著狂風暴雨找到老鄭,希望知道誰是舉報者。老鄭不肯說,于是舅舅改變了戰術。他試探道:“老鄭,或許你有難言之隱,但你能不能告訴我那封信是不是用綠色墨水寫的?”老鄭被舅舅的問題驚得目瞪口呆,他盯著舅舅,思索了片刻,開口道:“年輕人,將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藏在心里。今晚我會銷毀那封信,你姐姐和你的家人都會平安無事的,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老鄭說完這些便閉口不言。盡管老鄭沒說是或不是,舅舅已經印證了他的猜測。
我的舅舅和母親感情一向深厚。母親大他十歲,像是他的母親一般照料著他。在大陸時,當日軍的炮火籠罩村莊時,是我的母親背著他到安全的地方躲起來;到了臺灣后,母親為他親手縫補校服。每當母親晚歸時,舅舅會出門去接母親,陪著她一起回家。也正是在回家的路上,母親告訴過他劉某對她的示愛和追求。顯然,舅舅也看過劉某用綠色墨水寫給母親的信,那特別的顏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們家被莫名的悲傷籠罩著。善良的外公外婆無法接受劉某的背叛。畢竟,在我們來臺灣之前,他就已經是我們家中的常客了。他經常和我們一起吃飯,和外公說笑。在舅舅們的心中,他就好比是兄長。“我一直以為我不會看錯他呢。”外婆喃喃自語,“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外公則沉默不語。我知道他是在為發生在他女兒身上的不幸而痛心,女兒受苦是他最不愿意見到的事。他困惑又無助,甚至懷疑母親來臺灣的決定是錯的,他開始責怪自己當初沒有阻止她。
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在事情發生了幾周后,劉某竟然還敢來我們家吃晚飯。他就像個惡魔,害了人還要來看看被害的人怎么樣了,看看他的陰謀是否得逞。外公和外婆十分吃驚,但是他們盡量裝作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過。還好那天晚上還有幾個老朋友也在,免去了我們和他相處的尷尬和不快。盡管如此,我發現外公還是一反常態地沉默著,皺著眉,眼里不時閃過警覺的眼神。外婆也一直借口去廚房,一晚上只出來了幾次,跟客人寒暄了幾句。
我們坐下吃晚餐時,我觀察著劉某,他坐在溫暖柔和的燈光下,但我感覺我能從他不動聲色的臉上看出他的內心。他心里一定在想:“警察收到我的揭發信了嗎?這些人會猜到我就是寫信的人嗎?”他僵直地坐著,雙手顫抖,還把筷子掉到了地上。盡管窗戶開著,不時有涼風陣陣,但劉某還是在流汗,前額上都是汗珠。當他看向我時,我覺得他的目光冷冰冰的,好似鐵劍一般向我投來,我不禁覺得后背發涼,毛骨悚然。我只好盯著面前的青椒和牛肉,不敢抬頭,以免自己控制不住,害怕膝蓋發抖發出聲音。突然,外公的聲音打破了緊張的氣氛:“姑娘們,你們可以走了,不是還有作業要做嗎?”妹妹和我立刻騰的從座位上跳下來,直奔房間,能夠離開餐桌真是讓我們松了一大口氣。
劉某沒有等到我媽媽回來就離開了。或許他良心發現,因此在我們家呆不住了。這樣也好,要是我舅舅回家,我想劉某是不可能毫發無損地離開的。
大概六個月之后,我們收到劉某寫的信,還是用可恨的綠墨水,他告知我們他已經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去美國學習數學,即日便將離開。我們全家都很高興。我們把信扔進火中,用力將他永遠地從記憶中抹去。二十年后,我們又收到了他的來信,但這次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
思念無盡
尼克松的歷史性訪華是1972年的頭條新聞。美國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也為此開始全國性的論戰,學生們分成兩派,一派是臺灣當局的擁護者,他們抗議尼克松訪華;另一派站在中國大陸這一邊,對對方言論予以回擊。接下來的十年里,兩派學生的隔閡日漸擴大。
1973年,母親取得美國國籍,有了穩定的身份。于是,她立即開始尋找父親。當時,中美兩國還未建交,母親只能向加拿大中國領事館尋求幫助。很快,她得知在“文革”中,父親被下放到福建的一個小山村教高中語文。父親和母親終于開始通信。母親急切地想要見到父親,但父親的回復卻不冷不熱。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父親已經組建了新的家庭,二是父親當時正被下放。他原來是新華社記者,那時則是被改造的對象。在中國當時翻云覆雨的運動中,父親受到的迫害和煎熬已經讓他如履薄冰,他不知道和在西方世界的前妻聯系又將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厄運。但更重要的是,父親不愿意傷害母親,或者說是他更不愿意讓母親失望。
1973年冬,母親前往香港,希望能夠通過香港回內地。這個決定十分草率,她甚至都沒收到父親的回復。不過,香港方面也拒絕了母親的申請。備受打擊的母親,獨自一人從香港取道馬來西亞,又去了新西蘭,最后回到紐約。到各地去旅行是她自我療傷的過程。在馬來西亞的時候,母親給父親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詳細地描述了我們姐妹倆如何長大成人及已陸續離家的過程。她又直截了當、毫不含糊地說:“我不會給你帶來任何麻煩,但是我必須知道事實。”這樣,她就不必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尋找父親。母親寫道:“不管怎樣,我是個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像一臺計算機一樣,說開就開,說關就關。”
收到母親的信后,父親悲痛欲絕。他知道母親這二十多年的日子有多艱難。雖然他也明白他們兩人的分離是因為時勢所致,但卻不能不自責。父親很快寫了封回信寄到母親在長島的地址,希望母親一回到美國能馬上看到。他們一旦恢復了通信,那壓抑已久的感情就如同沉睡的火山突然爆發,來勢兇猛,一發不可收拾。
石溪因為離紐約市很近,很快就成為中美關系論戰的前鋒。中國大陸和臺灣雙方都想盡辦法爭取支持者,向各校園提供了各種免費宣傳影片和書籍。石溪和當時美國其他很多大學一樣,分為兩派,針鋒相對,水火不容。母親當時是親中國大陸陣營的積極支持者,她是“中美人民友好協會”最早的會員之一。這個協會并沒有任何政治性目的,協會的宗旨在于促進中美兩國人民間的友誼。雖然母親一直以來都很愛國,但她對政治并不感興趣。當然,在臺灣的經歷也有可能讓她更傾向于中國大陸。但母親參加“中美人民友好協會”還有其個人目的,那就是想要早點見到父親,一年前申請訪華被拒的事還時刻涌上她心頭。
第二年,母親再次向中國政府申請入境,這一次,簽證順利通過了。我想母親在協會中的積極表現應該是發揮了某種重要作用。
(摘自《中外書摘》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