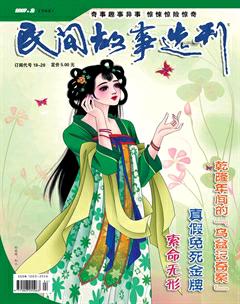乾隆年間的“烏盆記奇案”
《烏盆記》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鬼戲,由于這部戲舞臺形象可怖、唱腔動人,又被多位名人關注或演繹,所以名氣極大。不過下面要講的,卻是發生在乾隆年間的一個奇案,它被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記錄在《子不語》一書中,這起案件的吊詭之處極多,比如,從一開始就和《烏盆記》扯上了關系。
假包公遇上“真鬼魂”
乾隆年間的一天,廣東省三水縣的縣衙前人聲鼎沸,萬頭攢動—這天正趕上吉慶的日子,戲班子搭起了舞臺要演整整一天的戲。這天的主打劇目是《烏盆記》,包青天斷烏盆,在那個年代可稱得上是“恐怖懸疑大片”,不光戲臺下面的觀眾,就連準備粉墨登場的演員們也興致勃勃。前面四場,演的是劉世昌遇害后,其冤魂請求一個叫張別古的老頭兒替他找包公告狀;第五場輪到包公上場,上來后應該有這么四句臺詞:“十年寒窗讀圣賢,常將鐵硯試磨穿,身受皇恩為知縣,朝廷王法大于天。”然后,包公命令兩位差役將放告牌抬出,之后才是飾演張別古和劉世昌的演員上場—對這段表演,臺下的觀眾大多已耳熟能詳。
只見“包公”上得臺來,在公案后面落座。突然,他雙目圓睜,大吼一聲:“你是何人?為何跪在臺上?!”
原本有點喧鬧的臺下,剎那間寂靜如死,他們和扮演差役的演員一樣,大白天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因為“包公”說出的話并非戲詞,而且他對著說話的那一處舞臺上,根本就空無一人!
誰知更加可怖的一幕出現了:“包公”從座椅上跳了起來,即便是濃重的黑色油彩也掩飾不住他那驚恐萬狀的神情,他一面跌跌撞撞地朝后躲避,一面用顫抖的聲音喊道:“你是什么人?為何頭上帶傷、滿臉是血?你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臺下的觀眾萬萬沒想到,看《烏盆記》卻趕上了“鬼告狀”直播,一片嘩然,“其聲達于縣署”。
一座墳埋了兩個人
此刻正坐在縣署里辦公的知縣,聽到外面的喧嘩聲,立刻命令差役前去查看發生了什么事。不久,差役把飾演包公的演員帶了回來,只見他的臉已被汗水污得青一道紫一道,帽子也掉了,驚魂未定地說:“嚇死我了,剛剛在舞臺上落座,便看見一個披頭散發、滿臉血污的人跪在臺上……分明是個鬼魂啊!”縣令聽了也十分吃驚,命他將那鬼魂帶到公堂上來。
演員無奈,只好走出縣署,重新回到舞臺上,坐在公案后面,依舊望著舞臺上那處空無一人的地方,很久才開口說:“我這個包公是假的,你若有冤情,不如跟我一起去縣署,讓縣令大人替你討回公道。”然后朝臺下走去。
已經升堂的縣令,見那飾演包公的演員上得堂來,且指著身后說:“大人您看,他已經跪在臺階下面了。”縣令起身看去,見臺階下空無一人,只聽演員低聲說道:“大人,那冤魂朝我招手,看意思好像是讓我們跟著他去什么地方,我該如何是好?”
縣令決定帶人跟去看看。一路走去,他們來到了一處草長叢深的野地里,前面兀立著一個饅頭樣的墳包,墓碑上的文字寫著“冢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演員指著墳頭說:“那鬼魂鉆進里面不見了。”
縣令更以為奇,命人把王監生找來。王監生被帶來后,縣令命人掘墓,頓時鍬鏟俱下,地面剛剛挖了兩三尺,一具頭骨碎裂的男尸就從土里浮現了出來。王監生見狀嚇得面如土色:“冤枉啊大人!我母親下葬時,送葬的人數以百計,他們都看到了我母親的棺木入土時的場景,根本沒有這具尸體。”縣令問道:“你是看到墓坑封土之后才離開的嗎?”王監生搖了搖頭:“我看到母親的棺材下到墓坑之后,就帶著送葬的人們一起回家了,剩下的封土之事都是土工所為。”
縣令撫掌大笑:“吾得之矣!”
隨即,縣令將那天埋葬王監生母親的土工們都找了來。土工們見事情敗露,撲倒在地不停地磕頭道:“我們認罪,我們認罪!”
伸張正義的“獨角戲”
原來,那天王監生帶著送葬的人們離開墓地之后,這幾個土工便在附近的一個茅棚下歇息抽煙。有個獨行的旅人迷路走到這片荒野之中,上前來向他們問路,順便討口旱煙抽。土工中的一人偷偷往那人肩上的包袱縫隙瞄了一眼,發現竟是白銀,頓時財迷心竅,跟其他幾人商議殺人劫財,把尸體埋到王母墓里。土工們一聽,都覺得此計妙極,于是痛下殺手。
在刑場上,一個土工對著同伙們嘆息道:“還記得埋尸時咱們曾經夸耀,這樣的殺人滅尸之法,誰也破不了案,死者要是想申冤,恐怕只有包龍圖在世才能做到吧……”監斬官聽了,更覺得此案真是詭奇之極,認為那個死者的冤魂正是聽到了土工們的對話,才受到啟發,雖然包龍圖已不在世,但總可以找戲臺上的包公申冤吧!
實際上,聽到土工們對話的并非什么鬼魂,而是那個扮演包公的演員:當土工們殺人埋尸的時候,那個演員因為內急,恰恰就在附近的草叢中目睹了慘劇的發生,也聽到了殺人者猖狂的對話,受到啟發,才有了這出伸張正義的“獨角戲”。
選自《北京晚報》
(段明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