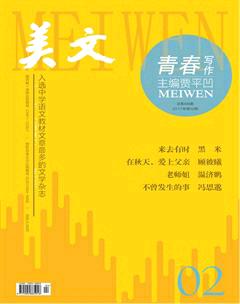軟硬兼施為上品
章伊辰
怎樣挑選一顆優秀的手榴彈?或有一種粗拙的角度:看它的外殼是否足夠堅硬,里面的火藥是否足夠帶勁。空有硬殼,火藥蹩腳,免不得是個啞炮;火藥給力而彈殼易碎,也容易炸傷自己。唯有內外兼優,軟硬兼具,手榴彈才有可能飛越彈雨擊中目標,然后火藥爆炸,彈片四濺,于無聲處起驚雷。
竊把小說也分成軟、硬兩個部分,硬實力在于結構安排、敘事技巧、語言風格等等,軟實力體現于小說主題,即其精神內核。對于科幻小說,硬實力更有兩個集中的體現,一為“科”,即支撐小說的科學理論;二為“幻”,即通過想象對理論的具體展現。還有軟實力呢?可以把它稱為“靈”,像一顆衛星,游離在“科”“幻”二字之外。
由我觀之,《北京折疊》的“靈”可稱不錯,切入新穎,人文關懷滲透其中;但在“科”方面較為薄弱,流于空泛,在“幻”之方面同樣不遂人意,想象或許新奇,但因缺乏必要的理論基礎而站不住腳,反而更像奇幻、玄幻,反正不太像科幻。
《北京折疊》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未來之北京由于土地緊張改造成為三個空間,靠建筑的翻轉折疊輪流露出地面,三種階層的人分居其中,享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一個垃圾站的工作人員為了給撿來的養女掙學費,接了一個送信的任務,從第三空間“偷渡”到第二和第一空間,完成任務拿了報酬回家。這是一趟有驚無險的旅程,借此作者描繪了三種生活畫面,也提出這樣一個可能的未來:生產力的發展使勞動力無關緊要,機器人基本可以代替人來工作,底層人連被剝削的理由都失去了。出于維持社會穩定政府才保留底層人的部分工作,于是他們被“塞到夜里”,不參與社會經濟的運作,過無法反抗的卑微生活。
作為小說之“靈”,作者對民生的關切貫穿全篇,從許多細節中我們能發覺作者之敏銳,也能看出潛伏的情感,這是作者成功之處:人文關懷的默默滲透,如同縈曲折中始見的涓流。
但是科幻小說之所以區別于廣泛的小說,正在于“科”“幻”這兩種硬實力,作為雨果獎的獲獎篇,竊以為《北京折疊》在這兩點上實在沒有做好。
譬如此篇小說最核心的科幻構想,其中的折疊城市,作者絲毫不提其構建原理和筑造過程,只用主角父輩的記憶旁敲側擊:“他們埋頭斧鑿,用累累磚塊將自己包圍在中間,抬起頭來也看不見天空,沙塵遮擋視線,他們不知曉自己建起的是怎樣的恢弘。直到建成的日子高樓如活人一般站立而起,他們才像驚呆了一樣四處奔逃,仿佛自己生下了一個怪胎。”哪有這么簡單?哪有這么多藝術感?細節在哪里?我在讀這篇小說時,總期待著作者會補敘理論和原理,可惜到結尾也沒看到影子。
作者對城市折疊旋轉的畫面之描寫也顯得蒼白——我是指缺乏科幻想象力——而同樣地流于理想化與浪漫。“高樓像最卑微的仆人,彎下腰,讓自己低聲下氣切斷身體,頭碰著腳,緊緊貼在一起,然后再次斷裂彎腰,將頭頂手臂扭曲彎折,插入空隙。高樓彎折之后重新組合,蜷縮成致密的巨大魔方,密密匝匝地聚合到一起,陷入沉睡。然后地面翻轉,小塊小塊土地圍繞其軸,一百八十度翻轉到另一面,將另一面的建筑樓宇露出地表。樓宇由折疊中站立起身,在灰藍色的天空中像蘇醒的獸類。城市孤島在橘黃色晨光中落位,展開,站定,騰起彌漫的灰色蒼云。”
《北京折疊》,感人是有的,可這感人多由文藝的想象而發,少由科幻的構建而起;不像劉慈欣的作品,早期文藝氣息濃郁,如《朝聞道》《帶上她的眼睛》《鯨歌》《詩云》等等,后來較成熟的作品則將文藝和科幻糅合在一起,譬如《三體》。書里,當銀河系被二向箔平面化時,大劉磅礴的想象讓我有些難以全盤接受的呆滯,這是純粹的科幻,與文藝無關;當我讀到程心在冬眠的宇宙流浪后來到星環太空城,坐上百千年前坐過的公交,聽到鄰座關于鯽魚、高仿A貨和工資高低的討論時,那一刻的震撼實在無與倫比。
在科幻硬實力方面,對劉慈欣的作品涉及的理論,我缺乏知識去理解,對寶樹之類新興作家的作品,倒能略知一二。對《北京折疊》,我唯一看到的理論只是:“大地的兩側重量并不均衡,為了平衡這種不均,第一空間的土地更厚,土壤里埋藏配重物質。”
比起一些外國科幻小說,《北京折疊》的主題也并沒有那么高。相對而言,這篇小說的名字在文學方面擁有更多的象征、隱喻和深層含義,而在科幻方面,它只是說出了表層。《北京折疊》是篇好小說,但并不能稱得上一篇好的科幻小說。
回到小說與手榴彈的比喻,也許《北京折疊》的作家擅長研發火藥,但并不能造出一個好的外殼。作為一篇科幻小說,《北京折疊》獲雨果獎,我覺得是個意外,因為它只是披了一件科幻的外衣。如果把雨果獎的評委們比作軍工專家,或許《北京折疊》獲獎的原因很簡單:
他們只是玩膩了戰爭武器,想要收集一顆手榴彈工藝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