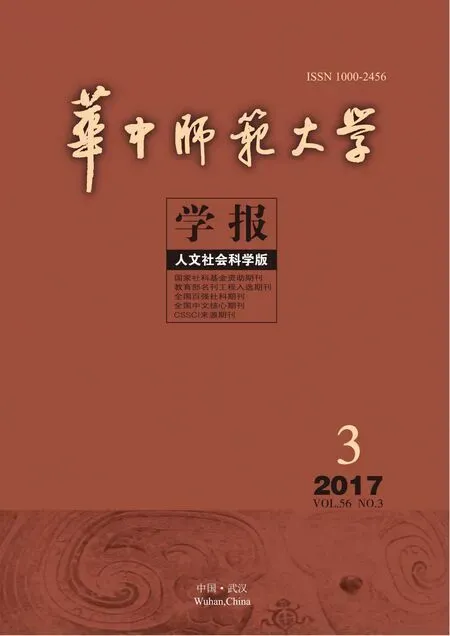茅盾“未完成”長篇小說探析
趙學勇 高亞茹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2)
茅盾“未完成”長篇小說探析
趙學勇 高亞茹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2)
茅盾“未完成”長篇小說創作作為一種“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引人注目。這種“未完成”,與茅盾對中國現代社會、革命的認知方式以及創作策略緊密相關,它是茅盾以文學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實踐的結果。在現代長篇小說的創造期,茅盾的創作極富實驗性特征,它不僅真實地反映了茅盾在文學的功利性與審美性之間的價值取向,也折射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重估茅盾長篇小說創作的文學史價值和意義,更能深刻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所經歷的艱難而復雜的演變歷程。
茅盾; 長篇小說; 未完成現象; 文學史重估
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小說創作奠定的,尤其是他的長篇小說創作,在文學史上有更為突出的歷史性貢獻。然而在茅盾的創作生涯中,卻有一個極為特殊而醒目的現象,那就是未完成長篇小說的大量存在。如果一個作家在眾多作品中有個別殘篇出現,這也無可厚非。而作為著名小說家的茅盾筆下卻出現了多部殘篇,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種奇特的現象。
茅盾的創作,在呈現不斷上演的殘篇現象的同時,也反映出了現代長篇小說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路程與困境。我們在探究原因的基礎上,一方面,可以對茅盾的小說創作,進行一番合理的再認識與評價;另一方面,通過分析茅盾未竟長篇創作這一典型事例,探視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中的某些重要現象,從而對這一現象做整體的感知與把握。
一、未完成:作為一種“現象”
從文學文本的角度來講,茅盾長篇小說的未完成首先表現在作品本身的殘缺不全。茅盾的長篇小說大都有構思清晰且較為完整的社會生活內容,盡管這些內容都沒有按作者的計劃得以實現,但其呈現主題的意圖是明顯的。如未完成的長篇《虹》,作者想通過梅女士來展現她“從一個嬌生慣養的小姐的狷介的性格發展而成為堅強的反抗侮辱、壓迫的性格,終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①。從梅女士掙脫舊式婚姻的束縛,走上經濟和人格自主獨立的道路,最終參加五卅運動的經歷來看,茅盾想要表現的這一主題是完整的。再如《第一階段的故事》,作者想通過抗戰中各階層人物的動向,來說明只要指導思想正確且為抗戰服務,那么去武漢和去延安對抗戰來說都是有貢獻的。雖然這部小說依然沒有寫完,成為殘稿,但是從所呈現出的內容上看,小說主題已經表達出來了。相比而言,茅盾在1940年代的兩部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和《鍛煉》由于內容篇幅的限制,沒能充分顯示出作家預設的主題。
由于小說是一種敘事文體,它的藝術審美性決定了它的完整與否應該從文學作品的核心層面,也就是從文學形象層面出發去判定,而不能以主題意蘊的清晰度為標準。就小說而言,它的形象層面包括情節、人物、環境等要素。
故事情節的殘缺和驟停,是茅盾長篇小說未完成現象的一個最鮮明的表征。《虹》的寫作時間是1929年4月到7月,此時茅盾正避難日本。作品塑造了一個沖破封建家庭婚姻,毅然出走尋找自身出路的時代女性梅行素。逃出“柳條籠”的她先后做過瀘州師范學校的教員,惠師長家的家庭教師,最終來到革命中心上海,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為自己尋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終于在五卅運動爆發之際,她毫不猶豫地選擇匯入革命的洪流。小說結尾當梅女士再次來到南京路的游行現場時,游行的主力已經散去,小說到這里突然結束,留給讀者的是一個永遠的殘篇。游行最終去向何處?革命形勢將會如何發展?幾位革命者的命運如何?這些都成了這一殘篇留給我們的迷。關于《虹》的未完成,茅盾的解釋是因為1928年9月的遷居,使得思緒隔斷,他自稱寫作時“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寫小說一氣呵成,中間如果因事擱筆,就好像思緒斷了,要好久才能重續這斷了的思緒”②。
脫稿于1932年12月的《子夜》被認為是茅盾唯一一部完成了的長篇小說,一直以來被奉為中國現代第一部成熟的長篇創作,但從作家最初的寫作計劃上來看,它仍然沒有完成。按茅盾原來的計劃,他要創作一部城市——農村的交響曲,而城市的部分,由《棉紗》《證券》以及《標金》三部曲組成。從《子夜》所描寫的實際內容來看,茅盾只寫出了《標金》這一部分,盡管當時《標金》的提綱與《子夜》有很多不同,但是《子夜》作為城市——農村全景式敘事的預設規模還是留有殘跡的。
1938年4月1日到12月31日連載于香港《立報·言林》的《第一階段的故事》,是茅盾自抗戰以來的第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作品原計劃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寫上海戰時各階層人物的思想和動向,包括資本家、革命家、工人、知識分子等,第二部分寫武漢生活。大量從上海來到武漢的知識分子,一部分去往陜北,另一部分繼續留在武漢從事救亡活動。作品先有一章楔子,講到書中的一些人物已經由上海到達了武漢,而后寫戰時上海不同的人們在戰爭中的種種遭遇。但最終,小說實際上只完成了上海戰爭時期的內容。結尾時仍停留在上海戰爭剛剛結束的階段,圍繞事件和人物展開的幾條情節線索完全沒有收束就戛然而止了。而之前計劃中的楔子,也不得不成了單行本中的“附錄”,因此在最后出單行本時,將題目由《何去何從》改為《第一階段的故事》。茅盾自己對這部未完成作品的解釋是“逐日寫一點發表一點的辦法我既不習慣,而生活經驗之不足又使我在寫作中途愈來愈怯愈煩惱,寫到過半以后,當真有點意興闌珊。”③不僅如此,《立報》的主編薩空了遠赴新疆,而茅盾自己“亦因杜重遠先生之邀,準備離開香港到新疆去教書”④,從此以后,就再也沒有機會將殘稿續上。
1941年夏,茅盾在香港寫了長篇日記體小說《腐蝕》,連載于香港《大眾生活》,作品以國民黨女特務趙惠明為敘述者。趙惠明的日記充滿對特務統治、對男權社會的憤恨和慍怒,可就在讀者期待著她如何“拿出像一個男人似的手腕和面目”⑤來反抗現實時,小說卻結束了。
出版于1943年的《霜葉紅似二月花》,以辛亥革命后的江南一個小縣城為背景,其構思的錯綜與復雜程度絲毫不遜于《子夜》。作品一開始以封建地主張家為中心展開敘事,講述了江南某縣城七個家庭的利益糾葛與人物情感糾葛,但最終小說只是描寫了這些矛盾的存在,并沒有繼續往下發展,除了地主錢良材與鄉紳王伯申所進行的斗爭外,其他線索都沒能充分展開。
1948年的長篇《鍛煉》,是茅盾在中篇小說《走上崗位》的基礎上續寫而成的,原計劃寫五部連貫的長篇,《鍛煉》是其中第一部。“這五部連貫的小說,企圖把從抗戰開始至‘慘勝’前后的八年中的重大政治、經濟、民主與反民主、特務活動與反特務斗爭等等,作個全面的描寫”⑥。但1948年剛寫完第一部,就因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使得寫作計劃中斷,以后再沒有機會續寫。一直到1979年,作家整理舊稿時,續寫了十四、十五兩章,但仍然是部殘稿。《鍛煉》所擇取的題材內容與《第一階段的故事》類似,描寫抗戰初期上海一家機器制造廠遷廠過程中的種種矛盾與斗爭,分為幾條線索,然而圍繞這些線索展開的情節,卻絲毫沒有收束,僅僅止于一些社會現象的提示。
故事情節的不完整,成為茅盾未盡長篇小說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它最直觀地反映出了茅盾長篇小說的未完成現象。同時,故事情節的殘缺和驟停,也導致了小說人物性格與命運未能完整呈現。
人物性格與命運的不完整,是茅盾長篇小說未完成的又一表現。就茅盾作品中涉及的主人公形象序列來說,主要有時代女性、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幾大類,除此之外,也有地主鄉紳、工農階級一類,屬于次要人物。
茅盾對時代女性命運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兩類性格刻畫當中。一是類似于《蝕》三部曲中的靜女士,二是類似于慧女士。依照人物性格的差異,茅盾從社會革命和女性解放的視角出發,對她們的命運進行了不同的書寫,但是直至小說完成時,還是沒有完整地體現出來。
在《第一階段的故事》中,茅盾把對時代女性的書寫視角主要轉移到她們的革命生活中,情感生活相對居于次要的位置。《第一階段的故事》中所涉及的幾位時代女性,諸如潘雪莉、何家琪等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女性,雖然在抗戰爆發后,積極投身到了抗戰工作中,但是她們的思想波動和斗爭,小說沒有交代。
《腐蝕》中的趙惠明,雖然是國民黨特務中的一員,但她同樣是個時代女性。茅盾在表現這一人物的境遇時,相比過去多了幾分冷峻,因為他一再強調趙惠明人格中的個人主義的傾向,她的命運最終如何,茅盾也陷入了深思。作品連載后,有讀者提議:希望結尾能給趙惠明一個自新的機會,因為她畢竟是特務統治中的被侮辱者和被損害者。但同時也有讀者認為不該給趙惠明以自新之路,怕會發生對特務的同情而對他們失去警惕。茅盾雖然接受了前者的要求,但對這樣的結局,他似乎并不滿意,因此,小說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在小昭被害和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后,作品并沒有表現出趙惠明在現實中所經歷的思想轉變。
《霜葉紅似二月花》中的張婉卿不像過去的新女性那樣沉迷于對男性的愛情和對革命虛幻的向往,而是對親友和丈夫都充滿責任感,似乎已經遺忘了自身性別的存在。但正是這樣一個女性,作者卻給她安排了一個性無能的丈夫。這樣的境遇對張婉卿來說,同樣是一種悲劇。在接下來的情節中,張婉卿的人格會如何發展,她的命運又怎樣通過性格來做出選擇,作品沒有交代。
茅盾作品中另一類重要的人物序列是民族資產階級形象,如《子夜》中的吳蓀甫,《第一階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陸和通,《鍛煉》中的嚴仲平、嚴伯謙等。茅盾筆下的民族資產階級形象,大多雄才大略,意氣風發,驕奢淫逸,既有管理者鐵的手腕,又有愛國者血的熱誠,他們想通過實業救國的方式來壯大民族資本,使中國走向富強之路。但是,現實的困境卻不允許他們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一方面,中國的民族資本長期受帝國資本和買辦資本的雙重壓迫;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又讓他們在政治上看不到希望,加之資本家自身的利益訴求,使他們沒能將龐大剩余資本用于再生產,而是玩起了金融投機,最終慘敗⑦。在這種情形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軟弱性都暴露無遺,但是他們接下來的選擇和走向,茅盾始終沒能給出答案,即使在勉力完成的《子夜》當中,茅盾也只是讓斗法失敗后的吳蓀甫逃到了廬山,并沒有預示他將來可能會做出的打算。而其他的資本家形象在作品中只是表現出了資產階級特有的一些性格特征,沒有寫出他們在困境當中的可能性發展。
小說對社會現實和時代環境的反映,可以是一種共時性的橫向截面,也可以是一種歷時性的縱向展現,但無論是橫截面也罷,縱向展現也罷,它在小說中應該有其完整性。但是在茅盾的長篇小說中,我們卻看不到這種完整性的存在。
茅盾小說所展現的社會現實,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已經過去的社會事件的反映,另一種是對正在發展中的社會現實的反映。《虹》本來預計從“五四”寫到大革命時期,算是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但是只寫到五卅運動。這樣一來,以梅女士為中心的革命者的人物群像的人生觀、價值觀的變化趨向就呈現出很大的空白。同時,五卅運動是讀者已知的確定的歷史事件,而人物的命運和情節發展卻是未知的,甚至已經完成的作品篇章也沒有為我們提供出可能性的發展趨向。這就造成了社會時代環境在小說作品中的片段式反映,失去了歷史完整性的意義。《第一階段的故事》雖然完整展現了上海戰爭的驚心動魄,但是作者卻沒有在戰爭結束后,提煉出一種對戰爭或革命中人的本質的把握,將社會環境和人物命運之間的聯系切割開來,弱化了它對表現小說主題意蘊的重要作用。同時,作品忽視了這場戰爭在整個戰爭歷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使文本社會環境的呈現顯得碎片化。《霜葉紅似二月花》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完成社會環境與人物命運之間的融合,但是由于錯綜復雜的矛盾并沒有在有限的篇章內得以充分展開,所以對社會環境的表現始終顯得很薄弱,使這部作品的時代感明顯不如作家的其他作品。《腐蝕》中的日記從1940年9月25日,寫到1941年2月10日,其背景是皖南事變前后。可見,作品完全是以社會事件的發生和結束為結構框架,來體現茅盾用創作反映那一時期社會重大事件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作家沒有展現出主人公趙惠明最終的去向,就使得這一社會背景的意義沒有充分顯現,同時也由于人物命運的不完整而沒有顯示出作品對社會時代環境的認知。
小說敘事中對社會環境和時代環境描寫的碎片化,涉及作品中對時間和空間關系的處理。英國文學批評家埃德溫·繆爾根據小說敘事在處理時間和空間問題上的不同側重將小說分為情節小說、人物小說和戲劇性小說幾大類。其中,戲劇性小說“空間關系相對確定,情節建立在時間中;在人物小說里,時間是假定了的,而情節是在空間上繼續不斷地再分配和改組的一個靜止的模式”⑧。茅盾在寫作之前,都有一個確定的時間段作為反映對象,小說的想象世界主要集中在空間范疇。無論是單線索敘事的《虹》,還是《第一階段的故事》《霜葉紅似二月花》以及《鍛煉》,茅盾都為作品事先設定了相對確定的時間。由此判斷茅盾的長篇小說基本屬于人物小說這一類型,他的長篇不是以講述情節曲折離奇的故事為主要目的,而是要反映在一定社會環境中人物的命運發展,以及人物的行動對社會時代的影響。因此,人物小說的價值和意義是社會性的。茅盾小說即是如此,他的作品在敘事想象方面需要處理的空間關系大于時間關系。然而在處理時間與空間關系的敘述中,茅盾的社會環境描寫呈現出了碎片化的特點。除了長篇《虹》因為是單線索敘事,人物視角的轉換相對較少,因此作品可以在人物所處空間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中,呈現對環境的連貫的而不是碎片的描繪。而《第一階段的故事》則不同,首先,這部小說和《鍛煉》一樣,屬于多線索敘事,并且每一條線索都占有和其他線索同樣的篇幅,人物眾多且互相獨立,在布局方面就給人物所處空間關系的處理上增加了復雜性。因此當空間發生變化時,很容易造成小說時間和空間上節奏的不一致和混亂。其次,由于人物眾多,而且主次關系不分明,導致小說敘事在人物視角的轉化上,往往過于頻繁,造成時間節奏的臃腫和空間布局上的破碎。《第一階段的故事》中頻繁轉換敘述者視角的例子在作品中隨處可見。盡管人物眾多且作品屬于第三人稱敘述,但奇怪的是,茅盾總是把很大一部分敘述故事的權利平均地分配給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打破了小說敘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原有秩序,而在這種多重視角敘述的秩序背后,就是作品中出現支撐小說敘事時間和空間因素的社會時代環境的碎片化。
茅盾小說中社會環境的片段和碎片化現象,映現出茅盾的小說敘事對社會時代與文本關系把握的缺失,同時也是他嘗試全景式反映社會時所做出的努力,只是這種努力并沒有在作品的藝術性上得到良好體現,相反還造成了作品的某些缺陷和不足。
二、未完成:之于茅盾的原因
面對茅盾創作生涯中如此之多的未完成長篇小說,我們不禁要問,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茅盾的寫作能力尚不足以駕馭長篇小說這種文體,還是作家創作時內在動力不足?是其小說題材面對復雜的中國社會的失語呢,還是中國現代文學進程中的必經階段?
茅盾的小說創作,始于他1927年避居上海時創作的《蝕》三部曲,由三個相對獨立的中篇《幻滅》《動搖》《追求》組成。這三部中篇一經發表,便在當時的文壇激起強烈的反響。茅盾小說所選取的背景,一律與時代緊密相連,而作品中所選取的人物形象,更是時代的典型代表,尤其是茅盾對“時代女性”形象的塑造,最能夠體現時代的發展與變革。時代女性是現代社會女性解放思潮的語境中產生的新時代的女性形象群,也是男性對理想革命期待的重要組成部分。她們具有一定的個體意識,同時受社會時代影響又向往革命,這是時代賦予她們的共同點。歷史決定了時代女性的生存必定處于身體與革命的夾縫之中,而茅盾長篇之所以止于殘篇,首先與茅盾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小說主題對象之間的裂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突出體現在時代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蝕》三部曲中的女性經歷了一個尋找個性解放和獨立自我的艱難歷程,然而在此過程中,《蝕》三部曲向我們展示出的,卻是一股頹廢悲觀的調子,沒有指明革命發展的方向,小資產階級情調與革命文學之間產生了令左派詬病的裂痕。茅盾后來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對《幻滅》的闡釋,體現了他執著探索女性解放的艱難之路,與信奉革命文學的時代要求之間的兩難選擇。這樣的兩難也體現在他之后的小說創作中,
《虹》對女主人公梅行素形象的塑造,與茅盾以往任何作品中的時代女性相比,有了更大的進步性,是茅盾對時代女性命運的進一步探索。梅女士不僅能夠在感情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保持相當的獨立人格和難能可貴的自信與清醒,而且她能夠從社會學的角度,為自己的人格解放找到合法性的申說。這一點,是那些從愛情陣戰上敗下來的環小姐們望塵莫及的,也是《蝕》三部曲中的靜女士、慧女士等難以企及的。如果說,女性解放涵蓋了女性的社會性和生理性兩個方面的話,那么,梅女士這一人物則同時獲得了這兩個方面解放的意識。從這一點上說,梅行素是茅盾對時代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要突破。那么,為什么茅盾在表現這樣健全的時代女性的社會生活、情感生活的長篇小說中,會讓它成為一個無法完成的殘篇呢?
我們首先從小說結尾的最后一個情節說起。在五卅運動游行的人群中,茅盾完全可以以梅女士的犧牲來收束全篇,但梅女士沒有犧牲,而是被徐自強救下,這一情節本身,仿佛完成了作者對梅女士命運的一次替換。對一個新時代的革命女性來說,私人的感情生活和集體的革命生活,本該是社會革命的語境下,時代女性應得的報償呢?還是在這二者之間,即使是健全的解放的女性也只能取其一呢?從《虹》這部作品的內容來看,茅盾所預設的答案,應該是前者。
然而,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深入發展,政治也開始了對女性性別的又一次改造。這一次的改造從政治上使女性翻了身,但卻徹底地把女性的性別遺落在了歷史時空當中。個人的解放變成了集體的解放,在集體當中又怎么會有私人的、浪漫的生活的展現空間呢?于是小說中的“革命加戀愛”模式,開始向“革命加親情”或“革命加友情”的維度轉變。但是茅盾所處的創作年代,政治還不足以對女性性別進行如此極端的改造,因此,它所對應的文學話語也注定是如茅盾早期小說所表現的那樣。具體從《虹》這部小說對梅女士的塑造來看,茅盾的女性主義思想,仍然向他早期所發表的那些宣傳婦女解放的文字靠攏,但是他個人的政治理想在經過大革命的洗禮之后,已經趨于無產階級革命理想。
但這并不是說茅盾的女性主義思想沒有趕上或落后于時代和政治的要求,這和他早期小說的創作手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他早期的創作中,一直堅持要客觀地反映現實,對現實進行細致觀察和描摹,“所以說,使他沉迷于揭示新女性性別認同的是他的現實主義需求”⑨。但他似乎低估了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和干預。茅盾曾經也有過對梅女士的集體主義思想的進一步改造,他說:“我本來計劃,梅女士參加了五卅運動,還要參加1927年的大革命”,“甚至于入黨(我預定她到武漢后申請入黨而且被吸收);但這只是形式上是個共產黨員,精神上還是她自己掌握命運,個人勇往直前,不回頭。共產黨員這一稱號,只是涂在梅女士身上的一種‘幻美’”⑩。茅盾的這一段自白,清楚地道出了他所面臨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他意識到梅女士政治思想本該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感到現實中,對梅女士的徹底的個人意識進行改造的艱難。也就是說,即使革命能將梅女士納進共產黨員的陣營,那么她也還是無法忘記自己那充滿肉欲和情欲的誘人的身體。因此,作品中的梅女士最終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者梁剛夫,找到了她的政治認同,但是她的身體和性別的沖動卻沒有找到合理合法的存在。茅盾在這樣的兩難中,沒有選擇用作家一廂情愿的想象去彌合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裂隙,而是用他那寫實的筆觸,真實地反映了時代面貌。因此,當小說發展到她追隨無產階級革命者,同時還未成為一名真正的“黨的女兒”之時,就不得不停下了繼續向前發展的腳步。《虹》這部小說,不多不少也只能寫到這里了。
《虹》的未完成,體現了茅盾對革命中女性解放的浪漫想象和客觀寫實的寫作手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造成這種矛盾的,一方面是茅盾對時代女性所注入的美好期盼;另一方面,則是來自現實革命中女性解放的尷尬處境。正如黃子平所說:“本世紀以來那些終未寫完的長篇小說,反而銘記了我們在天翻地覆的年代里,安身立命的悲劇性掙扎吧。”
和《蝕》三部曲、《虹》中的時代女性相比,《第一階段的故事》中的何小姐等已經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時代女性了。她們雖然生長在新的時代,但是她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淡化了社會革命語境中的女性解放的時代意義,她們應該被稱作“知識女性”。茅盾的這種寫作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將他早期小說中的身體敘事隱匿在了革命敘事或抗戰敘事的背后。這樣的選擇,體現出了茅盾對時代女性書寫的自覺妥協。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不斷占據主流的時代要求下,茅盾做出這樣的轉變,也是他多年關注女性解放道路后得到的沒有答案的答案。
到了《腐蝕》中,茅盾開始了對女性的另一種方式的性別改造。曾經走出家庭的時代女性卻意外地墮落為國民黨特務,沒有完成社會革命時代對女性的要求。到此時,對女性身體欲望的抒發,終于不再是茅盾盡力展現的對象,而是成了批判的對象。無疑,趙惠明是繼梅女士之后又一位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的時代女性,茅盾對趙惠明這一形象的設定,是女性進行身體和革命的雙重表現的回歸,但作家回歸后的視角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作家表現出的是對女性性別意識中欲望彰顯的間接性否定,曾經代表時代、反映著革命動向的時代女性,如今卻成了作家筆下的反面人物。盡管她們依然擁有石膏雕塑般的曼妙身體,但是身體欲望在茅盾的作品中,卻不可逆轉地成了女性性別當中原罪般的存在。在1942年的《霜葉紅似二月花》中,茅盾繼續強化了這樣的認識,對張婉卿形象的塑造,就是一個例子。這一形象回歸了傳統女性的溫柔賢良、持家守業,她身上新女性的特征只保留了干練與膽識,儼然一個男性化了的女資本家。而那個性無能的丈夫,成了對女性身上那蒸騰的肉欲的最大的懲罰。茅盾筆下的正面女性形象,已經徹底從最初的身體敘事中抽離出來,成為身體欲望的贖罪者。但是,茅盾對女性形象建構做出的這一選擇仍然建立在一種悲劇性的描寫當中,無論是趙惠明的沉淪還是張婉卿不得不面對的丈夫,都以悲劇的方式印證在她們的命運之中。可見要在革命中完全消解女性的性別意識和現代小說的身體敘事,對茅盾來說是多么艱難。
經過這一系列的思考、探索與糾葛,最終,在《鍛煉》中,茅盾徹底放棄了對現代社會中時代女性的性別構建。無論是蘇辛佳還是嚴潔修,又重新回到了《第一階段的故事》里所塑造的那類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女性。
茅盾對時代女性形象構建的這一系列轉變,深刻地反映出中國現代文學中性別書寫所走過的道路,也說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對女性性別意識的改造,在茅盾的作品中并沒有完成。最終,對女性命運的書寫,似乎成了茅盾寫作生涯的一塊心病。
茅盾小說未完成的原因,還在于其敘事生成性的缺乏,我們可以從他小說的典型形象的塑造與情節沖突兩個方面來分析。
“生成性”是指事物本身的生命力,也就是對自身生命衍生的能力。這一概念目前被廣泛運用于教育學、心理學等多種研究領域。把生成性運用于小說敘事,賦予小說敘事源于其自身的生命屬性,敘事生成性為小說敘事的延續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小說中,影響敘事生成性的因素包含多個向度,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節沖突的設置是其中很重要的兩個方面。一旦這些因素破壞了小說的敘事生成性,那么必將導致小說敘事無法向前延續。茅盾長篇小說之所以會出現大量殘篇,與他作品的敘事生成性的缺乏有很大關系。
典型形象塑造是茅盾現實主義小說的重要構成部分,它是在典型環境中形成的,兼具了個性與共性的人物形象。人物也被茅盾看作是小說敘事的中心,小說情節的展開應該以人物為中心,因此,如何塑造典型形象,與茅盾小說的敘事生成性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茅盾早期的小說創作一直受自然主義的影響較大,尤其在人物刻畫方面,由于茅盾自身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社會體驗,使他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能夠以一種獨一無二的面貌來生動地反映出時代脈搏在他們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記。而后期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和他早期的人物形象相比,在描寫的方法上有著很大的不同。茅盾早期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是“寫人物就非屢見其人,且作各方面之長期觀察不可”,然后“把最熟悉的真人性格經過綜合、分析,而后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這樣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如靜女士、孫舞陽、梅女士等,其成功不僅在于她們身上聚集了各類時代女性的共性,重要的是,她們還具有典型性格當中為自己所獨有的個性,這樣的個性不一定與階級屬性有關、與社會有關,而是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本該具有的獨一無二的特點。茅盾早期小說中,人物身上所表現出的豐富的細節化描寫、心理描寫,都是有力的證明。在后期創作中,寫資本家,總是老謀深算,自私自利,既有革命性又有先天的軟弱性;太太們庸俗無聊,愛慕虛榮;工人階級勤勞勇敢,富于反抗又忍辱負重。我們似乎很難從典型性格的角度,區分出吳蓀甫、何耀先、嚴仲平之間到底有什么區別,何家琪和蘇辛佳又有什么不同,他們都成了一個階級的代名詞。
茅盾小說人物設置的弊端還表現在,《子夜》以后的作品中,情節敘事始終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心人物,大多數人物只配合事件和情景出現,只是為了說明當時當地的環境中,存在什么、發生了什么。在《鍛煉》中,作者先后分布了六條線索,每條線索都有它的中心人物,但是這些人物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系,他們像走馬燈似的,在一個情節中完成自己的一件事,然后就不見了。普實克就曾經這樣描述茅盾小說中的人物:“所有這些人登了臺亮了相,在某一情節中成為主演者,但他們還沒有完成自己的角色,作者的鏡頭就移開了,我們再也看不到他們了”。《虹》中的惠師長、李無忌,《第一階段的故事》中的工人阿歡一家,《鍛煉》中的趙克久兄妹等,都是這樣的存在。這樣一來,小說情節缺乏很好的人物依托,情節的出現也就只能像一張張幻燈片一樣,失去了敘事性作品所必備的重心。
小說的情節沖突的需要依附于兩點:一是外在事件,在事件中體現出社會的、時代的沖突,以及生活在這樣時代的人們的社會關系、階級關系的沖突;一是人物內心世界的沖突,這種沖突既可以表現在人物與自身的關系,也可以表現在人物與他人或環境的關系當中。而小說的敘事生成性,就以這兩種沖突為依托,只有小說中存在著沖突和矛盾,小說敘事才有其發展的動力。反過來說,如果小說的敘事生成性不足,那么小說情節的推演就只能靠作者一廂情愿的表現社會的愿望了。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小說這種虛構性敘事文體的藝術性難以保證,小說看起來會像一份社會現狀報告一樣,而作為小說情節推動者的人物,也只能是為配合說明社會現象而存在,失去了獨立的美學價值。
這樣的問題在《蝕》三部曲中已初現端倪。尤其是《幻滅》中的一些情節往往失之突兀而顯得有些生硬,反映出作者一廂情愿的主觀意圖對作品情節發展的牽制。相比之下,《虹》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無論情節發展,還是人物性格轉變,都有突出的矛盾沖突做支撐,如梅女士的感情線索與老父親的經濟處境之間的矛盾,結婚后梅女士追求個性解放與薄弱的反抗意志之間的矛盾等。矛盾沖突的設置,不僅有效地推動了故事情節繼續向前發展,為梅女士的選擇出逃做了很好的鋪墊,而且還在沖突中充分展開了梅女士性格中的多側面:反抗和軟弱并行,清醒與短視共存。從茅盾創作的基本情節構思上說,《虹》是很成功的例子。
但是,在《子夜》《第一階段的故事》《腐蝕》以及《鍛煉》中,茅盾并沒有延續《虹》的敘事策略,設置長篇小說所應有的情節沖突。情節沖突的缺乏對小說敘事生成性的弱化,首先體現在人物塑造上。如果主人公的內心處于一種情感、思想都平衡的狀態,那么,他的實際行動將是按部就班的,改變對他來說是沒有必要的。而茅盾后期小說人物塑造的臉譜化,也導致小說情節沖突生成的困難,因為所有人物的一舉一動都顯得那么正常,在社會階級范圍內沒有任何超越階級、超越社會屬性的行為。沒有沖突,小說內容的完整性就失去了落腳點,最后呈現出來的只能是對現實的不完整反映。這樣的缺陷也使讀者對小說的發展沒有了閱讀期待。
茅盾小說前后期敘事策略的轉變背后,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一條脈絡,“與第一個十年強調文學與思想革命的關系、第二個十年更強調文學與無產階級政治、經濟革命的關系的文學思潮演變,有著內在的聯系”。那就是三十年代以后,小說敘述者的身份,由“五四”時期的個人立場敘述,轉化為社會化的、集體化的立腳點。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由表現人性中的私人生活向社會生活的轉變。因此在后來塑造人物的過程中,茅盾所看重的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定律,再加上在缺乏一定的親身經歷和戰爭體驗的情況下,導致敘述者個人化體驗的缺乏。茅盾筆下的人物,不再具有當初鮮明的個性,所有人物的特性被人物的階級、階層性所決定。這樣一來,如何在人物身上注入合理的矛盾沖突,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這樣的文本缺陷,使得茅盾的長篇小說不能夠在表現社會主題的同時,通過人物塑造和情節沖突兩方面的作用,去架構完整的長篇小說。這也體現了茅盾在創作長篇時所面臨的困境與矛盾。
總之,茅盾長篇小說中之所以會出現大量殘篇,與他作品的敘事生成性的缺乏有很大關系。這些未完成作品顯示出茅盾長篇小說在敘事衍生上所缺乏的源自于文學本體的生命力的缺乏,因為,任何一種文學敘事在一開始形成的時候,就具有了脫離于作家主觀愿望之外的獨立生命,而連貫的敘事是經由敘事本身和作家共同完成的。從這些方面,我們看到了茅盾小說文本本身在情節和形象塑造方面的缺陷給小說的完整性所造成的影響。同時,這也是茅盾“主題先行”的創作策略投射在小說敘事結構中的弊端所在。尤其是從《子夜》開始的創作,無一不是作家通過文學形象序列來表現社會主題和革命主題,這與當時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密不可分。《子夜》的寫作就是為了說明“中國并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壓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抗戰爆發后,茅盾的長篇創作又緊緊圍繞著抗戰以及中國革命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展開。《第一階段的故事》寫革命者的何去何從,突出正確的革命思想指導對人們的重要性;《腐蝕》揭露國民黨特務集團的黑暗統治;《霜葉紅似二月花》寫反動勢力雖然暫時氣焰囂張,但是革命力量終究會取得勝利;《鍛煉》揭露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假抗戰的行徑等。
所有的這些社會的、革命的主題,都成了茅盾文學創作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茅盾作為一個現代作家群體中無產階級革命者的代表,他所創作的小說要解決的是證明題,而不是解答題。也就是說,茅盾的作品要做的,是證明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正確性和合理性,而不是要給中國社會開出他自己的藥方。茅盾在社會現象面前,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家自己的獨立思考,這是茅盾殘篇作品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是許多現代作家創作生涯中的實際處境。我們可以這么說,對歷史現實認識的正確與否,并不絕對影響作家創作出完整的長篇小說作品;而作家思考的獨立性,卻可以為作品的完整性提供自圓其說的可能性。盡管在茅盾的早期創作中,也不乏獨立思考的一面,然而這樣的獨立思考卻因為缺乏對革命形勢的“正確”估計而遭到猛烈批判。《從牯嶺到東京》中,茅盾說:“我就不懂為什么像蒼蠅那樣向玻璃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這一年來許多人所呼號吶喊的‘出路’。這出路之差不多成為‘絕路’,現在不是已經證明的很明白”。從這些辯詞中,我們看到的不光是茅盾堅定而單純的革命立場,還有他內心對現實的獨立思考。然而,在后來的作品中,我們只能看到茅盾日益堅定的革命理想,卻看不到茅盾思想的獨立性投射作品的光芒。一直到茅盾晚年在接受法國女作家蘇珊娜·貝爾納的拜訪時,他仍然直言:“因為我沒有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所以就當了作家”,言語中仍然流露出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熱情。但是,這種最大程度的對革命者身份的靠攏,也注定了他作為一個作家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茅盾對革命生活多方面經驗的缺乏,使他筆下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小資產階級或大都會的上流社會中。對革命生活的疏遠也為他理解革命、理解社會時代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他始終“對上流社會的人物比對無產階級的群眾來得熟知”。當作家對現實的思考和認識不能自圓其說時,他的作品也就只能以殘篇作結。
除上述諸多因素外,我們也不能忽略茅盾創作中的一些細節性因素。比如茅盾文學批評水平與創作水平之間的差距,一定程度上顯露出作家本身在書寫重大題材時底氣不足。茅盾理想中的文學應該具有的藝術審美性和社會功利性之間的高度融合的境界,在他的作品中并沒有實現。作為“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最具眼光的一位”,茅盾在審視自己創作中的缺陷和失敗時,會自覺地將他完成作品的必要性大大減弱。這也許正是茅盾對自己文學創作的“寧缺毋濫”的追求。同時也可以說明長篇《子夜》之所以能夠寫完,是因為它是茅盾所有長篇中相對滿意的一部吧。其次,茅盾的長篇小說除少數作品因為篇幅過短(如《霜葉紅似二月花》),導致主題表達不鮮明之外,大多都以明確的社會主題為創作動機,因此,當他在長篇巨制的寫作過程中一旦將主題表達出來了,那么作品本身的完整與不完整,對他個人而言,似乎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另外,在那個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時代,茅盾選擇了通過對民族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生活、思想進行描繪,揭示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這是從反面去闡釋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他生活環境和生活經驗導致他選取這樣的視角來反映社會,同時,也是通過作品對自己進行思想和生活方面的雙重改造,反映出了“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中自我改造的可能性及其積極意義,肯定了已經成為現實中一種巨大力量的革命勢力對于這種自我改造的重大保證作用”。但是,這樣的書寫是否真的能如茅盾所想的那樣?他的大量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創作現象,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部分答案。
三、反思與重估
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是在1930年代開始得以充分發展與成熟的,但是這一成熟,有它極其艱難的一面。雖然這一時期產生了大批量的長篇作品,但同時也包含了大量的未完成長篇。茅盾的創作,作為這一現象最典型的個案,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現代長篇小說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路程與困境。
任何現實都是歷史的結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剛剛走完了它最初的十多個年頭,然而導致長篇小說繁榮的歷程卻遠遠不止這十多年。當我們回溯現代文學的發展時,不難發現,長篇小說的未完成現象早在中國小說和社會革命產生不可阻擋的聯姻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顯現,從曾樸的《孽海花》到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都沒能以完整的篇章示人。彼時中國文學還尚未開始它的現代進程,卻已經為長篇小說創作埋下了殘篇的傳統。一直到現代文學經歷了三十年的發展后,長篇小說的未完成現象仍然像一塊巨大的陰影,籠罩著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天空。
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不斷強化的過程中,文學的審美性對政治權利做出的妥協,是造成這一階段殘篇創作的重要原因。從更早時期的《孽海花》和《新中國未來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小說對理想社會的政治體制的構建,成了中國近現代長篇小說最初的表現對象。緊接著,“五四”文學對人的發現,造就了一批中短篇小說作品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小說家。對人的發現是“五四”文學最大的收獲,但是也可以看到,對于反映大時代的長篇小說這種文體來說,僅僅有對人的發現,還不足以支撐起更為龐大的小說體式。這就導致了那一時期的長篇小說創作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偏枯。隨著社會局勢的變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終于使得“人的發現”的意識自覺與知識分子對理想社會政治體制的建構融為一體,形成了足夠支撐現代長篇小說的時代性,于是就有了《倪煥之》這樣的作品,然而,這部作品對時代性的反映卻不夠本質和全面。隨著現代文學對歷史的把握,對時代性的表現,逐漸成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重要品質和文學傳統。在這一過程中,長篇小說也在一直努力調整著自身的形態來適應時代形勢的變化和革命對文學的要求。作家們紛紛向全景式描寫現實的方向靠近,然而社會革命的發展,中國社會本身的病態畸形,城鄉的差異,東西方文化在中國不同程度的入侵等,都造成了那個動蕩復雜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全景式展現社會的面貌,如何滿足作家主觀上對文學理想的實現,不能不說是中國小說家遇到的難題,因為取任何一個截斷面都很難全面地反映這樣復雜的社會現狀。因此,茅盾在《子夜》的創作過程中,那樣大幅度地刪減框架與題材,可能就是使作品能夠以完整形態示人的不得已的辦法。《子夜》的寫作恰好為我們證實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所面臨的社會歷史與文學表現之間的矛盾。
而那些試圖與政治和社會革命保持一定距離的寫作,本身也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這些作品總在試圖相對審美地反映社會歷史圖景,以審美的方式圖解人生與現實;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本身就是以現代政治為依托,它是社會革命的必然產物。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就必然帶有政治無意識對作品的滲透。那么這些作品是否能夠抱守著脫離政治意識形態侵染的純美學世界呢?答案會是否定的。篇幅較短的小說或許可以在這樣的夾縫中獲得一點生存的空間,但是一旦它們想要擴大自己的存在,就很可能會在這樣的夾縫中被粉碎。
總而言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未盡長篇的現象,是時代和作家,政治和文學,個體與集體等多方面碰撞摩擦所產生的文學的傷疤。正是這些未盡長篇的存在,為我們證明了現代長篇創作在發展過程中,的確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困境,為我們看待文學史的全景圖時,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它不斷召喚著歷史長河中的后來者,以合理想象的方式去填補現代長篇小說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細節。因此,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殘篇創作現象,不僅是對作家個案研究中所要把握的問題,同時,也應該成為現代文學史書寫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就茅盾來說,他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的重大意義,使他成了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子夜》奠定了中國現代長篇的基礎,他所開創的史詩式宏大敘事,成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重要傳統。對茅盾在現代小說發展史上重要地位的肯定貫穿了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才開始對茅盾小說的藝術價值進行質疑。接著這種前所未有的質疑進一步上升到對茅盾文學地位的否定,進而有人提出將他逐出文學史。而這種否定聲音中有一個直接的理由:“茅盾始終沒有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向讀者提供一個完整的藝術世界,沒有哪一部長篇作品能夠讓接受主體獲得充分的藝術感受和體驗,他的個人藝術才能嚴格說來也始終沒有通過長篇小說獲得充分表現”。我們不得不承認,茅盾長篇小說的未完成,無論是給小說本身的思想深度還是藝術價值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從小說所要建構的價值主題上來說,要想使得一部作品能夠呈現出作者所設定的價值主題,那么一個經過小說敘事發展而來的結尾是必不可少的。而未完成的作品,恰恰無法讓作品在面對受眾時呈現出它原有的創作意圖和價值主題,也無法使作者對社會、對人性的思考,達到普通人無法企及的境界。僅僅憑借作者的寫作技巧、篇章結構、思想政治覺悟,以及對社會現實的真實客觀全面的反映,不能顯示出文學作品本應該給讀者的心靈和認識所帶來的強大感染力和震撼力。茅盾長篇小說所匱乏的就是這種思想的深刻和形而上的思考。茅盾曾經在《讀〈地泉〉》一文中提出,一部作品在產生時必須具備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中一個就是“情感地去影響讀者的藝術手腕”,他的這一主張無疑是正確的,體現出茅盾在文學境界方面的見解是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在具體創作中,他自己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盡管茅盾留有多部殘篇,但卻不能無視茅盾小說創作的價值與意義。
首先,對小說時代性的強調。茅盾的小說創作主要表現社會革命,表現現實社會。表現現實社會的哪一方面呢?從茅盾評價魯迅的《吶喊》可見一斑。茅盾充分地肯定了魯迅小說在嚴厲抨擊封建思想上的深刻性,具有“五四”的精神,“然而并沒有反映出‘五四’當時以及以后的刻刻在轉變著的人心”,在所反映的社會層面上有“老中國的暗陬的鄉村,以及生活在這些暗陬的老的中國的兒女們,但是沒有都市中青年們的心的跳動……很遺憾地沒曾反映出彈奏著‘五四’的基調的都市人生”。茅盾反復強調文學對現實的表現的重要性,從中要體現出中國社會的實質內容,同時他又是有選擇地反映社會現實。后來他進一步說,如何選擇社會現實的內容來作為文學表現的題材呢?——“憑那題材的社會意義來抉擇”,這一注解,似乎說明了茅盾選擇將都市作為自己作品的主要表現對象,是因為在他看來,都市人群的生活動向、內心思想,更能深刻地體現出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茅盾對時代性的強調,不僅說明了現代小說反映現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畢其一生的長篇小說創作為我們提出并回答了一個中國現代小說產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為什么現代小說一定要強調時代性。中國革命所帶來的現代政治環境的形成,決定了小說要有時代性。在茅盾看來,現代小說中人物的價值觀是通過時代性來體現的,而體現了時代性的人物,本身就有一種對真理的探尋。因此,現代小說對人物類似傳統小說那種宿命般的書寫自然就淡化了。
其次,通過事件、語言、心理描寫等,全方位地刻畫現實主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對現代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從而突顯了小說文體的虛構性特征,這樣,茅盾的長篇小說完成了小說反映現實社會的時代性與小說虛構性的結合。
茅盾早在《小說月報》時期就提出,客觀的“描寫”在小說創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五四”時期新派和舊派小說共同的弱點在于,就描寫方法而言,他們缺了客觀的態度,就采取的題材而言,他們缺了目的,而茅盾開出的藥方就是西方的自然主義。雖然,事實證明了茅盾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提倡過的自然主義在展現中國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存在多重缺陷,但同時茅盾也受到了自然主義的很多積極的影響,如強調創作小說時要精于調查分析社會現象,對人物形象的全方位刻畫,將人物的內心獨白、日常語言、群聊式語言等結合起來,有時還呈現出復調的氛圍。茅盾小說創作的這一系列努力,從真正意義上突顯了小說文體的虛構性特征,使小說在現代文學建構中具備了獨立的文體品格,從本質上完成了小說反映現實的時代性與小說文體虛構性之間的結合,使中國現代小說展現出全新的發展面貌。
再次,茅盾長篇小說對結構的駕馭,多線索、多視角、全方位展開敘述的長篇寫作策略,實際上是為中國傳統小說與西方小說在長篇結構上的結合,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與嘗試。通常認為茅盾的小說創作受西方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當我們在分析茅盾長篇小說的情節結構時,卻驚訝地發現,茅盾在小說敘事的思維上,完全是傳統的。傳統小說的顯著特點即是情節和人物會隨著講述事件的不同而隨意移動,如《水滸傳》《儒林外史》等,可以從多個側面來展現社會各個層面,使每個人物在單獨的情節中都有成為主人公的可能。這樣的思維在中國傳統繪畫中也有體現,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全景式地展現了汴京以及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和繁榮景象。不同于西方的“焦點透視”,中國繪畫所采用的是“散點透視”的手法,全景式多側面地展現對象。茅盾將傳統小說中的類似散點透視的敘事方式,創造性地置換在了一個全新的現代文學語境中,以達到全景式地反映現實社會的創作意圖,在這一過程中,茅盾又吸收了西方現代小說的描寫方法,通過有效的內心獨白,心理描寫,敘述視角的靈活轉化,在強調小說虛構性的同時又將“時代性”融入這種虛構之中。
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贏得的地位,不僅是由他的長篇創作的突破和貢獻所決定,而且還在于茅盾所選擇的創作策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第一時間反映了剛發生不久的社會歷史事件,盡管這些作品都沒能寫完,但是作家卻能在很大程度上將現實社會的本質融入作品主題進行闡發。由于對當下現實事件的及時反映,使文壇在為他震驚之時不知不覺地就將殘篇現象掩蓋在了作品的社會主題之下,使后來的人們也都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瑕不掩瑜”的事實。這樣看來,文學不過是茅盾介入革命事業時采取的一種方式而已,這與他曾經直言自己對文學事業的不忠誠是相符合的。
我們從茅盾的殘篇現象中看到的,不僅是現代長篇小說進程中經歷的艱難,而且還有作家自身在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局限,亦即作品的美學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損傷。從美學意義上來說,殘篇現象導致小說這種虛構文體的文本斷裂,無論是在情節還是在人物上,文本的不完整就意味著小說所表達的世界觀、價值觀的較大流失。而茅盾面對自己的未完成長篇似乎并不以為然,也沒有像后來的讀者一樣流露出多大的遺憾,這和茅盾的寫作策略分不開,他總是將剛剛過去不久的社會大事件及時地反映出來,先聲奪人,而在茅盾之外我們又很難找到一樣及時、一樣宏大敘事的作品。由此不難看出,最初現代文學史對茅盾的接受,是社會政治意義大于文學的美學意義的。而新時期以來對茅盾的評價之所以會和過去產生如此大的反差,是因為在遠離了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的文化環境中,人們更加注重對文學作品藝術性的接受。然而,一味地脫離歷史情境去做所謂純審美性的評價,又恰恰是最不可能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做出客觀評價的。
以上分析應該看到,茅盾的長篇小說只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的一個階段,并不是我們所期望到達的頂峰,而這個階段對后來文學史的發展又是非常重要的。人們不該忽視歷史語境去評判茅盾長篇小說存在的價值。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長篇小說的未完成作為一種現象,不光意味著文本本身的殘缺不全,在這殘缺不全的文本背后,卻為我們填充了更為完整的文學與社會的時代關系的內涵。雖然茅盾長篇小說的未完成留給我們的是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彌補的損失,但當我們把它作為一種現代小說普遍存在而又獨特的文學現象去看待的時候,就會發現“未完成”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本質的顯現,這些未完成的小說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比那些完整的作品更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而復雜的演變歷程,其在文學史中留下的烙印,與那些完成了的作品同樣具有文學史價值和意義。
注釋
③④茅盾:《茅盾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476頁,第476頁。
⑤茅盾:《茅盾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95頁。
⑥茅盾:《茅盾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43頁。
⑧盧伯克、福斯特、繆爾:《小說美學三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362頁。
⑨劉劍梅:《革命與愛情》,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78頁。
責任編輯 王雪松
The Analysis of Mao Dun’s “Unfinished” Novel
Zhao Xueyong Gao Yar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Mao Dun’s “unfinished”novel, as a “phenomenon”,is very striking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is “unfinished” work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Mao Dun’s cognitive way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and his creative strategie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Mao Dun’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by means of literature.In the period of novels creation,Mao Dun’s works are full of experimental characteristic,not only truly reflecting Mao Dun’s value orientation between usability and aesthetics,and also disclosing the dilemma lying i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The reevaluation of Mao Dun’s novel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history can help to realize the rough and complicated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eeply.
Mao Dun; novels; unfinished phenomenon; reevaluati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2017-02-1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11&ZD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