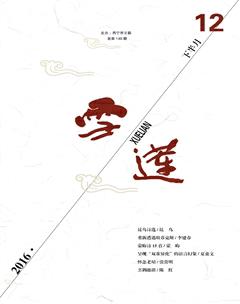蒙晦詩15首
花之惡
是否從地獄中吸滿惡的汁液
由美決定。
上帝隕落大地濺起的花朵。
惡,輪轉著歷史。
難道觀賞者不是神祇抓出的
一把泥土,飽含肉體的灰燼
與死亡的意志?如今滿是塑料和垃圾
又能從中抓出什么?
他摘取,企圖占有,偽飾空虛
他造出假花,以為永恒
他屏住呼吸,聞到惡的香味
命名為美。
詞 語
你們這些黑色的骨頭
葬在一起
為了像一個人
為了有點意思
你們這些瘦鬼魂
相互擁抱又纏在一起
而默不做聲
等待安慰
你們相互訴說的故事
正如詩人的命運
你們只是命運里的
一個意外
(被忽略不計的意外)
而我終不能
把你們一一娶進家門
把你們排列好
像婚榻旁的鞋
而我終不能
安慰你們
卻等待著你們的安撫
在詞語的墓地里
我們是一起喝醉的陌生人
虛構桔皮
為了吃掉這顆桔子
我首先要
虛構桔皮
為了剝掉桔皮
我先要
虛構一棵桔樹
爬上桔樹前
我必須虛構這世界確實
存在果實
以及果實這種說法
現在,我開始虛構秋天
虛構一年的勞作
我開始認為
汗水,曾是太陽流出的熱油
我忍受太陽時
還要忍受風和季候
而這已足夠久
最后,還有想象
還有文明的說辭
或借口
現在我要大口吃下
咀嚼起來
叫桔汁四溢
然后我就吐出
過冬的桔籽
虛構春天
小旅館
這公共枕頭被無數人夢過
無數人,在這里停留
在無數的鼾聲中我們醒來
做過的無數個夢
是同一個
我們躺下我們反復躺下
像女人的抱怨
誰在我們耳邊說過的話
已默默變為鐘
誰伸出的舌頭
在夢以外的地方被閹割
誰在夢,夢到了他們的終點?
于是我們繼續忍耐
所有的空白引誘我們進來
在等待眼睛睜開的時辰里
尋找另一個窗口
我們沒有夢到自己的醒來
卻不斷說著夢話
像窗戶,在風中抱怨過的
是夢話遺忘了我們
而唯有永恒的鼾聲
使一只炸彈的計時器
得以在現實中延續
拔掉燈絲也會閃爍
燈絲,就像等死:
一把旅館鑰匙突然將我們砰然關閉
小教堂
從教堂中走出來,她們是
聚在一起的黑暗的云
投在大地上的一小塊陰影
她們對一切事物說話
而無人聽見,唯有她們在夜晚深處
洗盤子的響聲,在持續響
并在她們日漸空曠的身體中
孕育了回聲
回聲就是她們的信仰
為了聽見一個回答她們的聲音
她們才走進來,敞開
那略有怨恨的心——家庭的門窗
終于坐定,憂慮
卻在刻有孩子身高的木門上
不斷生長,連同她們的信任
幾乎是迷信
每個禮拜日她們都不再回頭
脖頸因仰望變粗——青春
那美好的身體曾使接送她們的男人
總是在門外等候,總是
有一個可讓她們揮霍青春的理由
而此刻,她們不再確信自己的存在?
肥大的臀部尋找長椅
她們不時偷窺那曾有過的人生
上帝!嘹亮但不見身影
唯有聲音,自成堆生銹的樂器
旁證著你的存在?——她們吹奏
男人的罵聲就從床上飛來
而你的存在是否證明了,她們也曾
擁有過愛?幾乎同時
你們虛構彼此,而訓誡
也只是暫時修正了她們的某次發音
奧德修斯
眼前的世界已擁有成熟的語法
修辭感到了必要的羞恥;
當形式那最強大的美學
退讓于對內容的膚淺理解
散文,已經勾引了人類。
因為年輕人像老朽一樣無視隱喻
卻對佩涅洛佩的緋聞保有熱心,
當上百個求婚者顯然都相信
同一個謠言:奧德修斯的死
已成為語言的真實——
成為世界現在的樣子,成為是其所是:
那些平鋪直敘的街道和商店
沒有面孔的背影,也沒有幻覺和回憶
而在詞語之內,我們已經開始流亡
誰讀出,誰就永不歸來。
蜉 蝣
漫長的童年太重,也只是
習得了死亡的傳統。
孩童們已從學校走出
走進情侶的爭吵與遺忘
中年人在低頭走過
而老人停止了皺紋的觸摸。
一切都在準時發生,傍晚的窗內
有人打開了電燈,但無人
能被照亮——此刻
落日在地平線上滾動
一連串意義的句號
人生的祝福應該寫在哪一行?
有人捏起翅膀,覺得太輕;
松手,落下,是因為太重。
白日夢游
攜帶巨大的夢境
你走入人群而默不作聲,
為免眼前的世界發現
秘密正在呼吸。
你走動,偽裝著醒來;
一整條街道的黑傘
同時舉過了頭頂
黑夜彌漫,由內而外。
這是最為漫長的一刻
從夢中越向醒之廣場
如同你要成為非你;
你全力按住到點的鬧鐘
為免死寂的人群發現
亡魂中唯一的生者。
福壽公寓
你不看窗外的雪
只說往事
雪就沒有年齡。
你說一九四九,同窗去了臺灣
幾十年后來信相邀
你年老不便,路途太遠;
你說廣州有一位兄長
一九何年,你去那里住過一個月
只剩嫂嫂還在獨活。
你向訪客講述,對此深信不疑
但無人證實,但無人證實
只有死者們在雪下
呼吸——
那是我們共有的沉默
面朝著喪失,直到白霧呼出
吸滿用掉的時間
換氣之間
屏息,讓大雪停在半空
但,你的老手表在轉動
早晨,晚上
你深知死后也是。
錦母角①
旅行者停止中途觀望樹影與大海
地圖已在此處斷開它的色塊。
這里,所有的緯度都在承認:
自由主要是表象,卻無所顧忌地懲罰著
不自由的人,懲罰他并不認識自己的終點。
此刻的海灘空余海風,只有無肉的海螺在諦聽
風與風聲,究竟哪一個更為殘忍
吹動海鷗的羽毛,迫使那些偉大的翅膀傾斜
當詞語已經無法稱量這個世界
它們叫出了聲——不!
注釋①:錦母角,位于三亞的一個小型半島,是中國大陸架的最南端。
楊柳路疑云(組詩)
影 子
太陽每日高高撅起的臀部不可觸摸。
光
沿輪廓切割我的形象
而沒有眼睛
從地面回顧天空
這影子黑得像一場空難
我原是太陽手中的紙飛機
折疊我,遮住我
然后扔出我,放棄我
當黑暗降臨
誰能歸還我——
獨 居
這里是白色的
只有白色。墻壁
圍著我下雪
而床在做夢:什么時候睡著?
家具廠的油漆味像噩耗傳開
木材們學會燃燒對方
為自己取暖
我獨居在自己之中
用掉一根手指拉住另一根
前往熱愛光明的電燈
代替向日葵的太陽
鎢絲的爐子燒我,只剩影子的碳
我九指
用掉一只手臂
挽住另一只,前往四壁的盡頭
外面有人說話,然后是寂靜
像停電,我獨臂
用掉一只腿跟隨另一只
我來到大街,傾聽無休止的腳步
彈奏黑色的履歷
木材們在街上排成了隊伍
陰謀的言語從電鉆中冒煙
造我們的床:什么時候才能睡著?
四只床腿,四個送葬人
女人們在用高跟鞋釘釘子
那棺材,被釘緊
那影子被釘住,那男人的欲望
那房間那盡頭,那普照倫理的電燈
那,運走未來的車站
一只車輪,更像年輪
測量還未到來的時間
測量我們的思想,沾有多少油污
我獨腿
人們在世界上排成了隊伍
脖子套著繩索,另一頭
抓緊在自己手中,死亡的多米諾骨牌
像頁碼,抓緊在孩子手中
課本夾緊翅膀,鉛筆夾緊尾巴
詞語下滿一生的大雨
淋濕虛構的屋檐,下面
讀我們的頭顱,是斑斕的風箏
一起在虛無中扔出炸彈
用掉上面的嘴唇
親吻下面的嘴唇
用掉一顆牙齒咬住另一顆
用毀滅的,追趕造出的
用人群,減去人
大廈里電梯升向天堂
有一陣雞被扭斷脖子的聲音
在繼續無血地扭動
我獨居
帶剩余的身體尋找床鋪
殘缺的靈魂,像是鬼魂
我是一群,卻像一個
我是一個,卻像半個
一群人在我體內哭,哭我一個人
一輛滿載的公車
從樓下冒著煙繼續前行
直到無人的廢車場
一群人在我身上燒
一群人圍住我,埋葬我
我在另一群中圍住你,埋葬你
可是沒有死,也不像有重生
你活著見不到他們的臉
就像我從未看見自己的眼睛
這里是黑色的
只有黑色,只有黑色
那些眼睛繼續模仿
結核的星星
在煙霧嚎叫的城市一起獨居
橡膠人
代替我們穿上衣服,卻失去
你的塑料頭顱,失去面孔的
被偷吃腦子的模特!
你要我們在燈光下繼續忍受
用同一張臉孔,撞上
一個同樣布料的自己像傳單
是羞恥,定格了我們的關系
是類似使我們安于普世的死亡
那被共用的陳舊太陽
從早晨不斷升起的紅色齒輪上
削去我們多余的五官
延長那影子——死者的繩子!
橡膠人,你用虛構的身姿
站在商店門口,代替人們的情侶
與時代的密謀匆匆媾合
同樣的牙齒,同樣的沉默
繁衍我們無頭的欲望
具有同一種氣味:蠅群的青春
同樣的沉默,同樣的未來
今天只是一個歷史上的舊年份
我們卻要在蜂巢里重溫一生
我要買下你重復的命運:
那模具,棺材!在造你之前造出
虛偽的父母,蜜蜂的國度
我們怎樣從已死定的舊影上
被刻制下來?意志,曾被復制
懸在另一龐大機器中的橡膠碎片兌換出
一個沒有我的我
橡膠人,那是沒有你的你
然后才給你,給你的主人
給你泡沫的生活
你,就繼續用橡膠味的痛苦
言明我們的處境:每換一季
被羞辱地脫光一次,親愛的無頭模特!
一九九二年的雪
窗內的雪總是舊的,窗外
雪人代替著無人——
無人從雪地之外回來,唯有烏鴉棲滿
幼年的屋頂:一九九二
此刻父親的額頭仍在下雪,撞墻聲
仍在傳來,手表內的一圈骨架
陰冷地撥動
已有二十年,年輪又一圈地損壞
可是媽媽,節日已把節日過完
唯有爆竹在雪地辨認它的
殘骸(我撿回的紅里有太陽炸碎的血
在孩子的手中全都變得烏黑)
看哪,雪地的足跡
夏日星夜的底片在季節的更迭中毀滅
迫使我看那隱秘的動蕩——噓,小聲點
媽媽,爸爸去的地方像父親一樣遙遠
混合著成批的父親
被運往南方的廠區,在兩種制度之間
重塑半生:一半鮮紅,一半發黑
早年的雪,已使我陷進父親的腳印
我濕透的鞋子——冷
自最早的富人駛過街頭的大笑中傳來
穿透這選擇,使邏輯無從選擇
我應否在門聲響起時懷疑歸來者:誰
一把黑傘突然撐開,二十年后的陰天
在同一個翻新的火車站下車,已置身
父親舊日的輪廓——那繼承
使命運蓄謀一個繼承者,繼續
將冷卻塔強行塞進窗框;一只用壞的肺
吊上天花而鎢絲閃爍;蝴蝶誤入帝國的呼吸
風暴四起;隔夜的青年在鏡中拉開啤酒
黑太陽正從四點的瞳孔放射血絲
讓刀子指著梨子
脫下臉皮,讓刀柄抓住我的手
刺破邏輯,讓父親劇痛的汗珠從鐘背
滾向我額頭,耳邊的公車已滾動黎明
媽媽,我要結束游戲,可再也回不去
覆雪的道路棲滿烏鴉,燒焦的眼睛盯住我
承認我是它們的主人
沒有一只不是來時的腳印所留下
化雪早已偷換了四月,超市里一場塑料大雪
使閑置的父親從陰暗的盥洗室
走出,陳舊剃刀扔向天空的一刻
光,仍不愿承認自己是一道傷口
午夜的太陽射死了夢,表格中
走出人形之馬,成批的肉體集體老去
木窗剝落的白漆
還原樹木,但不還原時間
我等待童年拆開的鬧鐘此刻突然響起
但一九九二年的雪
仍在下——這雪夜后的荒野
憑空的足跡,是否要對一串命運表示省略
楊柳路疑云
落日銹蝕的螺旋逐漸停止了
轉動。紫的,灰的,深藍的海藻
被絞碎,在天空得到廢棄
我得到你的遺忘有如塔樓:
宿命的影子被拉得長于一生
——那魔鬼的彩虹
彎向地獄,啜飲黑夜的蜜汁
又把晚來的天使唾棄
噢,此刻烏鴉已喊出你的名字
太陽,遮蔽我吧
光芒把我的影子拋棄得更遠
誰能從喜悅之苦中幸免
誰又愛這疑云重重的人生——
【作者簡介】蒙晦,1987年生于江西廬山。2002年開始寫詩,主要作品發表于《活塞》《低岸》《行吟詩人》《詩歌月刊》《詩林》《詩選刊》《創作評譚》等文學雜志及部分年度選本。曾被新浪、搜狐、天涯等網站評為“2008中國80后十大詩人”之一,獲得北京大學未名詩歌獎(2009年)。自印詩集《橡膠人》《在哪里——詩選2007-2016》、《虛線輪廓》(長詩)。現居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