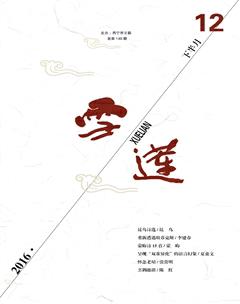劉南山的詩
永 恒
我們一家人坐在院子里,
隨意的聊著天。
母親張著的嘴里可以看見缺失的牙齒,
棕色的臉上掛滿簡單的滿足。
出嫁的姐姐們一左一右,
一個隨意地坐在地上,
越發瘦弱的一個找到了凳子,
還有一個回了婆家沒有加入。
我離她們有2米遠,
我透過陽光觀察著,
一切都有了變化
我們在不斷地變老。
可是父親更明顯的老了,
他的身體在更深的佝僂下去,
垂下來的臉皮
因為擔憂而變得腫脹。
想起我們上一次的聊天,
姐姐們玩耍的孩子比我當時還要小。
他們像我們小時候一樣
并不知道勞動日后會要求得到報酬。
我們在慢慢拉長,
談話的聲音在越發舒緩;
沒有變化的老屋子
即將要被拆除重新再建。
真實的鄉村之夜
我們來看那痛苦的黑夜:
兩顆星星交叉飛行
像戀愛的鴿子
一直向上穿破天空
地上,一些老百姓們在剃頭
依次降低的兩只眼珠
在煙霧、燈泡和被侵略的森林中
轉動鮮活之信息
易碎的紙幣躺進了旁邊
一個小小的木頭盒子
光頭兒童們伸出手撥弄著
彩色的旗手在泰山中笑望
這時,不知何處的蟋蟀們
手拿樹枝劃破了水晶
而一對新人在屋子里潛伏
陶醉于創造的喜悅。
在人類中談論你我他
我和你擁有不同的愛,
仿佛負擔兩個世界的小蟲。
我時常反對你,批判你,
用自身制止高亢的沉默。
這有時會太累:
你會越過自殺,與我合一。
當然,我不是花紋的門窗,
不經受長久的折磨。
雖然,我和你都成為人,
生產后,從宇宙里游回河岸。
相 機
我能找到你嗎?找不到
咔,咔,咔,你藏起來了。一切悄無聲息。
我找不到金屬的銘牌。等等,你在我的影子中?
不,在光中。不會吶喊,又不會呼喚
我會不會因此忘記你?就是這樣
一陣風景從門里流出,如大海閃現。別忘了,那是誰?
走過來,站好,擺出一種期待。噢,多啦A夢
請為我制造現實。你讀到一個玻璃瓶中的書信被記錄。
麻木與知識是一種痛苦。不行,還沒夠,看那個玉米
像一個星球,它圍繞太空被拋到那邊。噢,它落到母親那里去了
母親開始坐起來了,父親在她外面融入明亮的黑暗。但天空呢?
天空飛到了相機之外。
無法對抗的邏輯
到了今天,如果它還是無效的
那么,到死也許還是無效的
我用盡三年刻度的蠟炬
妄圖擺脫生命周邊的冰冷火焰
我絕望地稱它為邏輯的模式
“我”的驕傲,令我不希望成為
任何人希望的模樣
因為那意味著我終將變成 “他”的面孔
我的肉體,我眨眼時的精神活動
無望的墜入黑色的人性深海
仿佛哲學家窒息于維特根斯坦的腦中美杜莎
“你”發明的一切隱喻,早已被他錨定
這也許就是更長久的希緒弗斯,未被美化的
赤裸與猙獰。這也是死亡的另一面
我們終將歸于上帝,連同我們的心血、體驗
與從前我們稱之為“我”的那些感受
由此,我偏愛詩歌,偏愛現代性的寫法
偏愛每一個日常的瑣碎靈光,做個經歷者
既不去立法,也不去闡釋,只是經歷
“我”之為“人”的那一部分如何運作
當渺小者在午后的蝴蝶夢中醒來
再次遇到雨中金黃的博爾赫斯
他奇異的嗓音會訴說“上帝是我們的迷宮
而每一個人只是上帝的精子”
這時,桑塔亞那還會念叨如下格言
“渺小者充滿情趣,偉大者枯燥乏味”
禱 告
我讀著卡瓦菲斯
蘸著他的嗓音,寫下這些詩句:
我眼前是綠色的大海
不知何時,它會變成黑色
這將是我的一生
上帝隨時會賜予生命和死亡
讓我和琴弦一同逝去
而在肉體與精神的兩眼間
我如何對誰談起遠方的詩神
“也許我擲下色子
即可啜飲她眼中的泉源”
我撥動古琴,聽出
絲絲悲傷正在樹木間生長
那是有雨落在無人記得的夜晚
隔壁的那個人
借不來明月為我歌唱
我的眼睛笑著,步子里含著月牙
但你讀懂了我
你說“我會知道
它永遠不會再回來,永遠”
當我停下閱讀
寫下兩篇廣告文案
“如果你要買,我可能不賣”
我就會突然意識到那不是我的生活
我從未見過黑海
不會彈琴,甚至琴弦有幾根
也從未用手觸摸過那溫潤
如果不是傾聽了卡瓦菲斯的傾訴
我可能會更快樂一些
我會滿懷祝福的為你
這樣寫下另一首詩
在工單堆砌的黑字里
我看到賺錢之路
它編織出你的明月微笑
讓小鹿跳躍在音樂里
當然,我會取消你
因別人而垂下的眼瞼
用吻來一步一步
接近你的頭發
那是你彈琴時的節奏
我會取消你被樂器引起的悲傷
我會取消你身上
我可以辨認的生活
雖然從普遍的意義上
那也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
我只能自我欺騙:多一分不是你
少一分也不是你
如果不是彈奏你的嘴唇
我會喜歡你的寂靜
你對現實緘默的一切
我聽說,你家里收藏著幾本圣經
那不信教的我只好禱告
愿上帝賜福,為你
我本希望這首詩的語言遲鈍
回到我在學舌時的笨拙
可惜,情感是輕盈的
而憂傷是輕浮的
【作者簡介】劉南山,1982年生于河北保定雄縣。曾入選2008年柔剛詩歌獎。詩歌隨筆《聲音的饑餓》入選《西部》雜志。有作品入選《存在詩刊》《鋒刃》《終點》等,連續兩屆入選《新詩品》。詩集《真相》《星球儀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