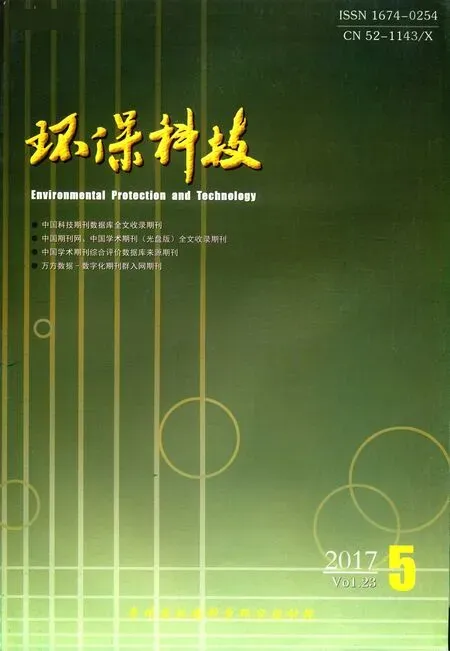企業危險廢物外運處理風險案例分析與探討
王 亮(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節能減排監測中心,天津 300452)
企業危險廢物外運處理風險案例分析與探討
王 亮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節能減排監測中心,天津 300452)
近年來,全國各地危險廢物非法處置的案件頻發,對環境和社會輿論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本文從諸多案件中選取江蘇泰興非法傾倒危廢案作為典型案例,從違法成本、訴訟主體、法律責任、環保意識、賠償方式五個方面對案件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期為企業危險廢物外運處理提供借鑒。
危險廢物;違法成本;訴訟主體;法律責任
1 前言
隨著工業的發展,工業生產過程排放的危險廢物日益增多,其帶來的嚴重環境污染和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使得危險廢物處理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當前我國危險廢物處理價格高昂,引發危廢層層轉包、黑市交易猖獗,大量危廢隨意傾倒和掩埋,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嚴重污染。近兩年,全國各地發生了很多危險廢物非法處置的案件,對環境和社會輿論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針對上述情況,國家先后發布了《危險廢物貯存污染控制標準》(GB18597-2001)[1]、《危險廢物鑒別標準》(GB 5085.1~7 -2007)[2]、《危險廢物鑒別技術規范》(HJ/T 298-2007)[3]、《危險廢物收集、貯存、運輸技術規范》(HJ 2025-2012)[4],并于2016年更新了《國家危險廢物名錄》。
但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危險廢物產量也出現明顯增加。截止2015年,全國危險廢物經營單位核準經營規模達到5263萬噸/年,其中,核準利用規模為4155.1萬噸/年,核準處置規模為982.4萬噸/年。從實際利用處置情況來看,2015年危險廢物實際經營規模為1536萬噸,其中,實際利用量為1096.8萬噸,實際處置量為426.0萬噸。回收利用核準規模的實際利用率為26%,無害化處置核準規模的實際利用率為43%。雖然核準規模遠超危廢產量,但認為由于部分小企業產能利用率不足、核準規模的行業和地區匹配差異導致危廢處置仍有缺口。可見,現有的危險廢物利用處置能力遠不能滿足實際需求,成為環境安全隱患。加之民眾環保意識不斷提升、區域性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行業管理秩序混亂、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問題越發凸顯,這給危險廢物的科學監管帶來了更大的挑戰。
企業作為環保責任主體,無疑是危險廢物環境風險控制最為重要的一環。目前,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能力和資質對產生的危險廢物進行自行處理,基本上都是與外部單位簽訂危險廢物處置合同進行外運處理。從近兩年發生的危險廢物非法處置案件來看,違法行為大多發生在外運處理的環節上。企業環保意識薄弱,貪圖短期經濟效益,對違法成本認識不足,環境危害嚴重性認知不夠,是造成此類案件頻繁發生的主因。鑒于此,本文從諸多案件中選取在中國環保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江蘇泰興非法傾倒危廢案作為典型案例,從違法成本、訴訟主體、法律責任、環保意識、賠償方式五個方面對案件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期為企業危險廢物外運處理提供借鑒,從源頭切實加強危險廢物的科學監管。
2 案例分析
江蘇泰興非法傾倒危廢案是一起由環保組織作原告、檢察院支持起訴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該案件不僅訴訟主體最特殊、訴訟程序最完整,而且涉案被告最多、判賠金額最大,同時探索創新最多、借鑒價值最高。此案一改以往“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勝訴難”的眾口定調,注定將載入環境公益訴訟的史冊,成為里程碑式的破局。這一案件也給環保新形勢下的企業借鑒與警示。
2.1 違法成本
環境污染對社會和人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損害社會福利并且阻礙經濟發展。對這種因環境污染而引起的經濟損失進行評估,統一以貨幣形式來表示各種損害的程度,是科學決策以至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案件在賠償數額上,民事賠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6億。受罰的其中一家企業年利潤只有幾百萬,此次罰金為兩千萬,巨大的數字沖擊,讓企業難以承受。本次民事判決是按照“虛擬治理成本法” 這一環境經濟損益評估方法進行核算,并根據受污染影響區域的環境功能敏感程度,確定一定倍數進行計算。該案虛擬治理成本為3660萬元,但要使環境恢復到受污染之前的狀態,需要的費用遠大于虛擬治理成本,根據受污染河流的敏感程度確定的系數為4.5倍,最終罰金確定為3660萬元乘以4.5的系數,即1.6億余元。企業表示傾倒的廢酸已經隨河水流走,對環境造成的侵害已經消失,不應該承擔如此巨額的賠償。法院認為,此案件造成的是一種長期的、漸進式的污染,短期無法發現,因此采用虛擬治理成本乘以敏感系數的方法進行計算。可見,如果企業將廢物進行合規處理,付出的成本為3660萬元,現在卻需要承擔1.6億的罰金,并且主要責任人面臨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實在得不償失。《環保法》修訂前,我國環保法律和行政法規對環境違法行為的罰款處罰額度,嚴重低于企業的防治污染成本和違法生產收益,“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普遍存在,這導致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引導下,寧可選擇違法,承擔相對輕微的法律責任,也不愿履行防治污染的法定義務。這成為環境違法案件頻發、違法排污企業屢罰屢犯的一個重要原因。新環保法及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基本扭轉了“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企業在新的環保形勢下,面臨著刑法的巨大威懾力以及巨額民事賠償的風險,企業必須要重新審視環保的罪罰與收益。
2.2 訴訟主體
此前我國對環境公益訴訟并沒有完備的機制,環保公益訴訟實踐常常遭遇“有法可依”但“有法難依”的窘境。不少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法院均以原告主體不適合為由不予立案。此案一審兩次開庭的攻防激辯中,雙方就“環保聯合會作為社會組織是否具有訴訟主體資格”進行了多輪答辯。最終,法院認定泰州市環保聯合會具備啟動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但在以往的類似案件中,沒有明確的主體資格,是否立案,往往取決于當地法院的環保意識、理念,甚至是各種利害關系的考量,社會組織的訴訟主體資格往往不被認可。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環保法[5],對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資格進行了明確界定。新環保法明確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相關社會組織,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同時規定,提起訴訟的社會組織不得通過訴訟牟取利益。新法擴大了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此舉對增強公眾保護環境的意識,樹立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理念,及時發現和制止環境違法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初步統計顯示,基本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將超過300家,主體資格不明將不會再成為環保公益訴訟的門檻。可見,今后通過環境公益訴訟來遏制企業對環保的破壞和損壞將會是一個常態,環境組織用法制化的方式去推動環境保護也將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在新的環保形勢下,寄希望法院對環境污染事件不予立案的僥幸心理必須要摒棄。
2.3 法律責任
受到民事賠償處罰的六家企業認為自身并未直接向江中傾倒廢物,而是委托銷售給其他企業,存在的僅為合同買賣關系,對非法傾倒并不知情,也沒有指使他人進行傾倒,因此對于造成水體污染沒有因果關系。為此,在庭上就“企業排污與環境受損之間有無因果關系”展開激烈辯論。六家企業以1元每噸的價格將廢物賣給其他企業,并給予20~50元/噸不等的補貼。接收廢物的企業并無處理危險廢物的資質和經營許可證,因此自己不會對廢物進行處理,而廢物無害化處理需要700~1700元/噸不等,更不可能自掏腰包進行處理。可見,六家企業與接收方簽訂買賣合同,只是為了規避責任,主觀上存在放任對方的行為。因此,最終法院認為這六家企業明知接收方沒有處置能力還進行補貼銷售,這不僅給四家貿易公司提供了污染源,客觀上使其獲得了非法利益,是造成環境污染的直接原因,其銷售行為和污染構成了因果關系,應當做出賠償。可見,企業在對危險廢物進行外運處理時,是需要承擔相應法律義務的,決不能在明知對方不具備處理資質和能力的情況下簽訂買賣或者接收處理合同。此外,交由具有資質的單位進行處理時,也需要嚴格審查接收方的處理資質、經營許可證、處理能力等,以免在環境事件發生后承擔連帶責任。
2.4 環保意識
在媒體對涉案企業的相關人員進行采訪時,有一個細節值得深思。受訪者認為這種做法在前幾年司空見慣,往江中傾倒廢物就像生活中倒垃圾,掃地倒灰一樣平常,沒想到這次居然會面臨2~5年的刑期和1.6億的天價賠償。這些想法與涉案企業環保觀念的淡薄不無關系。隨著當下環境狀況日益惡化,公眾對環境問題帶來的健康問題日益關注,新環保法及相關法律相繼出臺,企業面對新形勢、新法,必須理清思路、調整思維,才能更好地適應新形勢、新局面,否則就會像此案中的企業一樣面臨法律的制裁、天價的賠償以及社會對其企業責任缺失的譴責。
2.5 賠償方式
此案的二審判決中寫道,40%的賠償款可以延期一年支付,如果企業在一年內建造了廢酸處理設施,可以將建造費抵扣這40%的賠償款。法院認為廢物在市場上的無序流動,必然是被傾倒,因此,通過源頭上減少廢物的無序流動量,也就減少了環境污染的風險。對于這樣的處罰調整,是為引導和鼓勵企業主動實施環保技術改造,更能起到司法的引導作用。如果能起到控制污染風險,預防環境污染的作用,這個判決更有意義。可見,目前司法對于環保案件不僅從重從嚴處罰,而且也在探索其判罰的創新性,加強司法的引導力。
3 結語
危險廢物非法處置案件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案件說明當下環保執法力度和處罰力度不斷加強,社會組織采用法制手段通過環境公益訴訟來遏制企業對環保的破壞和損壞也必發展成為一種常態。對于企業而言,只有加強環保意識,踐行社會責任,切實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并且要對廢棄物接收處置單位做好監管,才能牢牢把握環保工作主動權。反之,若造成環境污染事件,必將帶來嚴重的環境風險和社會風險,結果必然是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
除此之外,面對日趨嚴厲的環保法律法規監管,企業在危險廢物管理中盡到環保責任和義務的同時,還需要在將管理延伸到與自身簽訂危險廢物處理合同的第三方企業,以規避可能的連帶責任。如嚴格審查危險廢物處理單位的資質范圍是否覆蓋企業危險廢物產生類別,接收單位資質證書是否在有效期內,接收單位處理能力是否滿足危險廢物產生量需求,運輸單位是否滿足危險廢物運輸的資質和能力等。對于行政執法部門而言,制定出更加有針對性的危險廢物管理的法律法規,以明晰各方責任、量化賠償數額、優化賠償方式,在今后的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切實嚴厲科學地管控好危險廢物這一廣受關注的環境風險。
[1] GB 18597-2001 危險廢物貯存污染控制標準 [S].
[2] GB 5085.1~7 -2007 危險廢物鑒別標準 [S].
[3] HJ/T 298-2007 危險廢物鑒別技術規范 [S].
[4] HJ 2025-2012 危險廢物收集、貯存、運輸技術規范 [S].
[5]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Z]. 2014-04-24.
Acasestudyonrisksofenterprisefortransportinganddisposalofhazardouswastes
Wang Lia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entre of CNOOC, Tianjin 300452, China)
In recent years, illegal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has been seen frequently, which has imposed a serious adverse effects on both environment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is paper, a typical case of illegal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in Taixing, Jiangsu Provicne is chosen for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ith respect to unlawful cost, litigation subject, legal liability,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mpensation metho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concerning hazardous waste transport and disposal.
hazardous waste; unlawful cost; litigation subject; legal liability
X705
A
2017-08-14; 2017-09-21修回
王亮(1984-),男,碩士研究生,環保工程師,主要從事環境監測與評價工作。E-mail: wangliang3@cnoo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