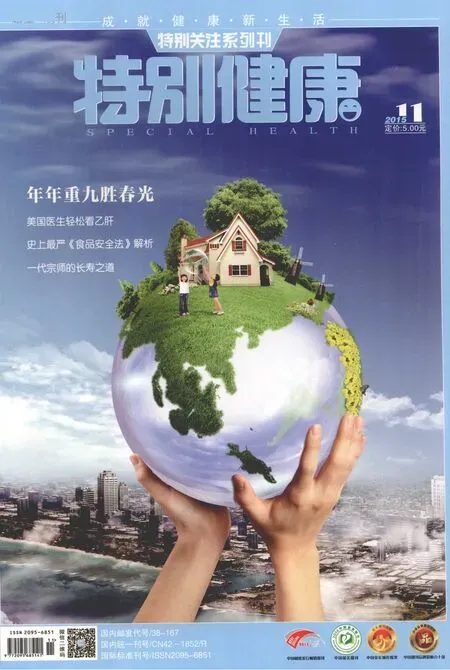買不起新藥可能是福氣
◎何裕民

進口抗癌藥在國內十分昂貴,一片規格為250毫克的艾瑞莎在美國售價為10.3美元,可到了國內,這種藥竟達到了500元人民幣每片的高價。“格列衛”一盒120粒,可以吃一個月,但要開銷2.4萬元。治療頭頸部鱗癌、大腸癌的“愛必妥”,一個月要6萬到8萬元,也很貴。
那些剛研發出來的“新藥”,已炒成“天價”。對于老百姓而言,新藥或許只是一個“買不起”的希望。
有位結腸癌患者,確診時并無轉移,卻因身份特殊,身價過億,8個多月時間用去200多萬元,最后多臟器受損,來我這里求救,但為時已晚,拖了1個多月去世。他的死,讓人扼腕!此人遍請良醫,用盡世上最貴的西藥,每日2500元,照用不誤;中藥也吃,起初是吃每日近400元一劑的“好藥”,用時配合用一種奇貴無比的所謂抗癌之物,又是每日幾百元,最后卻是多臟器受損衰竭、死于肝腎衰竭之惡果!這也許是個典型,然而類似的1年半載用掉50萬~60萬元,最后保不住命的經常可見,其原因很值得深思。
癌癥治療與康復中,存在著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經濟條件好,社會地位高的,大部分治療效果很差,花盡巨款,遍尋名醫,最終常早早撒手人寰;經濟條件差,社會地位低的,一般無錢也沒有特別的求治欲望,這一階層中除部分中老年人可長期帶癌生存外,其生存期也大多短于一般人群。
活得相對最長,康復相對最好的是中間一段。經濟條件一般可以,文化層次與社會地位均屬中等的,他們既能接受一般需花費偏高的治療,又不可能無休止地到處尋覓良醫和“好藥”。不能說心理沒有波動,但也不像達官貴人、商界巨賈那樣失落感巨大。
不得不說,對于新藥,有時候“買不起”也是種“福氣”。一方面,新藥的療效有待臨床考證,未必那么保險;另一方面,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人們對于治療用藥會再三思量,理性分析,謹慎決定,不易出現“過度治療”的情況,無意間避免了不必要的耗損。
對于腫瘤治療,除了手術、放化療、抗癌藥就沒其它了?當然不是。
有的患者逃離大醫院,回歸自然,康復得很好;有的患者,回到工作崗位,融入社會群體,病灶縮小了;有的患者,放松心情,享受當下,活得很好。人的身心是一體的,我們可以先讓自己的心情愉悅起來,精神氣就會好很多,身體也會跟著好起來。加之適度的運動、飲食和生活方式上的調整,配合適當的治療,就能更好地康復。
須謹記,藥不是萬能的,更遑論是一種新藥,腫瘤的康復絕對不單單是因為藥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和適度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