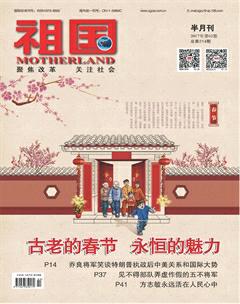試分析微信公眾平臺新聞傳播的正負效應
微信在當前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騰訊公司于公布的《2016年中期報告》,截至2016年6月,微信及其海外版 WeChat (之后在本文中僅稱微信)的月活躍賬戶達到了8.06億。根據2015年數據,有86.2%用戶年齡在18至36歲之間(當時月活躍賬戶約7億),鑒于微信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及華人華僑中使用,根據我國人口總量和年齡分布推算,這代表著,在18至36歲區間段,幾乎人手有一個以上微信號。從來沒有一個以手機APP為主打的軟件,與人們的生活結合得如此緊密。微信在當前,不僅僅是一個手機軟件,也從一個方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微信成為了人們社交、娛樂、生活中的一種常用的工具,對于部分用戶來說,可以稱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種與人們生活密切關聯,具有龐大的用戶群的手持終端軟件,不可避免的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微信公眾號新聞傳播的特點
(一)平臺的開放性
當前微信平臺的公眾號的申請十分簡便,筆者自己即關注過一些僅有數十粉絲的個人微信公眾號。筆者在寫作這篇文章之前,曾花費約半小時,通過網絡提供了相關資料后,即申請了一個訂閱號,也就是說,隨便一個有正當身份的人都可以申請訂閱號,這也是公眾號在數年內迅速飆升至二千萬的原因之一。
(二)傳播的廣泛性
微信平臺是作為一個社交平臺存在的,在其登陸手機平臺之初,就定位為一個跨平臺、跨終端的APP。其添加好友方式有從騰訊QQ、手機通訊錄兩個群體添加方式,另有按號碼查詢、朋友推薦、搜附近的人等個別添加模式。而微信公眾平臺的新聞推送,不僅可以直接送達到關注該平臺的用戶的手機上,而且可以通過私信、群消息和朋友圈進行再次轉發及多次轉發。
二、微信公眾號平臺新聞傳播的正效應
(一)擴大了新聞的受眾面,拓展了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方式
當前有八億多微信活躍用戶,這是國內同網絡平臺用戶最多的一個群體。根據美國人斯坦利·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gram)實驗得出的六度空間理論,在美國任意兩個陌生人之間經過少于六個人的中間介紹,即可認識,并進行物品傳遞。在微信平臺這一新事物之下,消息的轉發近乎于零成本,如果一條消息有足夠價值,可以認為無論其第一次推送給幾個人,都有機會經過層層轉發傳送至所有用戶。在這種情況下新聞有了新的載體和傳播方式。當前,中國的傳統媒體幾乎都開設了微信的公眾號,用以進行作為傳統手段——報紙及廣播電視的擴展和延伸,更有一部分作為直接與用戶進行溝通的手段,以致于當前有一個特有名詞來形容這一過程,即線下交流。
(二)引發了有素質的個人與團體深度參與新聞傳播與評論
原本僅僅作為普通受眾的微信用戶,通過微信公眾號,也成為了新聞報道和評論的參與者。部分有自己觀點見解的受眾,通過評價這一功能,參與到了新聞的評論之中,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見解。普通受眾的參與感的增強,也使用戶對于新聞媒體有了一種特殊的歸屬感。而且,配合微信支付功能,微信公眾號的運營者,可以通過“贊賞”這一功能接收到讀者的金錢鼓勵,而前文提到那位擁有175萬粉絲的公眾號運營者,每天可以收到數百次“贊賞”,每次的“贊賞”金額在1元和256元之間。
(三)提供了相對精準的新聞服務
微信公眾號的多樣性給予了讀者更多的選擇余地,通過在朋友圈或者朋友推薦,來發現更多的新聞資訊來源,經過反復的關注與解除關注,就能從大量的信息中,篩選出自己關注,與自己的理念相統一的公眾號,作為長期關注的對象。由于資訊號微信公眾平臺每天只能推送一次消息,而且大多資訊微信號僅由一個人或少量人運營,所以精力和知識基礎的限制,也要求作者必須審慎地選擇新聞種類和來源。新聞傳播主體與讀者的雙向選擇,在微信平臺上得到了最直接的體現。
三、微信公眾號平臺新聞傳播的負效應
(一)部分公眾號運維人員缺乏新聞從業人員應有的素養
利益的驅使,使微信號的運營主體,往往會關注于微信公眾號的粉絲量,于是部分運營者一切以吸引眼珠為導向就不足為怪了。在新聞選取上,娛樂化的傾向比較明顯。即使是非娛樂性的新聞內容,往往也采用一些不很適宜的編排手段。在微信平臺上往往出現一些具有性暗示的題目,并且以一張具有挑逗意味的圖片作為封面,而實際上,內容卻是一條家庭或社會類的新聞。由于微信朋友圈的開放性,據微信官方公布,有近百分之二十的未成年用戶,而這樣的導向,明顯是不合適出現在公眾視野的。但如果以不良信息相關法律來對其進行規范,又失之過嚴。更重要的是,這種傾向開始由微信微博等,向傳統媒體擴散。
(二)新聞同質化影響傳播效率
由于大部分公眾號并無采編的機構,傳播的大多為二手資料。所以在網絡語言甚至日常語言中,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詞就是“刷屏”。一個公眾的事件的發生,微信群,朋友圈中,馬上就會出現各種公眾號的鏈接,題目不一樣,內容往往相似。前一段時間楊絳先生辭世,筆者有232位好友的微信朋友圈中,共出現了43條相關消息。其中17條在題目中,出現了《我們仨》。雖然個人對于楊先生的辭世覺得是中國文化界的又一大損失,然而,被資訊轟炸后,實在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違和感。
(三)話語權的單向性
在微信公眾平臺上,是有讀者的評論功能的,似乎可以評論的微信公眾平臺,應該能夠獲取一個較為客觀的讀者反應。但是這僅限于運營者看到,而讀者看到的評論,是由運營者經過篩選的。據筆者個人的使用體驗來看,能夠在前臺反饋給觀眾的,都是正面的評價,負面的評價基本僅限于調侃類的。這種虛偽的話語權平等,對于讀者的引導性是很嚴重的。
(四)平臺自身的局限
微信本身是進入商業動作的,微信公眾號平臺也是一種可以獲利的行為,其獲利行為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出租廣告位,二是讀者直接的“贊賞”。從本質上來說,它仍然應作為一種商業運營的形式來對待。在這種運作中,不免會出現片面追求點擊率的行為。而且由于平臺的開放性,也給了虛假片面的消息、低俗信息一個迅速流傳的渠道。而對于微信公眾號的監管,卻缺乏一個合適的尺度以及有效的監管方式。
參考文獻:
[1]丹尼斯·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M].崔保國,李琨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田耘.微信公眾號影響力排行榜[J].互聯網周刊,2014,(65).
[3]肖麗娜.微信公眾平臺:新聞傳播變革的又一個機遇[J].新聞研究導刊,2015,(09).
(作者簡介:孫吉,遼寧廣告職業學院,研究方向:新聞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