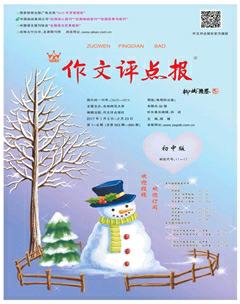桑梓的厄運
初中語文教材有南宋大詩人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一首,末兩句“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極富童趣和田園風情。但時至今日,范成大隱居的蘇州西南郊“石湖書院”附近的農村,再也難覓桑樹的蹤影,古時宅院周圍遍植喬木桑樹的習俗已徹底改變。究其原因,卻是漢語的語言迷信造成的,完全是非理性的因素。
古人稱故鄉為“桑梓”,“桑”是農家首選的綠化樹種,因為它有養蠶的功用而屬于生產的一部分,故農業又稱“農桑”。《詩經》中有“無折我樹桑”的詩句;《孟子·梁惠王上》中明白地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桑樹在古代社會的地位可想而知。其次,桑木又以質地堅硬而成為上好木料,又因諧音“喪”而常用于喪事。《儀禮·士喪禮》中“鬈笄用桑”鄭玄釋曰:“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現代學者聞一多的《釋桑》中也有寫到:“古者行喪禮器用多以桑為之。”
漢人祖先心懷開闊,既不因“桑”與“喪”諧音而忌諱,反而因桑樹貢獻大而視為吉祥物。《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劉備房舍東南角籬笆上有高五尺大桑樹,“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晉武帝為將軍時曾植桑一株,歷時悠久,枝葉繁盛,亦被視為瑞兆。后陸機、傅咸、潘尼有賦頌桑,潘尼《桑樹賦》有“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啟茲”的頌辭。直到元代,桑樹仍是吉祥物。元曲《鐘離春智勇定齊》劇中仍以桑木梳作禮品,并從梳子功能方面理解其好處:“休看這桑木梳小可,它能理萬法。”
明代諧音迷信大行其道,桑的聯想開始變異。《智囊全集·王戎》說:“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自后大小男女凡七喪,夢椹化喪,明用其雅。”從此之后,桑樹由貴族淪落為棄兒,被逐出了農家宅院。張中行《留夢集·戶外的樹》:“家鄉習慣,院里不種桑樹、柳樹,推想是桑與‘喪同音,柳與‘花容易合伙,使人想到香艷以及水性楊花吧。”青年作家劉慶邦《月光依舊》:“葉新榮想起老家的說法:‘門前不栽桑,屋后不栽柳,院子里不栽鬼拍手。所謂鬼拍手指的就是楊樹。”二位說的是河北、河南兩省的民俗,其他地區也多如此。但養蠶用的地桑不受歧視,不過桑園也大都在村子外面,盡量遠離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