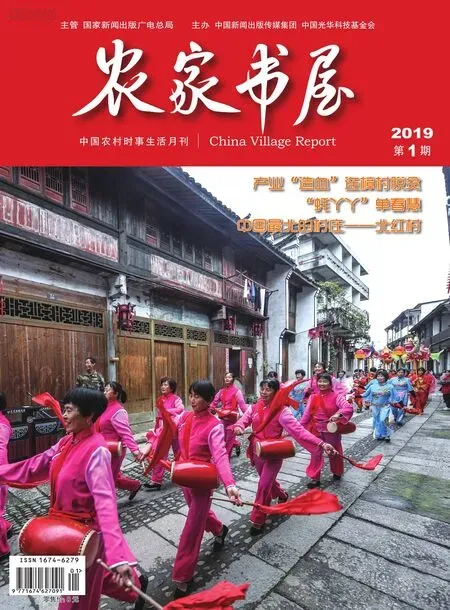母親手中的年鞋
劉賢虎

作為中國傳統(tǒng)習(xí)俗精髓載體的春節(jié),隨著經(jīng)濟(jì)社會的發(fā)展每年都有新的變化。但是,無論世事如何變化,永遠(yuǎn)難忘母親那雙縫制年鞋的手。
我小時候生活在農(nóng)村,那時家里只有兩盞煤油燈:一盞是出行時的手提馬燈,另一盞用來家用照明。這兩盞燈貫穿著我童年的所有記憶,而母親在燈下縫制年鞋的身影是我記憶中最溫暖的畫面。
母親出身地主家庭,是遠(yuǎn)近聞名的大家閨秀,不僅端莊賢良還心靈手巧,只要她見過的人,不用去丈量身高,看一眼就可以做出一雙合腳的布鞋。
在老家,幾乎所有人會做布鞋,但能做出母親那樣完美的并不多。因此,每到過年,村里的嬸娘們都會聚集在我家,讓母親手把手教她們做好看的布鞋。母親做的布鞋,以燈芯絨的最佳,男鞋大都是灰色或者褐色的面料,女鞋面料是紅色或者紫紅色;孩子的鞋則會在鞋口沿了一圈黑色的絨線。
我們家有七口人,母親每年至少要做20多雙鞋,每人各有一雙冬鞋和過春節(jié)時穿的過年鞋。平時,勤儉的母親把一些零碎的布料和一些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洗凈晾干收起來。農(nóng)閑時,再用麥粉調(diào)制成漿糊把布頭層層鋪開,按照布頭的形狀拼接,一層層鋪平一層層涂漿,反復(fù)鋪著涂著,一層又一層,母親叫它千層底。之后,母親采下園子里的蘇麻,把蘇麻的絲搓成麻繩,留著納鞋用。母親說,用蘇麻繩納的鞋底,結(jié)實而牢固,不管怎么穿都不會破底,而且走路很穩(wěn)當(dāng)。
每年冬月,母親就找出搓好的麻繩,把提前糊好的千層底也拿出來,然后根據(jù)大小剪鞋樣,剪鞋樣的原料是在竹林中找來竹子的包殼。母親還會給我3分錢,讓我買一根大針和一個頂針,做鞋子時用。
做鞋時,母親坐在院落的墻角,腳邊放著一個竹籃子,一邊曬太陽一邊和鄰居的嬸娘們聊天,然后靠著頂針納鞋底,縫一針要拉一個大弧線,“哧啦、哧拉”的響聲如同小夜曲,每縫一針都要用頂針頂一下針眼,然后用力地拔,拔一下就把針放在頭發(fā)里擦一下。小時候,我不明白這樣擦一下的用意,后來才知道,擦一下頭發(fā)的油性,針不膩,容易拉出來。
母親縫制的鞋底不管是橫行還是斜行,都如一個直線,針腳細(xì)細(xì)密密,勻勻稱稱,母親將她的愛都縫進(jìn)這一針一線中,橫平豎直都表達(dá)了她對子女們的深愛。很多個冬月和臘月的晚上,我總能看到昏暗的煤油燈下,母親低頭彎腰專注縫鞋的樣子……那時候,我總在想母親的手怎么不怕痛?長大了才明白,母親做鞋時那雙酸痛的手,表達(dá)了一份沉甸甸的愛,正因為她無懼繁瑣的制作,才有我們過年走出家門時蹦蹦跳跳的新布鞋穿。
我是穿著母親的手工布鞋長大的。鞋底與鞋面都夾有綿花,腳一穿進(jìn)去,軟軟的,暖暖的,這軟暖的感覺溫暖了整個年,也蔓延至內(nèi)心深處……
如今,人們已經(jīng)不再習(xí)慣穿布鞋了,而我年邁的母親再不能給我們納千層底做布鞋了。已經(jīng)20年沒有穿過布鞋的我,現(xiàn)在想來,母親做鞋的含義,或許是希望我們踏踏實實走路,老老實實做人。
又到了穿新衣新鞋的時候,但我再也無法獲得一雙飽含著母愛、溫暖樸實的布鞋。那一雙雙千層底的布鞋已隨著遠(yuǎn)去的煤油燈,承載著我今生無法釋懷的記憶遠(yuǎn)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