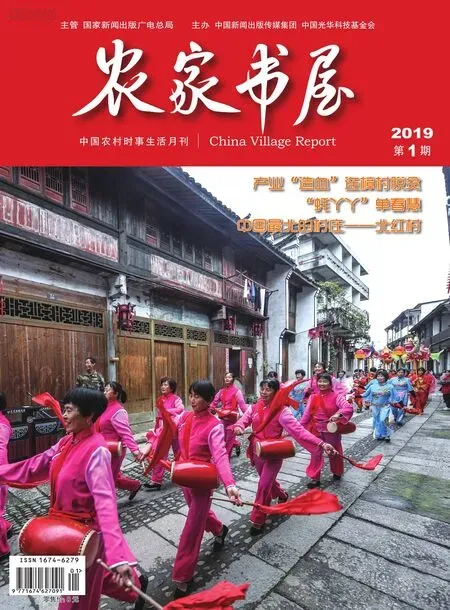消失的村莊
瓦力

《望春風》是1933年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一首臺灣歌曲,數十年來,被許多歌手演繹過。這首意境優美的歌曲描寫的是少女思春的場景,作家格非在小說《望春風》里將它移植為自己對故鄉的眷戀和思念。
小說《望春風》講的是一個鄉村消失的故事。這種消失不僅僅是從地理形態上,更重要的是依附其中的鄉村文明。這種消失的表現是前一輩老人的離世以及后代的遠離,整個村莊因為拆遷建廠未定而荒蕪。我們在雋永流暢的文字里體會著作者這種彷徨無奈、傷感厚重的鄉愁。
作者將故事安置在幾十年悠長的歷史長河中,以第一視角凝視著一個個人物的生長、成熟以及消失。如同在廣場欣賞煙花一般,一束束火花點燃、騰飛、展開、熄滅,除了給觀眾一聲聲驚嘆外,更多的是曲終人散的惆悵。作者離去的背影,成為這個故事以及這個消失的鄉村最好的注腳。
盡管作者全書中沒有提到這種消失的原因,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中窺見一斑。首先,桃花源思維在外來人帶來的異地文化面前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是緩慢變化的,更表現為固步自封、安于現狀與社會階層地位、結構變化的抗爭;其次,因果論和宿命論在解釋社會變革中涌現的新鮮事物時越發蒼白無力,傳統的儒家思維和以佛教為主體的宗教意識,經常遇到難以辯解的難題,這種困惑動搖著賴以生存的傳統文明的基礎;最重要的是現代化進程沖擊著每個人的內心,展現出對比之前生活更加富裕與文明的渴求,人性的追名逐利是各種匪夷所思行為最好的解釋。這三種原因相互糾纏,逐漸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評判標準,最終讓讀者認為,消失的村莊其實是大家一步一步放棄和淘汰的。書中描寫了一個典型,當禮平拿著五十萬解決糾紛時,受益者自覺地放棄了當初為他們出頭的人。
許多讀者對本書后半段的設置不太滿意,從結構以及與前半段對比,后半段確實顯得急促簡單,但我覺得這樣更加突出了前半段的深厚沉重。作者用更多的筆墨來敘說與懷念。其意圖很明顯:當這種消失無法避免的時候,村人的命運重要但不關鍵。更可能的是,作者是在有意忽視與村莊沒有太多關聯的事,這樣更能反映出作者想表達的立場。
村莊的消失意味著最初存封于內心的美好的湮滅。主人公最后“回歸”意識的覺醒代表著一些鄉愁濃厚的人的初衷和愿景。盡管這種愿景的實現是不真實的。我們傳統文化意識里強調著“葉落歸根”和“魂歸故里”,但這種文明的喪失使得“根”和“故里”僅僅是地理位置的不遷移而已。事實上,“我們早回不去了”。書中的“我”每一次換工作,都是離村莊更近一點,最后干脆和春琴搬到當初父親在村里自殺的地方居住,這種倔強的回歸方式更襯托出現實中的無奈。
相對于肉身的回歸,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回望。這也是作者創作、表達意圖的初衷。他在接受讀書報采訪時曾說:“我的世界觀是農民的世界觀,我的身上有很多農民的特質。在過去,我以農民的身份為恥,總是希望洗掉這個身份。以前,如果有人罵我鄉巴佬,我一定會被激怒。這種自卑的感覺一直存在。也就是說,我希望通過知識積累,通過學習,變成城市人。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作為農民的過往成為我值得珍視的財富。在一個普通的農民身上,你不僅可以看到鄉村生活的全部印記,甚至還能找到整個鄉村文明在農民身上的凝聚和投影。”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鄉村文明在沒有找到維持和繼承方式的前提下,類似更多的村莊會消失在地理以及心靈上。
“我朝東邊望了望,我朝南邊望了望,我朝西邊望了望,我朝北邊望了望。只有春風在那里吹著。”這種類似于“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失落是國人在社會劇烈變革中精神家園迷失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