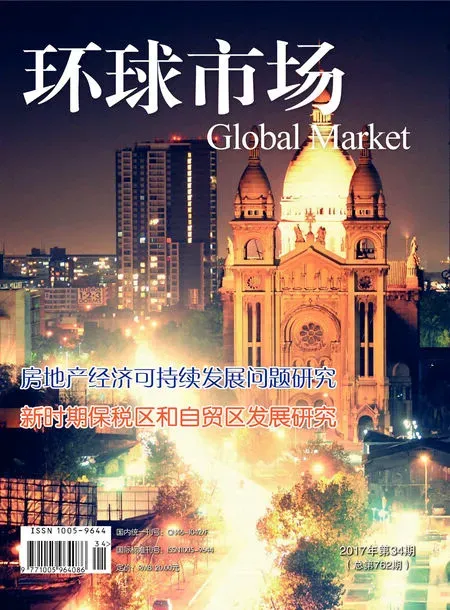TPP磋商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的研究
任子英
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
1. TPP的概述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源于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四國在 2005 年 7 月簽訂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該協議于2006年5月正式生效,經過數年多輪的談判,該協定各方終于在2015年10月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就TPP達成了基本共識。
1.1 TPP的主要內容
TPP作為一個高標準的區域貿易協定,由正文、附件、雙邊換文和獨立解釋組成,正文共分30章,除傳統議題外還設計大量的非傳統議題,其主要內容大概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知識產權化、勞動合作、農業、電子商務和國有企業條款等方面。吳澗生。
其中知識產權條款一直以來都是談判的重點,具有全面化、美國化、超前化的特點,梁意(2015)以TPP知識產權草案為視角,論“超TRIPS”邊境措施及其合法性問題。[1]宋錫祥、周聖(2016)介紹了TPP最終文本對商標權的規定,指出其最新規定充實了執法部分的內容,對于我國有關法律的建設具有警示作用。[2]謝青鐵(2016)以TPP知識產權章節中的專利條款為研究對象,分析了TPP專利規則在制藥及生物技術領域和其對各締約國以及全球專利水平的影響。[3]
1.2 TPP的特征
TPP被譽為“21世紀黃金規則”,姜躍春(2014)總結出TPP具有高端設計、美國主導、區域組織化動向三個主要特征。[4]林桂軍、任靚(2016)指出,TPP提出的規則有八個“新”,即采用負面清單開放模式、對外資實行全面國民待遇、政府采購、勞動權利和環境、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等。[5]
1.3 TPP的戰略意圖
國內外學者大多將TPP和TTIP看成是美國總體經貿戰略的“一體兩枝”,認為兩者戰略意圖更多的是為了制衡中國的影響力,削弱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重塑國際經貿規則,主導全球多邊貿易體系。
國內方面,李文韜(2014)指出了美國權力控制TPP談判擴容的動因,即鞏固亞太地區政治經濟主導權、引導未來“制度建設”的趨勢以及對中國、俄羅斯等亞太競爭勢力的制約壓力。[6]
國外方面,Eric Yong Joong Lee(2015)指出了TPP作為美國在G2系統下的戰略聯盟計劃的法律和政治意圖,其成立的戰略意圖及主要目的是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維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7]
2. TPP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關于TPP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國內外研究的重點,TPP談判一方面會阻礙中國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又會激發中國發展潛力,國內外學者的分析大體可以分為理論研究、實證研究兩個研究角度進行研究。
2.1 理論研究
TPP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的理論分析主要是指其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李春頂(2014)認為,中國的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將不可避免地受到 TPP 協議達成的沖擊,因為通過“貿易轉移效應”,區域化自由貿易協定有利于區域內的“貿易創造”,而“貿易轉移”會對區域外的國家和地區產生非正面效應。[8]
Majchrowska El?bieta(2014)在其文章中指出了TPP在當今世界貿易發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對亞太地區意義更為重大,TPP協議對于成員國尤其是美國會產生貿易創造效應,但是對于非成員國產生貿易轉移效應尤其是對中國。[9]
2.2 實證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實證分析主要運用一般均衡模型、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和出口相似度指數(SI)以及引力模型方法來研究。
其中一般均衡模型運用最多,鄭昭陽、劉晨陽(2016)都是通過GTAP模型將TPP和RCEP對成員國的收益進行對比,得出中國加入TPP將使得GDP增長4.7%,加入RCEP使得GDP增長1.4%,中國應積極參加RCEP和TPP談判。[10]
對于貿易互補性和競爭性的研究,國內學者則更多的采用計算RCA和SI等指數的方式,劉瀾飚、陳明偉(2016)通過對中國與TPP成員國的五大主要出口行業進行RCA、SI等指標的測度,指出,短期內TPP對我國經濟貿易的影響有限,但是長期會通過改寫全球貿易規則對我國產生負面影響。[11]近幾年國內關于引力模型方法的研究主要有汪燦(2015)、潘琳(2016)等,由于其需要的數據比較多,而且計算過程所占的篇幅比較多,所以主要是學術論文采用了這一方法進行研究。
在國外方面,主要是采用了一般均衡模型和引力模型的研究方法。Rahman Mohammad Masudur 和 AraLailaArjuman(2015)運用一般均衡模型驗證了指出當中國、印度等國不加入時將會產生消極的影響,[12]Juyoung.Takayama和Shino(2016)運用一般均衡模型檢驗TPP協議的關稅減免措施對于TPP成員和非TPP成員在貿易流量和貿易福利方面的影響。[13]
3.總結與評述
本文主要選取了近三年的文獻進行了梳理,目前大部分學者關于研究TPP的經濟效應都是基于關稅同盟理論,并且TPP涉及到很多的非傳統議題,關于TPP的主要內容和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應對TPP的挑戰,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重點。TPP對中國的貿易轉移效應大于貿易創造效應,但是這種消極影響比較小。
[1]梁意.論“超TRIPS”邊境措施及其合法性問題—以《TPP知識產權草案》為視角[J].國際商務,2015(02):95-105.
[2]宋錫祥、周聖.TPP最終文本對商標權的規制及其對中國的影響與對策[J].上海大學學報,2016,33(03):1-17.
[3]謝青鐵.《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專利條款研究[J].知識產權,2016(01):127-133.
[4]姜躍春.TPP新特征與日本加入談判的影響[J].亞太經濟,2014(02):121-124.
[5]林桂軍,任靚.TPP協定的特征與新規則[J].國際商務,2016(04):5-15.
[6]李文韜.TPP擴員的復雜性及中國戰略選擇[J].全球治理與區域經濟研究,2014(03):73-79.
[7]Eric Yong Joong Lee.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as a US Strategic Alliance Initiative under the G2 System:Leg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2015(08):323-352.
[8]李春頂.TPP 年底簽署成泡影,TTIP 又會怎樣[J].世界知識,2014(1):25-26.
[9]Majchrowska,El?bieta.Will TPP undermine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J].Research Papers of the Wrocla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2015(12):40-51.
[10]鄭昭陽,劉晨陽.TPP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經濟效果分析[J].亞太經濟,2016(02):51-57.
[11]劉瀾飚,陳明瑋.TPP對中國宏觀經濟與相關產業的影響[J].亞太經濟,2016(01):29-36.
[12]Cheong,Juyoung.Takayama,Shino.A Trade and Welfare Analysis of Tariff Changes Within the TPP[J].B.E.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Policy,2016(16):477-511.
[13]Rahman Mohammad Masudur and AraLailaArjuman.TPP,TTIP and RCEP[J].South Asia Economic Journal,2015,16(01):2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