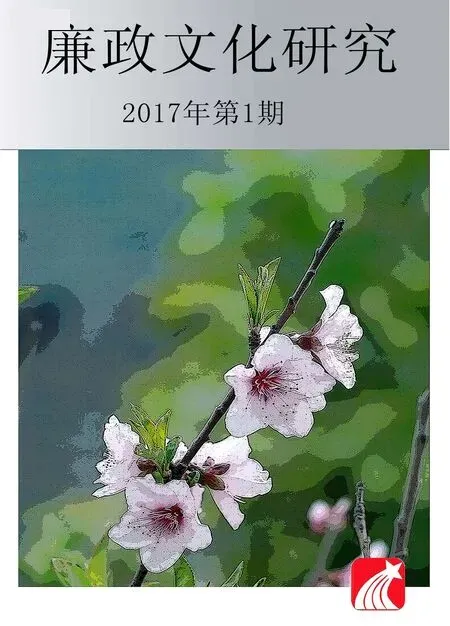高校監督的低效問題
于學強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高校監督的低效問題
于學強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高校腐敗案件增多的原因很多,如高校自身決策、執行與監督的失衡等,其中權力監督不到位是主要原因之一。高校監督的低效問題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教育主管部門監督的低效、高校內部黨委監督的低效、高校內部紀檢監督的低效、高校內部橫向監督的低效、高校內部師生監督的低效。規避高校腐敗案件的發生,必須構建起高效科學的權力運行與監督制約機制,推進高校政治權力的健康運行與政治生態的和諧發展。
高校;權力;監督
近年來,高校腐敗案件不斷增多,高校權力運行與監督制約已經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許多學者開始探索如何構建高校權力制約體系。構建高校權力制約體系的前提是明確高校權力失范情況及原因,以便根據原因來對癥下藥,從而推進高校權力運行的規范化。高校腐敗案件增多的原因很多,如高校自身決策、執行與監督的失衡等,其中權力監督不到位是主要原因之一。依據監督主體的分屬情況,導致高校監督的低效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教育主管部門監督的低效
從監督理論與監督實效來看,來自上級或主管部門的下行監督最有力度。根據權力授受關系,由于這種監督的動力來自于金字塔式授權等級上位,是最具權威性和富有成效的監督。但是,上級或主管部門的有效監督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至少有以下三項:一是有意愿主動開展監督活動;二是有能力掌握監督對象信息;三是有精力處理監督材料。從現有的政治體制分析,首先是上級或主管部門的監督動力不足。雖然他們有意愿開展監督活動,以便推進本系統政治秩序良性發展。但是,由于監督主客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導致這種監督缺乏動力。比如就人事任免來看,根據干部下管一級的規定,我國干部任用過程包括兩大環節:一是由本單位領導集體特別是主要領導的推薦,二是由有干部管理權限的上級或主管部門對這一推薦的認同。如果一個相關領導出現了問題,上級或主管部門對于選用這一領導的認同是否也存在問題?所以,上級或主管部門雖然有監督的意愿,但其主動積極監督的動力仍顯不足。其次是上級或主管部門掌握監督對象的信息不全面。上級或主管部門掌握監督對象的信息基本上靠單向度由下而上的反映,而監督對象反映自身情況長期以來大都本著“報喜不報憂”的原則,在溝通方式既定的條件下,上級或主管部門很難完全掌握監督對象的信息。但是上級或主管部門并非沒有掌握監督對象信息的權力,由于受人力、時間和條件的限制,這種權力行使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從理論上講,上級或主管部門的層次越高、主管面越大,其與監督對象的距離就越遠,能夠有效開展監督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再次是上級或主管部門開展監督的精力不足。由于上級或主管部門監督的對象繁多,沒有足夠的精力全面分析掌控材料。在此情況之下,上級或主管部門的監督往往是滯后、低效的,甚至還存在相當大的空當。據材料顯示:在官員受到調查的案子當中,“有超過70%是來自民眾或其他官員的舉報”[1],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上級或主管部門監督的有效性在實踐層面未必能得以實現。
具體到高校內部,高校權力運行制約與監督機制同樣必須著眼于高校管理體制,尤其是干部選拔任用體制。對于高校而言的下行監督,主要是指來自主管高校的各級政府教育職能部門——教育部與教育廳的監督。長期以來,由于這些主管部門掌管高校發展的重要資源,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政府對高校的管理不僅僅在于政府控制著高校爭奪的各種資源,影響著學校的人事計劃與招生規模,還在于政府時刻監督著高校的權力運行。一方面是政府與高校的某些管理權限尚未完全清晰,權力邊界模糊帶來的是權力運行監督的空當。正如徐明稚、陳雨露等人論及大學章程時指出的,大學章程首先是“明確了政府、學校和社會各自在學校治理中的職責、權利及義務,促進管、辦分離”,“政府管理部門要放權,理順政府與學校的關系,實現‘管辦評分離’”[2]。言外之意就是目前我國政府與高校在治理過程中沒有形成有效的管辦分離機制,仍然存在一些權限交叉和職責不清的具體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有限政府對統攬統包政府的抵制,使政府對高校監督不作為有了合適的解釋。結果是“政府職能的有限性決定了它不可能也沒有精力對高校的管理事無巨細,而以往單一的、以政府為主導的內控型監督反饋模式顯現出缺乏權威性和效率性等弊端”[3]。西方國家如美國大都通過獨立于政府的非官方性的機構監督評估學校,評估結論往往“成為美國各級政府分配資金、社會衡量高等學校水準、學生選擇學校和專業、被評估學校制定活動方針和采取具體措施的重要參考,成為官方行政管理和學校自我管理的重要依據”[4]。國內外高等教育評估具有共同性,因此規避我國政府對高校評估方式的改革,可以吸納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有效經驗。
在政府對高校的監督過程中,教育部和省、直轄市、自治區教育廳是高校的直接管理部門。作為學校的管理部門,這些機構超脫且掌管高校爭奪的各種資源,對于高校權力的制約是最具影響力的,應是最為有力的權力監督機構。但是,由于這些機構本身不為學校內置,雖有權威但管理客體眾多、管理內容龐雜,真正要掌握每一個管理客體的每一項應管理的具體項目也十分困難。所以,教育部主要管控部屬院校,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教育廳對于省屬地方高校的管理也帶有明顯的選擇性,權力配置的不科學導致這些管理部門與學校之間職責不清,更不用說有些機構和部門本身也存在監督缺乏手段與渠道、力量不足甚至不作為的現實,從而導致上級監督的低效性。另一方面,與管理空當對應的是管理過當,“《高等教育法》規定的監督與評估是協調政府管理與高校自主發展的制度保障。但過多的監督、評估不但增加了大學的負擔,而且束縛了大學的手腳,成為政府干預高校辦學自主權的主要方式,迫切需要改革與完善”[5]。
二、高校內部黨委監督的低效
黨的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一直關注的重要課題,這一課題對于繼續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和促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落實關于“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的要求,應“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6]。落實主體責任是黨中央根據我國反腐敗形勢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務,標志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方面的新覺醒。目前,在反腐倡廉建設方面強調黨委“責任”的提法與原來責任制中強調黨委“領導”有著顯著不同,表明黨委是黨風廉政建設的主事方而不是場外人,對于黨風廉政建設出現的問題應主動承擔責任。這一規定有助于黨委專注反腐敗工作重心,從而提升反腐敗斗爭的力度,進一步推進反腐敗斗爭進程。黨委的主體責任是由黨委的領導地位和黨委統一領導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主體定位決定的,具有政治性、全面性和宏觀性。黨委要較好地履行主體責任,就必須進一步強化黨委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領導,確保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向。同時,黨委的領導權力與領導責任是相統一的,黨委領導責任要落到實處就必須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發揮好領導權力,增強自身的主體定位,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風廉政建設的具體工作中。
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書記和校長是黨政一把手,體現某種程度的“雙首長制”,結果往往造成“黨政權力重疊,黨委書記與校長常常因權力行使問題發生磨擦,造成下屬無所適從”[7]。正是由此,多年來,高校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認知與解釋并不統一,從而增加了黨委主體責任履行的難度。如有人認為“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是“領導的不負責、負責的不領導”;有人認為“黨委統一領導學校工作”就是書記統攬一切;也有人認為“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就是學校行政事務都應校長說了算等等。[8]由于認識與解釋方面的問題,導致高校黨委與行政的關系存在不和諧的情況,這是造成高校黨委監督低效的重要原因。實際上,我國《高等教育法》對于高校黨委與行政的關系規定是清晰的:黨委“統一領導學校工作”,校長則“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黨委處于學校的領導核心地位,統一領導學校的各個方面、各項工作。2014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再次明確指出:“黨委書記主持黨委全面工作,負責組織黨委重要活動,協調黨委領導班子成員工作,督促檢查黨委決議貫徹落實,主動協調黨委與校長之間的工作關系,支持校長開展工作”[9]。
實際上,高校的基層黨委作為高校發展的大腦和心臟,其工作方向與效能如何影響到高校的前途與命運。高校基層黨委同其他黨委工作原則方法類似,在決策中強調委員權利,貫徹民主集中制,也倡導黨內的民主監督。但是,高校有其特殊性,除了黨委會以外還有校長辦公會、學術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等體現自身特色的機構團體。如果不能有效規范這些機構團體的職能、職權,明確這些機構團體的定位和運行規則,就不能筑牢大學有序發展、規范發展與和諧發展的基礎,甚至會出現監督失控和權力運行失范現象。有效規范高校各類機構團體的運行規則,最為關鍵的是要抓住“牛鼻子”。在高校組織體系之中黨委仍然是核心,這一委員會中雖然書記是“班長”,但委員會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所以,在高校落實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關鍵是要增強黨委的主體意識。黨委主要責任人包括黨委班子其他成員,在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過程中應有對自身角色、能力、價值和所處工作環境的自覺意識。只有明確黨委主要責任人和班子成員的主體意識,才能夠更大限度地發揮他們作為主體的內在潛能,增強高校黨風廉政建設的實效性。但是,高校權力制約和監督運行與黨委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當制約和監督工作影響高校黨委工作效率與班子和諧時,它會有意無意地偏向效率與和諧。比如,當制約和監督工作影響到班子成員的團結,影響有關部門領導的積極性時,高校黨委很難求得兩全。從它的根本利益出發,他們只能以維護團結、保護積極性為重。
三、高校內部紀檢監督的低效
紀檢監察原本作為專門的監督機構,具有專業化水平較高的特點,本應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廉政建設中扮演更好的角色。但是,當前我國紀檢監察仍然存在一些體制不順暢問題,這也影響了紀檢監察工作的實效性以及民眾對紀檢監察工作的認同度。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接受服從同級黨委政府的領導,還要接受服從上一級紀檢監察部門的領導,但紀檢監察機關作為同級黨委政府的監督機構,主要在被監督的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開展并對同級黨委政府負責。這一體制存在以下四方面問題:一是紀檢監察制度定位不高,紀檢監察機構名義上是同級黨委的兄弟,母體都是同級黨代會,但從實際地位上看它只是同級黨委的附屬物,無法完成對同級黨委權力運行的有效監控。二是紀檢監察制度體系化水平不高,雖然中國存在各種各樣的監督主體,但是這些主體的監督邊界尚未清晰,并且監督的有效配合度不高,沒有形成規范的監督體制和運行機制。三是紀檢監察制度執行不力,紀檢監察機構的執行意識和相關規范制度還比較薄弱,再加上組織力量分散和紀檢監察專職人員相對較少,被監督者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比較差等原因,使得制度執行差強人意。四是紀檢監察自身制度不完善,紀檢監察對自身的監督主體不明確,使得監督者本身可能存在問題。[10]
以上四個方面原因并非并列的,而是有著主次之分。高校紀檢監督低效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紀檢監察體制尚未完善,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源于高校紀檢監察體制——紀委定位不高引發的。在我國,紀檢監察體制設計與實際運行存在事實上的偏差:如紀委與黨委原本都由同級黨代會選舉產生,對黨代會負責。但是,由于黨代會不常任,黨委在實際工作中就成了紀委的領導,比同級紀委高了半格。這樣,事實權力劃分出現不對等,讓同級紀委監督同級黨委就成了不可能。實際上,高校紀檢監察體制就是我國紀檢監察體制的縮影,也帶有這一體制的弊端。無論是在我國古代還是各國共產黨執政時期,都曾意識到監督機構獨立的重要性,但是沒有得到有效貫徹和執行。如我國唐代監察機構分為諫官組織和御史臺兩部分,御史臺成立臺院、殿院、察院分署辦公;宋代還曾設立專職審計機構。[11]列寧時期為了防止腐敗,曾在黨中央建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地方成立各級監察機構,并強調監察機關的地位要相對獨立和具有高度權威性[12],但是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對這一體制進行了變革,改變了列寧的初衷。從監督的一般原理分析,只有建立均衡的權力制約體制,才能實現監督的有效性。所以,讓低半格的紀委監督同級黨委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十八屆六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更加注重監督體系化改革,在國家層面推進監察委員會建設步伐,在某種意義上有利于克服當前紀檢監察體制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高校紀檢監察機構的制約和監督動力機制確實不夠理想:一方面是基于權力配置問題在高校中的體現,即同級紀委實際上成為黨委領導下的一級組織,缺少權力制約與監督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則是作為巡視監督本身具有很大的威懾力,但上級派駐學校的巡視組一般都具有階段性和短期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紀檢監察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能使巡視監督常態化來解決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由于存在監督體制問題,再加上高校紀檢監察部門一般人員配備較弱,這些人員在行使制約與監督權力的時候往往畏首畏腳,擔心交惡主管者,監督不當的問題并不鮮見。“作為黨內監督機構的紀檢部門,因為在黨委的領導之下,無法對黨委形成有效的監督,極個別學校的紀檢部門甚至迷失了自己的使命”[13]。既然高校權力運行制約的難點在于監督權力與被監督權力的不平衡,理順高校監督就應立足于權力的均衡,只有權力均衡才能實現權力制衡。按照權力均衡與制衡的原則配置高校監督權與被監督權,就應通過黨的代表大會的選舉和合法授權,賦予紀委與同級黨委均衡的政治權力,以便形成真正有效的權力制衡體制和機制,同時要進一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代表常任制度。[14]
四、高校內部橫向監督的低效
高校內部橫向監督主要指其內設平行部門(職能機構與院部)或人員間的同級監督。同級監督,俗稱內部監督、平級監督或平行監督,是指依靠本級組織的要素,監督權力運行,降低廉政風險,提升廉政績效的監督體制。在廣義層面上是指對黨內、行政部門內部的履職監督與權力制約,以及同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等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和權力制衡。原本按照制度設計,紀委對于同級黨委的監督也屬于同級監督。但是,基于如上紀委專門監督機構的定位,以及事實上存在的紀委與黨委的地位偏差,這里不再將其放在同級監督中討論二者的關系。這樣,同級監督主要涉及到的是同層級的職能部門之間、同層級的人員之間的相互監督。同級監督相對于上級監督而言,監督主體與監督對象離得近、知得多、看得清;相對于下級而言,監督主體與監督對象地位相當,沒有強勢與弱勢之分;相對于群眾監督而言,他們享有信息與時間方面的體制內優勢。所以,同級監督在掌控對方信息方面具有更為有利的條件,理應是最為便捷、最為直接的監督形式,也是一種富有成效的內部監督。
然而,理論往往與實踐存在較大差距。雖然從理論上講,同級班子或同部門的同僚之間相互了解,應更容易發現相互間的問題與不足,可以通過互評、互議使監控權力沿著正確的方向運行。但是,事實上的權力監督運行有時與理論假設完全不同,現實中這種便捷的同級監督往往因多種因素影響出現相互抵觸的問題。其原因主要是同級部門或干部之間不存在上下級隸屬關系,其相互監督不受權力影響;同級其他領導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情況,其監督缺乏依據;或出于對分管同事的信任和尊重,或者說是“官官相護”。具體到高校內部,黨政間的制衡主要體現在上面分析的書記與校長關系層面,從單純級別分析二者也是同級的,并且按照職責分工應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各自承擔不同的角色與任務,并且在各自履行自己的職責時相互監督,而不是基于爭“老大”地位對來自對方的監督進行抵制。不僅如此,在高校內部的同級監督,更多的是職能部門與二級學院之間以及各自內部平級間的相互監控。一般而言,職能部門對于各二級學院基于各自業務關系的監督要強一些,甚至呈現某種程度的單向性,而反向的監督則比較弱或者根本不存在。各二級學院之間除了涉及到公共利益分配方面的爭議之外,基本上是各自為政,不存在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
實際上,職能部門確實承擔著學校綜合功能中的某一項,而二級學院針對各職能部門,需要完成來自各個職能部門的任務。但是,各二級學院也可以通過正常的信息反饋,督促職能部門改進工作,以進一步推進自身工作和學校工作的協調發展。各學院內部權力運作以及院校關系的權力運作完全可以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相互監督,而不僅僅是為了爭奪資源,并且學校立足自身的發展,也積極主張各學院通過正當競爭去校外爭奪資源,而不只是著眼于校內有限資源的分配與爭搶。至于職能機關及二級學院內部各平級之間的監督,往往出于種種利害關系的平衡,或者互做老好人,或者相互抵制,甚至惡意詆毀,使得監控低效甚至失效。作為同級共同領導從掌控下級的角度來看,雖然希望他們之間相互制衡,但也不希望因權力制衡而導致組織體制效率受到影響,更不希望因同級監督制約權力導致班子團結受到影響。所以,對于如何平衡同級間既相互制約,又不至于因此而影響關系,上級也確實存在一定的難度。
五、高校內部師生監督的低效
“監督作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即政治上的統治力量和職權上的影響、支配力量”[15]。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群眾作為國家的主人,對國家機關特別是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也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監督作為民主的一種體現形式,是建立在尊重每一個個體權利的基礎之上的。主權在民是憲法精神的體現,也是現代民主政治遵循的基本原則,群眾監督最能體現這一精神與原則。群眾監督充分體現每個公民個體的權利,是公民或社會組織對于權力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或領導干部的監督。同時,群眾監督作為民主監督的重要形式,基于監督主體的特殊性使其具有廣泛性、動態性、針對性、隱蔽性等特征。但是,目前我國人民群眾對于憲法所賦予的相應權利并沒有充分享受,或者是沒有很好地運用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當下,群眾監督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群眾的監督意識薄弱,不想監督、不愿監督和不敢監督的心態較為普遍;二是群眾監督的渠道不暢,不能監督和無法監督的制度設計仍然存在。另外,隨著網絡平臺與信息技術手段的不斷發展,群眾在運用這些平臺與手段的過程中又存在生疏性與濫用性。所有這些情況,往往導致了群眾監督的事實缺失。
師生監督是群眾監督在高校內的體現,同樣體現了高校對師生權利的尊重。從高校內部而言,高校各種權力的最終來源是廣大師生的權力,各種權力都應受到來自于廣大師生權利的規約,必須體現在對廣大師生權利的維護與發展方面。所以,無論是書記、校長還是各職能機關、二級學院的領導,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首先應本著對全校師生負責的態度和意識,積極創造條件,讓廣大師生參與到學校的管理過程中來,并且校院管理人員應主動接受全校師生的監督,落實全校師生主人翁的地位。尊重師生的權利是高校民主化管理的重要標志和衡量指標,是貫徹“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精神的重要體現,有利于充分發揮全校師生在權力運行中的監督作用,克服和規避高校中的權力腐敗問題,促進學校的健康發展。另外,高校與社會不同的是,高校中的群眾是富有知識和思想的人,與社會普通民眾相比,他們的監督意識更高,監督手段更成熟,而且更容易主動尋找監督的渠道與路徑。
但是,目前大多數高校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師生員工對權力的制約監督機制。一般而言,高校中教代會、工會作為師生對權力制約監督的重要載體,一般采用教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進行民主監督,學校行政一般采用校務公開的方式接受民主監督。但“不論是教職工代表大會還是校務公開,都是監督事情發生的結果,難以監督事情進行的過程,而且公開的范圍和內容均有一定限制,其民主監督力度有限”。“馬后炮”性質的事后監督問責,雖然也有一定警示功能,但不能從根本上起到預防作用,所以“教代會、工會的民主監督有名無實”[16]。雖然,有些學校的二級學院也開始積極推進教職工大會或教代會制度,但目前這種形式對于推進實質性監督的意義不大。并且當前高校大都沒有形成廣大師生員工能夠制約和監督的信息渠道,也沒有構建廣大師生員工參與制約和監督的平臺,使得廣大師生員工積極參與制約和監督的氛圍受到影響,最終導致廣大師生員工對于學校權力運作與監督基本上處于無視與無奈的兩種境地。隨著中國法治化進程的推進,高校更應走在法治化前列,依法明確學校內部不同事務的決策權,把師生參與確定為重大決策的法定程序。同時,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師生監督權力、家長參與管理、權力陽光運行。[17]
另外,社會監督低效問題也是高校權力腐敗的重要原因。誠如王敏指出的“所有者缺位”致使外部監督虛化,“實踐中普遍存在群眾對干部監督工作參與熱情不高、民主黨派監督的渠道稍顯單一等問題”[18]。一方面,高校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常被認為是“一方凈土”,其高潔的定位往往弱化了社會監督的意識;另一方面,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社會個體,基于其與高校之間的關聯性不強,不能完全掌握高校內部信息,從而導致信息不對稱,弱化了社會監督的能力。
總之,高校腐敗不是因為沒有監督,而是基于各類監督的低效。“當前高校各種廉政監督力量沒有得到有效的整合,難以形成監督合力”,“形不成強大的內在自我約束機制和外在的社會約束機制”[19]。規避高校腐敗案件的發生,必須構建起高效科學的權力運行與監督制約機制,尤其是“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斷改革和完善高校體制機制”[20],推進高校政治權力的健康運行與政治生態的和諧發展。
[1]汪析譯.在中國,揭發者越來越多[N].海峽時報,2012-12-06.
[2]亮出政府和學校“權力清單”[N].中國教育報,2014-03-17.
[3]于文明.中國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體的生成與協調研究 構建現代大學制度的新視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24.
[4]熊衛華.進一步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的障礙分析[J].高教探索,2000(1):26-29.
[5]俞德鵬,侯強.高校自主辦學與法律變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38.
[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
[7]陳杰峰.高校權力運行與民主監督[J].湖南社會科學,2008(6):179-181.
[8]李延保.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與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J].中國高等教育,2008(18):7-10.
[9]中辦:高校必須堅持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EB/OL].(2014-10-15)[2016-11-28].http://news.ifeng.com/a/20141015/4 2211406_0.shtml.
[10]于學強,周浩集.制度視角下紀檢監察工作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4):41-46.
[11]陳光.淺談中國古代監察制度[J].科教導刊,2016(5):181-183.
[12]黃葦町.誰是蘇共的掘墓人[J].決策與信息,2002(1):42-48.
[13]劉獻君,張曉冬,劉皓.高校權力運行制約機制:模式、評價與建議[J].中國高教研究,2013(6):8-14.
[14]魏宏.權力論——權力制約與監督法律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59.
[15]侯志山.論監督的本質特征[J].廉政文化研究,2014(1):35-39.
[16]上海海事大學紀委課題組.建構高校權力運行監督機制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2008(17):67-70.
[17]讓法治融入學校治理每個細節[N].中國教育報,2014-12-08.
[18]王敏.現代大學制度視域下高校干部監督體系的改革[J].河南社會科學,2012(8):69-70.
[19]何等浩.高校廉政監督機制建設初探[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3(3):32-35.
[20]習近平.加強黨對高校的領導[N].北京青年報,2014-12-30.
責任編校 陳 瑤
Low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U Xueqi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Shandong, China)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im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ecision-making,execution,and supervision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in cases of corrup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out of which the absence of supervis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The low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ow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from the five channels as follows:administrative sections,Party committees,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s,parallel supervision,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A highly effective operational mechanism for power and supervision must be structured to facilitate a sound running of political powers and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log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power;supervision
G641
A
1674-9170(2017)01-0051-07
2016-12-13
于學強(1973-),男,山東茌平人,聊城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山東省廉政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聊城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山東省社科重點項目(14bzzj02);聊城大學重點社科項目(32102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