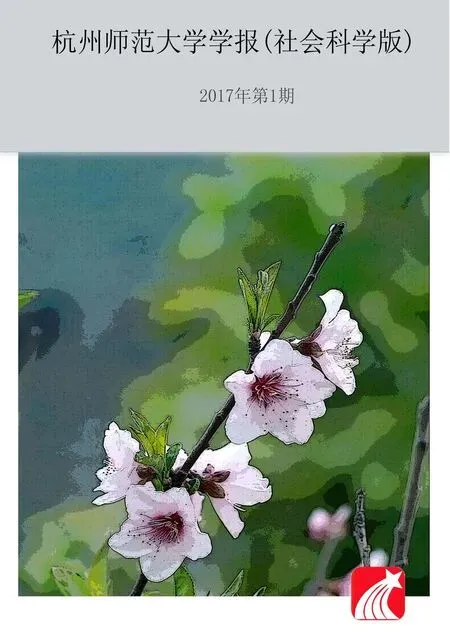遼宋之爭:論真宗朝意識形態層面的角力
——兼論宋代的秦朝觀之轉變
段 宇
(學習院大學 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 日本 東京 1710031)
遼宋之爭:論真宗朝意識形態層面的角力
——兼論宋代的秦朝觀之轉變
段 宇
(學習院大學 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 日本 東京 1710031)
宋真宗在位期間興起的大規模“東封西祀”運動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澶淵之盟以后遼政權試圖通過宣揚自身對秦漢正統的繼承來建構自身合法性,這使得外覺威壓內生緊張的宋政權在對內宣傳中做出了針鋒相對的行為。其措施包括對秦漢進行污名化,并最終在輿論場中形成了政治正確。這最終推動了文化和思想上中華史觀的重新建構,并使得此后學術發生轉向。
宋真宗;意識形態;秦朝觀;遼
北宋真宗時期的政治是宋史研究方面的一個重要的話題。從澶淵之盟的締結到封祀鬧劇的上演,引人矚目的政治事件接連不斷;而真宗本人主導的禮制改革的挫折和士大夫勢力抬頭在有宋一朝的制度建設方面都留下了濃重的印記。這些都極大地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其意義雖極言而不為過。
澶淵之盟的締結對于封祀鬧劇的最終上演,兩次重大政治事件之間具有深刻的關聯,這已經由諸多前輩學者充分地論述了。①如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葛劍雄:《十一世紀初的天書封禪運動》(《讀書》,1995年第11期)、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第3章(稻鄉出版社,1996年)、汪圣鐸:《宋真宗》第4、5章(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4章(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等,均持此種觀點。王瑞來對此的闡述包括,封祀決策的出臺并非真宗皇帝憑私意操弄皇權所達到的結果,而是體現為皇帝在得到士大夫勢力妥協和支持后,權力層所做的共同行為;同時,舉辦封祀的根源在于澶淵之盟締結后,“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一元的中華天下觀受到的強烈沖擊。[1](P.300)《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中的記載可以印證上述判斷。
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夸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后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由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小島毅的評價是“為了恢復和宣揚業已墜地的(真宗自己覺得)皇帝權威”的“系列國家級儀禮”。[2](P.71)而何平立在此基礎上注意到,“‘東封西祀’運動,并非僅僅是以往史論所言對‘澶淵之盟’的滌恥洗辱事件。該運動的目的,不僅在于以盛大規模的封祀禮儀來證明趙宋皇權合法性、合理性和權威性,而且也是禮治社會整合和調適統治階級政治秩序、強化意識形態和構建精神信仰的一場思想運動。”[3]
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轉述蘇頌的話,更加詳盡地談到了興起封祀的政治決策是如何出臺的: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圣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但是,僅僅對史料做出解讀,不加辨別地繼承史料中對于真宗的封祀行為的觀點,這樣形成的對于“封祀”決策的起因的認識是有局限的。固然,由于王欽若的進言,真宗皇帝對宋政權面臨的意識形態危機有了確切了解,甚至可以說是因此而深受刺激,他對于宋政權此時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有著清晰認識當無異議;同時,君臣雙方都對宋遼間的武力對比和宋朝面臨的形勢有所了解,并基于此做出了謹慎的判斷,因此通過對遼進行戰略進攻,以達成軍事勝利來凝聚人心、確保意識形態的做法并未被提上選項。常識上來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辦國家級的典禮的意義能夠與發動戰爭并帶回戰果相提并論;可是,這仍然不意味著國家在直面意識形態危機的時候,舉辦盛大的典禮會是順理成章的選擇。解釋真宗選擇了通過這種國家層面的禮儀行為的思想背景何在,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史料梳理,從中尋找線索;而在厘清這一政治事件內在的邏輯如何演生的同時,在政治史以外的維度來重新解讀這一歷史事件及其影響同樣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一、論澶淵體系下遼的文化競爭行為
關于真宗的封祀行為,早在元代脫脫修《宋史》的時候,就已細致地觀察到其與遼政權之間的關系。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洲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卷八《真宗本紀》)
“契丹故俗”既包含了遼政權繼承了以天命為尊、以得天命為夸耀的天命觀,也包括了禮重游幸這一特點。元人修《遼史》,作《游幸表》,明言“今援司馬遷別書封禪例,列于表”,正是基于對游幸的禮儀作用有所認識。根據上述史料能夠看出,遼政權通過游幸來夸示天命所在、在樹立自身政權合法性方面起到作用。將真宗一手導演的東封西祀和遼政權夸示天命的政治行為兩相比照,二者擁有形式和目的的雙重相似性。這對于遼宋間的“文化競爭”的實態確是明確的提醒。
胡小偉提出了用“文化競爭”一詞來描述這一時期宋遼之間意識形態層面的特殊關系。其研究顯示,宋真宗以封祀的禮儀“夸示外國”擁有充分的證據。一例是景德四年初次舉辦迎接天書的系列典禮時,恰有兩個契丹使節團進駐東京,分別對應著“降神”和“酌獻三清天書”儀式的時機。另一例是舉辦泰山封禪典禮之前,“命都官員外郎孫至遼境上,告以將有事于泰山”。盡力做到了對遼的展示。[4]然而,關于宋遼兩國之間的文化競爭是如何進行的,這一點還需要在利用史料時,在超越宋朝中心觀的前提下做出進一步的分析來顯示。
張耒寫道:“為今中國之患者,西北二虜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5](P.1293)點出了對于宋朝廷而言所謂的外患長期存在,并且即使是在軍事敵對行動依照盟約平息以后依然如此。此處“外患”的真實含義,除了一個與“中央政權”平起平坐的政權出現在“臥榻之側”,造成意識里的中華秩序內在的緊張以外,外在的以文化競爭為形式的壓力也始終存在,不可忽視。長期以來被視作野蠻民族的契丹,在建立遼政權后又是如何在文化領域挑起競爭、讓宋朝君臣花費重大代價迎戰,這是問題所在。
遼太祖接受“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的成規,推行帝制,并詔建孔子廟,保留幽州諸制度。隨著遼太宗滅晉,唐代禮器北歸,宗廟制度也得以完善。“始置太祖廟,歲時祭祀。”宋朝士大夫對此有著較為清楚的了解。《宋史》卷三四〇《蘇頌傳》言遼朝“頗竊典章禮義”。而《遼史》卷五八《儀衛志》里寫道:
王通氏言,舜歲遍四岳,民不告勞,營衛省、征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麾,斥地萬里,經營四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后嗣因之。旄頭豹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跡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
這說明了遼逐步制定典禮的過程。遼太祖建國時期戎馬倥傯,未得集中精力進行國家禮儀方面的建設,被附會為舜一般的行為;而太宗時期開始將意識形態建設工作正規化,并被后代帝王繼承了下來,其意識形態的內容則是“秦皇、漢武之儀文”。
僅僅過了一代,到了遼太宗時期以后,遼國方面的上述工作已取得了高度成效:
至于太宗,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棄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于是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于遼;周、宋按圖更制,乃非故物。遼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即使以現在的學術眼光來審視,也應當承認遼政權所做的這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建設在內涵上與秦漢立國時期所做的意識形態建設有著相當的共通性。“帝號”在統一之初執政合法性宣傳中的重要意義得到了充分重視,領導者的武略和德行方面也作為贏得社會認可的手段加以了宣揚,制造和展開了統一國家的熱望等方面的輿論、還有試圖通過“宗廟”的建設取得對執政權力的認可,[6]這些秦漢開國時期的意識形態建設過程中受到重視的因素,在此時依舊發揮著影響。
另外,本處對于王通言論的引用亦有可玩味之處。王通自稱“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主張以“天命”來判定正統所在,其尊元魏為正統之說飽受爭議。其所提倡固與遼“北朝”地位相匹配,又與作為“契丹故俗”的天命觀相合。有學者指出王通思想在此期間的傳播,可分南北兩大支。[7](P.119)而北方政權對王通思想更為重視,將其視作官方意識形態。宋朝諸儒亦重王通,視為道統中人而張撻伐于史論,如歐陽修作《原正統論》,斥王通之說為“不至之論”。張沛文中有“宋以積弱偏安之國而如此推重帝元魏之王通,豈非咄咄怪事”,[8](P.56)既注意到了現象又覺察了現象包含的理論矛盾,而解釋這種現象歸因為王通《中說》的理論堅實性。隋唐五代釋氏大盛,及宋儒學不免與之爭,為賡續此間儒家道統而不得不重王通,本不足為怪。而從宋儒對于王通的評價來看——部分肯定其學術地位卻做低于以往的人物評價,論短其史論,一意批判——正可推測宋人對于王通的批判態度也有否定遼金正統性的警覺心在起作用。
二、正統觀念層面的抵抗與傳國璽神話破滅
遼所得“帝王文物”里,最有意義的莫過于漢傳國玉璽。《遼史》卷五七《儀衛志》有如下記載:
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歸遼。
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玉,螭紐,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魚鳥篆,子嬰以上漢高祖。王莽篡漢,平皇后投璽殿階,螭角微玷。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權,以歸于魏。魏文帝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往往模擬私制,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圣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于中京。
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
玉印,太宗破晉北歸,得于汴宮,藏隨駕庫。
《遼史》的文字對于漢傳國璽的來源、授受交代甚詳,可以在這段敘述看出遼政權以自己擁有傳國璽這一禮器的名義,將自身緊密地歸入了因璽而得統的歷史王朝之列。于時人影響之深刻自不待言,對外足值夸耀。郝經指出“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9],可以為證。此處“璽之得失”指的是哲宗紹圣五年改元元符。到遼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為題試進士。一者可以明白地看出擁有漢傳國玉璽乃是遼朝主張自身政權合法性的依據;二者可以看出,遼通過表現對傳國璽的重視來主張自身合法性來源于秦漢,這一主張的提出不晚于圣宗開泰十年,即宋真宗天禧五年;三者可以看出遼政權試圖以主張該項依據來建立政權認同感的對象是知識人,亦即參與科舉的士人。
劉浦江注意到了趙宋時期圍繞政權合法性問題的政治文化中傳國璽的地位最終走向“淪落”。[10](P.184)但是關于傳國璽在這一漫長時期是如何淪落,傳國璽被否定的邏輯何在的論述依然有待明晰。解讀宋治下的士人們“集體性地、自覺地”在意識形態領域解構由傳國璽所象征的傳統正統觀這一行為,通過類比西歐史來歸結為這一時期存在一場啟蒙運動的確難免質疑。拙論也正是有意于沿用劉浦江提出的關于政治倫理方面的視角來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
截至真宗朝,遼政權借由宣稱對傳國璽的掌握,在傳統秦漢型正統觀語境下無疑處在優勢,在意識形態方面占據了絕對高地。遼政權通過宣傳戰強化這一優勢,并且與其他針對漢人的諸如經濟方面的優惠相結合,營造了契丹國治下尊儒盛世的景象。這與當時多起士人越境奔遼很可能存在著直接的關系;而非如同之前的研究一樣,把這一時期士人的越境和投效遼政權單純當作宋國在軍事上失敗的結果。[11](P.99)
不斷越境的士人在向宋政權表明著這場起源于澶淵之盟前的意識形態危機的深刻性。而這一時期進行忠節方面的文化建設因刻不容緩而上馬,舉行封祀也被認為是確有提升臣民忠誠的效用。[12]封禪一事最大的效用當在于,彰顯北宋對于圣地泰山的統治,來表明趙宋政權的合法性。這依然可以看作是針對王通思想語境下“中國”定義的行為,意即針對強調“中國之道”的北方政權,宋作為“居中國之地”的政權,具備自身合法性。在遼政權咄咄逼人的宣傳攻勢面前,宋真宗如此做出了強烈而有效的反擊。
士人們對這種大費周章的禮儀表示了抵觸與困惑,表現出一種外在的“天人關系的緊張”,這可能也包括對于陷入對方思想語境的憂慮。同時,面對最初由真宗本人主導的顯露出支絀的國家宣傳,士人們展現出他們在思想上的更多獨立。紹圣改元元符之際,士人們對于所謂傳國璽真偽的否定已經展現了他們對于圍繞著傳國璽、以及其所代表的“天命說”正統觀有了抵觸。李心傳、趙彥衛等人都認為“漢以前璽”毀于漢末董卓之亂正是其例。[13][14]宋金石學大興,圍繞金石相關的研究使得士大夫們形成了全新的關系,他們在國家禮儀方面的話語權得以提升,同時營造了圍繞文物的共同輿論場。圍繞著傳世史料的文本記載和來歷不明的《玉璽圖》等資料,南宋士人對所謂傳國璽傳世系譜做出了共同的解構。
可是真宗不惜強行推動封祀典禮的舉辦,這除了預期在上述意義上能起到瓦解遼國正統性宣傳的用途,也同樣可以解釋為這是試圖在一般民眾之間獲得影響,保持地位——所謂“神道設教”。即使面臨士人們所在的思想界難以被這種表演打動的情狀,真宗并未放棄沿用自身邏輯,堅持在天命歸屬方面在思想界做出全面反擊的姿態,這一期間形成的儒釋道三教的文本都能夠顯示這一點。*典型的研究有山田俊:《北宋·真宗の三教思想について——〈天書〉と〈清靜〉——》、東北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報告》第二十八集(第169~191頁)和中嶋隆蔵:《〈軒轅本紀〉と〈翊聖保徳真君伝〉——北宋真宗時代、読書人層における道教思想的一側面——》,《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研究年報》第五十一號(第57~87頁)。久保田和男:《玉清昭応宮の建造とその炎上:宋真宗から仁宗(劉太后)時代の政治文化の変化によせて》,《都市文化研究》Vol.12(第139-152頁)也有提及。一些時候,真宗皇帝親自布置。秦漢的正統性也是在這場宣傳反擊戰里受到懷疑和打擊。這場反擊的思路在于,如果推翻了秦王朝的所謂的正統,那么北方的對手就算如同他們自己所聲稱的那樣繼承其“正統”,也將毫無意義。如果說對于遼國通過傳國璽構建自身合法性這一事態,宋真宗的態度尚是停留在否定傳國璽真偽性,并未否定其價值的話,比較而言,對于初創玉璽的秦王朝,真宗的態度則是徹底否定其正統性,卻并不在意于否定遼聲稱對其正統性做出繼承這一方面。
三、政治正確下的秦漢觀演變
景德二年,奉宋真宗皇帝敕命,類書《冊府元龜》的編纂工作開始,由王欽若和楊億負責,耗時八年完成。在其中,關于帝王正統性的論述值得注意。該書體例,將歷史上稱帝的人物分為帝王、閏位、僭偽三類,在王朝正統以外詳細地品評了帝王正統。在《帝王部總序》之中,論及秦朝的部分意義深刻:
秦兼天下,獨推五勝,不當正統。
因而將秦王朝與蜀漢、孫吳、南朝宋齊梁陳、東魏、北齊、五代梁一起,置于“閏位”部。該意見的意義不僅在于否定秦王朝的正統地位,還提示了以五行說來標榜正統乃是對于秦朝話語體系的繼承。鑒于該書“區別善惡,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鑒戒”的性質,這代表真宗時期關于歷朝正統問題的官方意見。其意義不僅僅提示了超越歷史的語言窠臼,拋棄五行說來進行正統評判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是為歐陽修的“古今一大文字”[15](P.39)《正統論》的面世鋪平了道路。宋真宗并沒有直接否定五行德運說。實際上在他在位期間,對于宋朝德運的檢討一直不曾衰落,有大中祥符三年張君房進言事、天禧四年謝絳上書事載于史籍,[16](P.2130)其結果是真宗先后以“豈敢驟改”的意見和借兩制議“茲事體大,非容輕議。二臣所請,難以施行”駁回。直接對德運說進行否定有違他的不輕言利害更革的施政原則。
但是改變對于秦王朝的觀念正是所謂另外一個層次上的關懷,換言之這“使得某種政治語言成為可能”,對于秦朝乃至“承秦制”的漢朝做出否定都因此箭在弦上。不僅僅是通過《冊府元龜》的編纂來表明態度,真宗皇帝本人還在咸平四年四月頒布的《論賢良方正制策》中,提到“秦非正統,奚所發明”*見《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十一冊《選舉》一〇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4415頁。原文照錄如下:漢詔賢良,垂三百余載;唐策俊造,懸四十余科。得士者昌,于斯為盛。用能佐佑帝業,焜耀儒風。歷代已來,其道中廢。皇朝開國,復舉而行。朕奉祖宗,不敢失墜,思得天下方聞之士,習先王之法,明當世之務者,以輔朕之不逮。傳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斯則皇帝王霸之異世,其號奚分;步驟馳騖之殊途,其義安在。稱詔之旨,臨御之方,必有始終,存諸典故。加以姬周始之三十六王,劉氏承之二十五帝,受授之端,治理之要,咸當銓次,務究本原。而又周有亂臣,孰為等級;秦非正統,奚所發明。勒燕然之石者,屬于何官?剪陰山之虜者,指于何帥?十代之興亡足數,九州之風俗宜陳。辨六相之后先,論三杰之優劣。淵、騫事業,何以首于四科?衛、霍功名,何以顯于諸將?究元凱之本系,敘周召之世家,述九流之指歸,議五禮之沿革。六經為教,何者急于時?百氏為書,何者合于道?漢朝丞相,孰為社稷之臣?晉室公卿,孰是廊廟之器?天策府之學士,升輔弼者謂誰?凌云閣之功臣,保富貴者有幾?須自李唐既往,朱梁已還,經五代之亂離,見歷朝之陵替。豈以時運之所系,教化之未孚耶?或者為皇家之驅除,開我朝之基祚耶?是宜考載籍之舊說,稽前史之遺文,務釋群疑,咸以書對。。考核該文文體,“秦非正統”作為陳述的交代出現,能反映出真宗皇帝本人在秦是否正統方面直截了當的意見。
受到了權力支撐、由君主提出的這條意見在通過權力編織的毛細管般的網絡向下滲透,發揮著對于言論和思想的規范作用。在福柯看來,這種體現在日常的社會活動中的“規訓性”權力甚至比暴力、酷刑、國家機構、法律制度等更為有效,能讓權力下的每個人都在“權力的注視”下自我審查。[17](P.193)關于“秦非正統”的話語如何貫徹,這在一些事例方面有所體現,似可資參照。
例如此后宋庠寫出《紀年通譜》十二卷,意在區別王朝正閏,其事載《宋史》卷二八四《宋庠傳》,《紀年通譜》書目收入《宋史》卷二百三《藝文二》。原書已佚,考《直齋書錄解題》可以得其大概,其書將帝王的性質分為“正”、“閏”、“偽”、“賊”、“蠻夷”類,起自漢文帝,并未回答秦的正統問題。
另外,秦字在相當多的場合,特別是與儀禮相關的場合相當于被抹去。前述“漢以前璽”[18]的措辭采用是為一例。這與當時秦國=秦代在意義上成為了北方政權的暗喻指代也有關系。
如北宋更早一些的時期成書的《太平御覽》就記載了如下的故事: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筑長城。徒士犯罪,止依鮮卑山,后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效也。
將契丹民族的形象與秦代刑徒聯系在了一起。按《太平御覽》,其出典作《風俗通義》。《風俗通義》漢應劭著,原有二十三卷,今殘十卷。盧文弨、錢大昕、嚴可均等皆有考證。錢大昕《風俗通義逸文》將這條輯為佚文第十六條,乃輯佚中的直錄手法,因其出處唯一而直錄原文。其真實所出似有討論之余地,或仍為宋儒杜撰,而在政治正確以外又反映一種真實的心態。
被暫時放下的秦正統問題最終在此后的正統論論爭中發展為中心問題之一。圍繞這個正統爭議雙方因而可以分為兩派,代表人物分別為歐陽修和章望之。充分的辯論后正統論的學術成果由朱熹集大成,內藤湖南以“朱子綱目出,正統大勢定”來概括。[19](P.308)這可以看作是北宋真宗時代的諸象在思想界最后的波瀾。
四、結語
學術上與“漢學”相對立的“宋學”在東亞思想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宋學肇因于當時政治情勢的緊張,源自宋代的學者們對漢學進行批判的思潮,在當時形成的政治正確下注目實際問題。這使得學術范式發生了轉換,最終確立了獨成體系的全新學問。
長期以來,這一變化的過程被視作作為整體的中國思想史的一個部分,其思想上的淵源被認為是上承隋唐時期,并強調了這樣一個所謂的長期的學風轉變過程中社會的變革和士大夫精神的覺醒的共同作用。如此理解的話,從漢唐以來學風到宋學這一儒學的范式轉換雖源自對實際社會的關心,但是視野依然只是局限在國家的內部和士大夫本人的周圍空間,“內因”被當成了唯一解釋。這對于宋代士大夫的世界觀來說未必不是一種曲解。另外,固然這種解讀如溯“道統”而上,然而道統的建構就是放在宋學的全盛期也未曾自洽。關于唐宋之間學術系譜的解構仍存在著相當的研究盲點。
眾所周知,儒學學術的發展與政治史接觸緊密,在宋開國以來做出了崇文尊儒的表率后更是如此,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來說地位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與之相對應,儒學者為政治行為尋求理論支持的自覺也同步高漲。澶淵之盟以來,趙宋政權追求像漢唐那樣建立世界帝國的政治目標事實上破產,宋國朝野面臨全新的東亞世界,以及隨之加深的意識形態危機。澶淵之盟以前,遼國所做的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的努力造成的影響作為外部因素長期以來被忽視,遼政權以繼承了秦漢的正統來建構自身的合法性,在宣傳戰中處于攻勢,這讓宋國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正是意識形態方面遭遇的危機推動了宋國國內的知識人群體對史觀進行重新建構。除了引人注目的正統論爭以外,一些對于歷史朝代和人物的重新評價也顯示了這場文化轉變的徹底性。作為意識形態斗爭中的政治行為發酵的結果,北宋時期的思想與學術此后也隨著政治上對于“至大無外”的世界帝國路線被拋棄,走向提倡內省的道路。
[1]王瑞來:《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
[2]小島毅:《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何曉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3]何平立:《宋真宗“東封西祀”略論》,《學術月刊》,2015年第2期。
[4]胡小偉:《“天書降神”新議——北宋與契丹的文化競爭》,《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呂祖謙:《宋文鑒》卷九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6]王子今:《秦始皇議定“帝號”與執政合法性宣傳》,《人文雜志》,2016年第2期。
[7]張博泉:《略論金代的儒家思想》,《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5期。
[8]張沛:《“中國”之義——文中子的立身與存心》,Tiziana Lippiello、陳躍紅、Maddalena Barenghi編:LinkingAncientandContemporary:ContinuitiesandDiscontinuitiesinChineseLiterature, Venezia: Ca’ Foscari,2016年。
[9]郝經:《傳國璽論》,《陵川集》卷一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劉浦江:《“五德終始”說之終結——兼論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11]崔瑞德等:《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史衛民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2]路育松:《從天書封祀看宋真宗時期的忠節文化建設》,《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13]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4]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十五,《全宋筆記》第六編第四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15]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16]徐松:《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三冊運歷一之五,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17]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
[1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乙丑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第一冊,東京:平凡社,1992年。
(責任編輯:吳 芳)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iao and Song: On the Ideological Wrestling during Zhenzong Reig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Perception towards Qin Dynasty in Song Dynasty
DUAN Yu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Gakushuin University, Tokyo 171-0031, Japan)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deology of the massed sacrificial rites of “Dong Feng Xi Si” movement,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in Song Dynasty. After the treaty of Chanyuan, the Great Liao tried to claim its legitimacy by preaching its succession to Qin and Han, the heir of original Chinese. This policy triggere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and a drastic reaction from Northern Song to curb the hostile spreading even Song was already suffering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concentrated on stigmatiz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forming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This controversy ultimate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a paradigm shift to the academy.
Emperor Zhenzong in Song Dynasty; ideology; the perception towards Qin; Liao Dynasty
2016-12-21
段宇,日本學習院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宋代學術史、10-13世紀中國思想與國際關系史研究。
K244
A
1674-2338(2017)01-0084-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