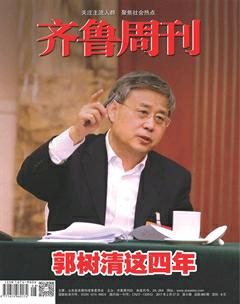用文字重建與親人的精神聯系
“大多數中國人都如我的親人一樣,在柴米油鹽、生兒育女、生老病死的細枝末節中推進人生”。 三村苦樂百家味,一城貴賤兩重天。 《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書寫幾十位親人的生命故事,關注三十年村莊的沉浮變遷,以實踐反思“返鄉書寫”,為大地上沉默的大多數發聲?
這本書寫得誠懇和慈悲,雖只是剖示一個家族樣本,卻不失為跟蹤中國社會千年變局的一種微觀史記,一份逼問過去與未來的深重憂思。在黃燈筆下,鄉村不再是寄寓鄉愁的載體,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傾其智識、關懷于其中的“問題的場域”。
作為整個家族唯一獲得高學歷的人,我的成長,隱喻了一種遠離鄉村的路徑。長久以來,在知識包裹、理論堆積的學院生活中,我以為個人的日常和身后的親人失去關聯,是一種正常。事實上,在一種掛空的學院經驗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學術的幻覺,我的生活確實難以和身后的群體產生太多交集。無可否認,當我不得不目睹親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無能為力的同時,內心也隱隱升起一種逃離的慶幸。
2002年6月,獲得碩士學位后,我沒有選擇工作,而是南下廣州繼續攻讀博士,“南方”作為一個實在的場域,突兀地進入我的視野。對我而言,人生的宏圖再一次展開,理論的誘惑讓我沉迷。在學院的高深和寧靜中,我一次次感激命運讓我逃脫了90年代后期國企工人下崗的厄運,慶幸個人的努力終于獲得了回報。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學位、順利畢業,我的人生就會自然而然駛入早已預設好的軌跡,從此遠離底層,遠離辛酸與淚水。在個人奮斗的路線圖中,每個環節嚴絲合縫,與閃閃發光的時代交相輝映。確實,十幾年前的博士頭銜,還有足夠的含金量讓一個底層青年擺脫卑微。
我從來沒有想到,堂弟黃職培的一次偶然造訪,給我提供了契機。這個契機不但悄然改變了我多年的平靜狀態,而且讓我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群體。
堂弟黃職培十四歲不到,就來廣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開我的門,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飾不住四年未見的喜悅。我因為一直外出求學,而他過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經多年沒有見面。他興奮地告訴我,自己如何巧妙躲過門衛的盤查、順利進入無比神秘的中山大學。我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園,并不是對所有人開放。少年時代就來廣州打工的堂弟,盡管有著一張年輕的臉孔,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廣州酒家”的精裝月餅,一箱是“蒙牛牛奶”,這些今天看來極為普通的東西,對當時的學生而言還十分珍貴,也很少享用,我沒想到十九歲不到的堂弟,竟然給我送來禮物。我責怪他花錢,他只說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我問他手頭是否還有錢,仿佛為了讓我放心,他很開心地告訴我身上還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當時因為年齡太小、手藝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飯吃。他甚至沒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飯的邀請,就匆匆趕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盡管多次從父母那兒得知,故鄉的很多親人都蝸居在廣州一個叫塘廈的城中村,離我就讀的學校并不太遠,但我從來沒有動過去看望他們的念頭,甚至因為有些親人賭博、吸毒,總和一些來歷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潛意識里希望和他們保持距離,劃清界限,以免給自己帶來麻煩。
堂弟的到來,讓我感動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逐漸清晰—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中,逃離的群體,是如何在知識的規訓中,以個人成功的名義剝離一種本真的感情,并在內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計和權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不動聲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覺,逐漸疏遠身后的親人?我隱隱感到竭力營構的優越感正轟然垮掉,自我審視悄然出現。
這是我內心深處最大的隱秘。這個偶然的場景和事件,堂弟壓根不會放在心上,但它卻總是自動校準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離人生的險境,在周密的計劃和有效的努力中,越來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軌跡;在貌似精英化的個人路線圖中,逃離故鄉是擺脫厄運的起點,遠離親人是塑造精英感覺的開端。我在暗中使勁,眾多親人不體面的容顏,在城市的傲慢和學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計的背景;我并非有意遠離他們,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確實讓親人之間普通的交集變得遙不可及。
我得承認,堂弟的事,有很多讓我迷惑不解。堂弟五個月大的時候失去母親,幼年并沒有得到父親的細心照料,奶奶過世后,只得和哥哥相依為命。初中都沒有讀完,為了獲取進城打工的機會,他謊報年齡,把實際年齡改大了四歲。我不知道,在戾氣橫生、情感粗糙的堅硬現實里,一個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廣州多年的辛酸輾轉中,如何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廈混亂、骯臟的環境中,一個底層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騙、被拖欠工資、被抓進收容所挨餓三天之后,為何對生活沒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被日漸生硬、冰冷的知識稀釋。反觀自己的生存,我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進而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從此以后,我意識到,單純從“經濟層面”來觀照打工的親人,并搭配一份來自身份差異的道德優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價的同情,是多么淺薄而又世故。對親人精神世界和時代關系的勾連,成為我多年的心愿。
堂弟稚嫩的身影,徹底接通了我和親人之間愛的通道,這條通道曾經暢通,只不過因為各自境遇的改變,被彼此的生疏、隔膜阻斷。在知識的包裹中,我還發現,因為眼光的轉向,心靈也重新獲得了活力。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山大學讀博士期間,多次接受他們的邀請,去白云區塘廈村和親人共度傳統節日。盡管去過多次,但塘廈村的每一條路、每一棟房子在我眼中都沒有差別,我始終無法記住其相似的面目,每次去看他們,還是得由堂弟職培帶路。跟著前來接我的堂弟,我一次次在城中村的街道間穿梭,真真切切地見識了什么叫“一線天”,什么叫“握手樓”,什么叫“蝸居”,什么叫暗無天日。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場景在我眼前展開,故鄉的美好記憶與他們在南方的生活場景,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
我決心書寫這個群體。當他們進入我的視線,并調動了我強烈的表達欲望時,另一種警惕立即出現—我意識到,在進入他們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內心世界時,要盡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我特別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優越感會凌駕于他們的講述之上,更害怕他們不經意中講出的人生經歷,會在我的筆下,被文字輕佻地包裝為他者的故事。因為對我的信任和愛,親人們在講起各自的南下經歷時,哪怕談起最悲慘的事情,都帶著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須意識到他們講述背后的情緒過濾與我文字背后情緒膨脹之間的客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