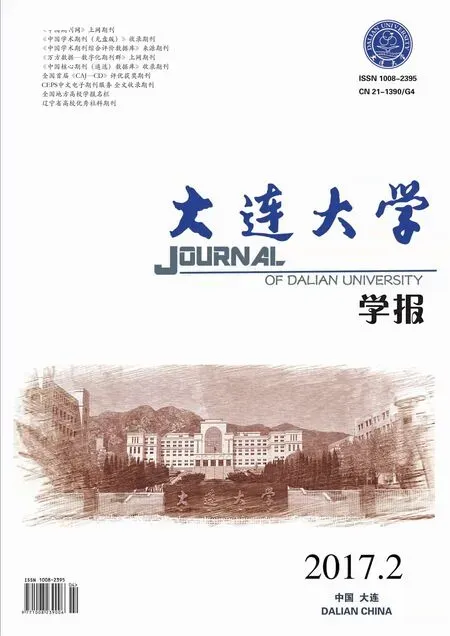中國(guó)智庫(kù)建設(shè)研究:歷程、困境與路徑探索
麻 紅, 國(guó) 宇
(1.大連大學(xué) 國(guó)際學(xué)院 ,遼寧 大連 116622; 2.大連大學(xué) 東北亞研究院,遼寧 大連 116622)
中國(guó)智庫(kù)建設(shè)研究:歷程、困境與路徑探索
麻 紅1, 國(guó) 宇2
(1.大連大學(xué) 國(guó)際學(xué)院 ,遼寧 大連 116622; 2.大連大學(xué) 東北亞研究院,遼寧 大連 116622)
歷史上,中國(guó)智庫(kù)的發(fā)展道路是有別于西方國(guó)家的。傳統(tǒng)的翰林制度的演變與門客、幕賓階層的興衰,構(gòu)成了中國(guó)智庫(kù)發(fā)展在官方與民間兩條路徑。在現(xiàn)階段,中國(guó)智庫(kù)發(fā)展面臨著缺乏公眾參與、功能定位單一以及缺乏社會(huì)影響力等問(wèn)題。從這些問(wèn)題的解決著手,可以尋找到中國(guó)新型智庫(kù)的發(fā)展途徑
中國(guó)智庫(kù);歷程;困境;發(fā)展
引言
智庫(kù),又稱思想庫(kù)或智囊團(tuán)。作為現(xiàn)代國(guó)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智庫(kù)在決策與咨詢領(lǐng)域發(fā)揮的重大作用已廣為人所知。究其本質(zhì)而言,智庫(kù)與智庫(kù)研究同屬于知識(shí)政治學(xué)的范疇。在西方,其理論淵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臘羅馬時(shí)期,蘇格拉底將治國(guó)的才能視為一種知識(shí),執(zhí)政者既要對(duì)其承擔(dān)的義務(wù)有自知之明,又要做好知識(shí)的儲(chǔ)備。[1]亞里士多德則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提出兩類人必須掌握政治事務(wù)的相關(guān)知識(shí),即政治實(shí)踐者與教授政治職能的“智者”。[2]而“智者”備于咨詢的角色功能顯然符合現(xiàn)代智庫(kù)在政策決策過(guò)程中的定位。
與大多數(shù)現(xiàn)代意義的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一樣,現(xiàn)代智庫(kù)的創(chuàng)設(shè)與發(fā)展也是首先在西方起步的。先發(fā)優(yōu)勢(shì)也令我們?cè)诮裉煺務(wù)撝菐?kù)時(shí),有了一個(gè)先入為主的,符合西方文化價(jià)值觀念的定義與較為固定的討論框架。智庫(kù)往往被定義為一個(gè)既非政府部門又非盈利機(jī)構(gòu)的獨(dú)立組織。以實(shí)際性與現(xiàn)實(shí)性作為其研究的最大出發(fā)點(diǎn),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目標(biāo),為政府決策提供多種可行性方案。自上世紀(jì)初在歐美國(guó)家誕生以來(lái),智庫(kù)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種類繁多,數(shù)量龐大,組織嚴(yán)密,運(yùn)行完善的組織,在西方國(guó)家的政治經(jīng)濟(jì)生活中發(fā)揮著巨大作用。以至于有學(xué)者將智庫(kù)視為是西方國(guó)家繼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門”。[3]
國(guó)內(nèi)對(duì)于智庫(kù)的研究,大致起始于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從最初的以歐美國(guó)家智庫(kù)發(fā)展?fàn)顩r為研究對(duì)象,逐漸過(guò)渡到集中探討如何發(fā)展中國(guó)智庫(kù)這一問(wèn)題上來(lái),對(duì)于中國(guó)智庫(kù)的職能、影響力以及發(fā)展方向的研究都取得了長(zhǎng)足的進(jìn)步。于此同時(shí),中國(guó)智庫(kù)也積極參與到全球性的能源與氣候變化,國(guó)家與地區(qū)關(guān)系等領(lǐng)域的政策制定過(guò)程中,在國(guó)家的政治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內(nèi)扮演著越來(lái)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相較于西方國(guó)家近百年的智庫(kù)發(fā)展歷史,中國(guó)的智庫(kù)與智庫(kù)研究都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文化與制度的現(xiàn)實(shí)差異,必然會(huì)使西方國(guó)家的智庫(kù)發(fā)展路徑在中國(guó)遭遇水不不服的困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提出的“加強(qiáng)中國(guó)特色新型智庫(kù)建設(shè)”的戰(zhàn)略部署,適時(shí)的為中國(guó)的智庫(kù)建設(shè)提出了路線指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梳理智庫(kù)這一決策咨詢機(jī)構(gòu)在中國(guó)原生形態(tài)以及其內(nèi)在的發(fā)展脈絡(luò),從而探索智庫(kù)的中國(guó)特色發(fā)展路徑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中國(guó)傳統(tǒng)智庫(kù)的形式與發(fā)展歷程
與西方先賢將政治與知識(shí)的關(guān)系作為一個(gè)學(xué)術(shù)問(wèn)題加以討論幾乎同時(shí),中國(guó)古代思想家也已經(jīng)將知識(shí)視為國(guó)家管理必不可缺的資源之一。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4],概括的反映了咨詢性研究成果在政治領(lǐng)域里的貢獻(xiàn)。在中國(guó)歷史上的春秋時(shí)期,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階層而出現(xiàn)的“士”,在當(dāng)時(shí)以貴族為主要行政管理者的社會(huì)架構(gòu)中擔(dān)當(dāng)了決策咨詢者的角色,以“稷下學(xué)宮”為代表的學(xué)者集團(tuán)具備了決策咨詢機(jī)構(gòu)的雛形。隨著中國(guó)專制文官制度的發(fā)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掌握知識(shí)不但成了學(xué)者入仕,轉(zhuǎn)型為政治實(shí)踐者的重要途徑,也使得具備第一線執(zhí)政經(jīng)驗(yàn)的官僚能夠?qū)⑵浣?jīng)驗(yàn)轉(zhuǎn)化歸納為經(jīng)世濟(jì)用的知識(shí),影響后來(lái)者對(duì)于政治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道路的設(shè)計(jì)。這種如同現(xiàn)代西方智庫(kù)“旋轉(zhuǎn)門”機(jī)制的人才角色轉(zhuǎn)換在中國(guó)歷史上比比皆是。此外,以“諫議”為主要形式的決策咨詢體系在秦代便已基本形成。以“士”為代表的非正式,非制度的咨詢形式逐漸逐漸讓位于官方咨詢機(jī)構(gòu)。作為政治體制重要組成部分的咨詢制度成為中國(guó)專制政治與中國(guó)特色的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幾乎貫穿了中國(guó)專制制度的演進(jìn)歷程。到唐代,翰林院的設(shè)立則標(biāo)志著中國(guó)官方性質(zhì)的輔政咨詢機(jī)構(gòu)發(fā)展到了一個(gè)較為完備的階段。翰林院設(shè)立的初衷是“天下以藝能技術(shù)見(jiàn)召者之所處也”[5],掌握各種技能知識(shí)的專家學(xué)者集中在一起,以其所長(zhǎng)貢獻(xiàn)君主。翰林院的設(shè)立,使得大批學(xué)者匯聚于此,其功能也逐漸超出了“供奉”、“待召”的初衷,成為起草內(nèi)制,參謀顧問(wèn)的樞要部門。
與官方咨詢機(jī)構(gòu)不斷制度化的發(fā)展途徑相比,民間的智囊團(tuán)體則沿著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演進(jìn)。它們依附于私人,往往以個(gè)體的方式提供專業(yè)性的服務(wù)。門客與幕府中的幕賓,都屬于此類。
門客特指從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開始出現(xiàn)的,憑借一技之長(zhǎng)寄身于貴族門下,為其提供服務(wù)的一類人。這一類人在春秋戰(zhàn)國(guó)的政治活動(dòng)中極為活躍,很多政治家從門客出身,為主君出謀劃策,又隨著主君的地位升遷而執(zhí)掌一國(guó)政事。自秦以降,隨著中央集權(quán)制與官僚體制的不斷完備,門客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到了漢朝,朝廷對(duì)養(yǎng)士之風(fēng)大加限制,門客逐漸淡出歷史舞臺(tái)。直到宋代,門客獲得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蓄養(yǎng)門客又成了貴族與高級(jí)官宦之間流行的風(fēng)氣。門客得以參加科舉,主要依據(jù)的是宋代的蔭補(bǔ)制度,這一制度規(guī)定太師及以上官員,太后、太妃等可以推薦門客任官,其余各級(jí)官吏也可按照一定規(guī)則,推薦自己的門客參加科舉考試。這種制度使得門客與其服務(wù)的主人之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緊密聯(lián)系,具有一定知識(shí)的學(xué)者積極投奔權(quán)貴之家,以自己的知識(shí)為權(quán)貴的政治活動(dòng)出謀劃策,進(jìn)而為自身獲得從政的資格。
幕府的出現(xiàn),最早亦可上溯到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據(jù)《史記》記載,李牧為防備匈奴入侵,“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fèi)”。這里的莫府便是早期的幕府。幕府誕生之初原本是領(lǐng)兵作戰(zhàn)的將軍臨時(shí)辦公僚屬參贊軍務(wù)的場(chǎng)所。隨著軍事將領(lǐng)權(quán)力的擴(kuò)大,幕府幕賓也有了與國(guó)家官僚相對(duì)應(yīng)的職能。在唐人李直芳《邠州節(jié)度使院壁記》中有“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署吏王國(guó)命官為比”的描述。[6]幕賓雖多居武職,但其私人參謀的身份特征無(wú)疑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服務(wù)的對(duì)象僅限于幕府的組建者,其參與的事務(wù)雖然以軍事為主,但也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jì)等其他領(lǐng)域。
到了清晚期,地方督撫大員權(quán)力的不斷擴(kuò)大,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握有實(shí)權(quán)的政治人物,為繞開繁冗的官僚體系束縛,或是避免政敵攻訐,往往會(huì)“更多地依靠人際關(guān)系的非正式系統(tǒng),而不是行政管理的渠道”,[7]發(fā)揮個(gè)人影響力,實(shí)現(xiàn)其政治上的目的。在他們的幕府中,幕賓的角色也發(fā)生了變化,其私人顧問(wèn)的形象愈發(fā)凸顯。大多數(shù)幕賓或者通過(guò)科舉考取過(guò)功名,或者曾為官場(chǎng)中人,或者接受了新式教育,無(wú)論其通過(guò)何種途徑成為幕府中的一元,其知識(shí)分子的身份都是毋庸置疑的。幕府的主要職能,也從參贊戎機(jī)為主徹底地轉(zhuǎn)變?yōu)槟桓姓咛峁I(yè)意見(jiàn)以及協(xié)助幕府所有者實(shí)施其政治經(jīng)濟(jì)主張。
總的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歷史上的智囊機(jī)構(gòu)與智囊團(tuán)體,其興衰歷程與中國(guó)專制制度的發(fā)展程度是密切相關(guān)的。當(dāng)政治體制結(jié)構(gòu)傾向于中央集權(quán)之時(shí),智囊機(jī)構(gòu)在政治中樞所起到的作用除了咨詢之外,甚至還會(huì)取代部分政府部門行使決策的職能。一旦集權(quán)制度遭到破壞,地方或個(gè)人權(quán)力膨脹,私人的智囊團(tuán)體就會(huì)迎來(lái)一個(gè)較大的發(fā)展時(shí)期,這也反過(guò)來(lái)加劇了政治權(quán)力的分散。
二、中國(guó)智庫(kù)在新時(shí)期面臨的主要困境
我國(guó)現(xiàn)代意義上的智庫(kù)發(fā)展起步于改革開放初期,伴隨著國(guó)家經(jīng)濟(jì)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不斷推進(jìn)。基本上,國(guó)家的決策咨詢體系是由該國(guó)的政治體制與經(jīng)濟(jì)體制形式所決定的,而智庫(kù)的發(fā)展模式又取決于國(guó)家決策咨詢體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智庫(kù)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程度是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與政治體制發(fā)展的集中體現(xiàn),這也是中國(guó)智庫(kù)發(fā)展,在面臨的問(wèn)題與前進(jìn)方向上有別于西方智庫(kù)發(fā)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我國(guó)的政策決策過(guò)程,創(chuàng)造性地將民主集中制、協(xié)商制原則以及政策實(shí)踐中的特區(qū)制,點(diǎn)面結(jié)合的推廣制有機(jī)的結(jié)合在一起。在這一過(guò)程中,智庫(kù)的參與模式應(yīng)當(dāng)是多樣與多層次的,但是由于傳統(tǒng)的“管理主義”依然是我國(guó)行政決策的主導(dǎo)思想,這就使得智庫(kù)在新時(shí)期的發(fā)展依然存在不小的困難。
“管理主義”決策模式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直接產(chǎn)物。這一模式通過(guò)行政體制內(nèi)的決策者壟斷決策的資源與權(quán)力的方式,實(shí)現(xiàn)決策者對(duì)人事、制度以及事務(wù)發(fā)展的直接管理。這一模式必然的要求盡可能龐大的行政體系支撐,而龐大的行政體制所帶來(lái)的不止是決策效率的低下,更多的是信息獲取鏈條的延長(zhǎng),信息獲取方式的單一,從而導(dǎo)致部分決策嚴(yán)重滯后,以至于決策失敗。此外,“管理主義”行政模式的另一個(gè)弊端在于,對(duì)于社會(huì)的個(gè)性化訴求或者新訴求,作為按照既定步驟與程序運(yùn)行的行政機(jī)關(guān)難以進(jìn)行有效靈活的回應(yīng)。當(dāng)這種訴求形成較大規(guī)模之后,行政者又往往只能依靠階段性的“運(yùn)動(dòng)型治理”或者忽視訴求合理要素的“粗暴型治理”加以應(yīng)對(duì)。這不但會(huì)造成社會(huì)發(fā)展的停滯與僵化,更會(huì)激化社會(huì)矛盾,加大社會(huì)治理的難度。
公眾參與是行政決策的基本途徑,但是由于傳統(tǒng)管理主義決策模式的影響,公眾在決策過(guò)程中扮演的往往依然是一個(gè)被弱化,甚至是虛化的角色,參與更是無(wú)從談起。公眾訴求往往被被錯(cuò)誤的當(dāng)做是個(gè)體訴求或個(gè)別訴求而無(wú)法有效的進(jìn)入決策過(guò)程中。原本在這一環(huán)節(jié)中應(yīng)當(dāng)起到對(duì)訴求研判,整理,提煉功能的智庫(kù),顯然是在管理主義決策模式中“隱身”了。
如果說(shuō)決策模式左右了智庫(kù)在決策過(guò)程中的角色定位,那么決策的組織結(jié)構(gòu)則決定了智庫(kù)在決策過(guò)程中功能定位。據(jù)中國(guó)社科院2013年發(fā)布的《全球智庫(kù)發(fā)展報(bào)告》的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guó)的智庫(kù)數(shù)量?jī)H次于美國(guó),共有426家。[8]在這400余家智庫(kù)機(jī)構(gòu)中,地方社科院占了其中較大比例。相對(duì)于高校科研院所,地方社科院由于不承擔(dān)教學(xué)任務(wù),可以將更多資源投入社會(huì)議題與政策調(diào)研的工作中來(lái),這使得地方社科院較為順暢的轉(zhuǎn)型為地方黨政機(jī)關(guān)思想庫(kù)與智囊團(tuán)。但是在行政編制上,地方社科院仍然隸屬于各級(jí)地方政府,在研究議題的設(shè)置以及研究經(jīng)費(fèi)的來(lái)源上依然依賴于各級(jí)地方政府。這就令地方社科院在社會(huì)議題的研究過(guò)程中存在著無(wú)法以問(wèn)題為導(dǎo)向而不得不以以政策為導(dǎo)向的問(wèn)題。原本應(yīng)該在決策過(guò)程前段便參與議題的設(shè)置、論證的地方社科院往往只能在政策決策后段才加入進(jìn)來(lái),為政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提供“背書”。這種“背書”是有利于政策的推進(jìn)與實(shí)施的,但是,單純的為出臺(tái)的政策提供理論或現(xiàn)實(shí)依據(jù),則顯然與現(xiàn)代智庫(kù)的功能定位有不小的差距,也有悖于決策必須科學(xué)民主的基本要求。
另外,角色的隱身與功能的偏頗使得中國(guó)的智庫(kù)往往缺乏必要的社會(huì)影響力。而一定的影響力卻恰恰是智庫(kù)存在與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智庫(kù)在為決策者提供各類咨詢產(chǎn)品的同時(shí),也同樣負(fù)有引導(dǎo)社會(huì)參與,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的天然使命。中國(guó)現(xiàn)階段智庫(kù)發(fā)展中,往往只是將智庫(kù)定位為單純的被咨詢者,將決策與咨詢割裂開來(lái),智庫(kù)機(jī)構(gòu)極少以問(wèn)題導(dǎo)向主動(dòng)進(jìn)行課題研究,僅按決策者的委托提供咨詢產(chǎn)品,同時(shí)又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決策的保密要求,拒絕向不特定公眾提供智庫(kù)的研究成果。事實(shí)上,國(guó)外智庫(kù)往往將向公眾公開研究成果視為有效的提升智庫(kù)影響力的手段,其對(duì)研究成果的公開也是智庫(kù)獲得專業(yè)性與公平性評(píng)價(jià)的途徑。如果智庫(kù)的研究成果不為外界所知,無(wú)法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社會(huì)監(jiān)督與社會(huì)效益,智庫(kù)的發(fā)展就必然會(huì)落入神秘化的歧途,決策由“管理主義”模式向“參與主義”模式轉(zhuǎn)型更是無(wú)從談起了。
三、新時(shí)期中國(guó)智庫(kù)發(fā)展的路徑探索
現(xiàn)階段我國(guó)智庫(kù)的主體,主要有以下幾類構(gòu)成。一是黨政軍智庫(kù),中共中央、國(guó)務(wù)院直屬的研究機(jī)構(gòu)、各省市的政策研究室,這一類智庫(kù)相對(duì)擁有更充足的政策信息儲(chǔ)備優(yōu)勢(shì),但也存在缺乏獨(dú)立性,靈活性,與各級(jí)黨政機(jī)構(gòu)存在著較強(qiáng)依附關(guān)系等劣勢(shì),研究成果客觀性不足。第二類是各級(jí)社科院智庫(kù),這一類智庫(kù)是現(xiàn)階段我國(guó)智庫(kù)的主要組成部分,研究領(lǐng)域更能兼顧理論與實(shí)踐,更能提煉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關(guān)鍵問(wèn)題,也能充分把握黨和國(guó)家的政策方向,但是,這類智庫(kù)與黨政軍智庫(kù)一樣,也存在獨(dú)立性與靈活性不足,研究成果甚少面向公眾等問(wèn)題。第三類智庫(kù)是各高校研究機(jī)構(gòu),是我國(guó)現(xiàn)階段發(fā)展最為迅速的智庫(kù)類型。 高校智庫(kù)得益于高校的人才資源豐富,學(xué)術(shù)交流頻繁等先天條件,在研究課題的前瞻性,研究方法的科學(xué)性等方面往往具有較大優(yōu)勢(shì)。在理論性、基礎(chǔ)性研究方面的貢獻(xiàn)無(wú)可比擬。但同時(shí),這類智庫(kù)也存在研究成果與政策實(shí)踐聯(lián)系不夠緊密,研究力量相對(duì)分散等劣勢(shì)。第四類智庫(kù)是各類民間智庫(kù),民間智庫(kù)作為我國(guó)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途徑之一,其的研究成果往往與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緊密,觸及到社會(huì)經(jīng)濟(jì)中的重點(diǎn)難點(diǎn),其研究結(jié)果也大多面向公眾,是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橋梁,但這類智庫(kù)也存在發(fā)展規(guī)模較小,研究成果易受資金來(lái)源左右,研究成果影響力較小的問(wèn)題。
綜合而言,我國(guó)現(xiàn)有智庫(kù)類型較為齊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國(guó)決策體系框架。但是各類智庫(kù)大多存在公信力較低,對(duì)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反應(yīng)不夠及時(shí)全面等問(wèn)題。如前所述,這主要是由我國(guó)現(xiàn)階段決策模式與決策組織結(jié)構(gòu)所決定的。智庫(kù)局限于政策闡述者的角色,顯然是與黨中央大力發(fā)展新型智庫(kù)的要求相違背的。筆者認(rèn)為,新型智庫(kù)的路徑建設(shè)可以遵循如下原則:提高智庫(kù)在決策過(guò)程中的參與程度,提高智庫(kù)影響力與公信力,提高智庫(kù)研究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
1. 提高智庫(kù)在決策過(guò)程中的參與程度
新型智庫(kù)發(fā)展必須轉(zhuǎn)變思路,將智庫(kù)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公共決策機(jī)制聯(lián)系起來(lái)。貫徹科學(xué)決策,民主決策的原則,明確智庫(kù)、學(xué)者、公眾在公共決策過(guò)程中的地位與職能。發(fā)揮智庫(kù)在社會(huì)問(wèn)題歸納、政策前期調(diào)研等方面的優(yōu)勢(shì), 構(gòu)建包括智庫(kù)、盈利組織、公共部門在內(nèi)的網(wǎng)絡(luò)化治理模式,實(shí)現(xiàn)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的合作共治。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化的多層次合作,實(shí)現(xiàn)決策信息資源共享,充分發(fā)揮智庫(kù)旋轉(zhuǎn)門機(jī)制,實(shí)現(xiàn)治理共同體內(nèi)部人才交流,打破咨詢與決策過(guò)程中不必要的系統(tǒng)性封閉,提高政策決策的透明性與公開性。
2.提高智庫(kù)影響力與公信力
新型智庫(kù)發(fā)展必須重新對(duì)智庫(kù)進(jìn)行角色與功能定位。我國(guó)智庫(kù)應(yīng)該既不是政策的背書者,也不是持不同政見(jiàn)者。在堅(jiān)持問(wèn)題導(dǎo)向的同時(shí),也必須堅(jiān)守客觀公正的立場(chǎng)。新型智庫(kù)應(yīng)該也必須成為政府的合作者、參謀者,同時(shí),智庫(kù)也必須扮演好公眾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從議題的提出,到論證結(jié)論必須同時(shí)對(duì)政府負(fù)責(zé)、對(duì)公眾負(fù)責(zé),其研究產(chǎn)品要即引導(dǎo)輿論又回應(yīng)輿論,做好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平臺(tái)。
3. 提高智庫(kù)研究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
智庫(kù)的思想產(chǎn)品應(yīng)當(dāng)具有公共性、政治性和社會(huì)性的特征。[9]智庫(kù)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正是智庫(kù)產(chǎn)品公共性與社會(huì)性的最佳體現(xiàn)。在現(xiàn)階段,我國(guó)各類智庫(kù)的資金來(lái)源主要依靠政府撥款,市場(chǎng)化還不是智庫(kù)產(chǎn)品的主要?dú)w宿,這導(dǎo)致了智庫(kù)研究產(chǎn)品類型化嚴(yán)重的局面。建設(shè)新型智庫(kù),應(yīng)當(dāng)建立智庫(kù)思想產(chǎn)品的購(gòu)買機(jī)制。政府應(yīng)當(dāng)在咨詢項(xiàng)目立項(xiàng)、研究產(chǎn)品采購(gòu)等環(huán)節(jié)建立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在平等的基礎(chǔ)上擇優(yōu)選擇各類智庫(kù)提供的思想產(chǎn)品。為各類智庫(kù)提供公平合理的獎(jiǎng)勵(lì)機(jī)制。另外,不能將智庫(kù)的思想產(chǎn)品局限在專供政府決策這一單一領(lǐng)域之內(nèi)。要開拓智庫(kù)咨詢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發(fā)布途徑,充分利用傳統(tǒng)媒體與網(wǎng)絡(luò)化新媒體提高智庫(kù)產(chǎn)品的曝光率,提高智庫(kù)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價(jià)值,進(jìn)而提高智庫(kù)產(chǎn)品的自我造血功能,實(shí)現(xiàn)智庫(kù)的良性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周輔成.西方倫理學(xué)名著選輯[M].上卷.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7:1.
[2]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政治哲學(xué)史[M].李天然,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26.
[3]于今.中國(guó)智庫(kù)發(fā)展報(bào)告:智庫(kù)產(chǎn)業(yè)的體系構(gòu)建[M].北京:紅旗出版社,2013:3.
[4]孟子.孟子[M].滕文公,下.北京:中華書局,2010:102
[5]王浦 ·《唐會(huì)要》卷五十七[M].翰林院.
[6]全唐文[M].卷六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766.
[7]劉廣京.李鴻章評(píng)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39.
[8]全 球 智 庫(kù) 發(fā) 展 報(bào) 告2013[OL].中 國(guó) 社 會(huì) 科 學(xué)網(wǎng) ,(2014-01-27). http://www.cssn.cn/jjx/jjx_dt/201401/ t20140127_955077.shtml
[9]王莉麗.中國(guó)智庫(kù)思想市場(chǎng)的培育與規(guī)制[J].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28(2):85.
A Study of China’s Think Bank: Process, Challenges and Path
MA Hong1, GUO Yu2
(1.Foreign Affairs Offic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2. Institute of Northeast Asia,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west historically.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Hanlin academic system”, the rise and the decline of house guests and advisors of high officials take two paths that the former is on governmental level and the latter on civil level.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 is faced up with such challenges as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unitary positioning of its function as well as lack of social influence, etc. Only by sorting out these problems can China trace its developing path to a new Think Tank.
China’s Think Tank; process; challenges; development
G0
A
1008-2395(2017)02-0092-05
2017-02-22
大連市社科聯(lián)(社科院)重點(diǎn)項(xiàng)目(2015dlskzd136)
麻紅(1973-),女,大連大學(xué)國(guó)際學(xué)院講師,主要從事國(guó)際教育文化研究;國(guó)宇(1980),男,歷史學(xué)碩士,大連大學(xué)東北亞研究院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東北亞國(guó)際關(guān)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