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氏菌病的診斷及治療方法研究進展
朱珠,陳安林 ,彭丹,閔迅,陳澤慧(遵義醫學院,貴州遵義563000;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
布魯氏菌病的診斷及治療方法研究進展
朱珠1,陳安林2,彭丹1,閔迅2,陳澤慧2
(1遵義醫學院,貴州遵義563000;2遵義醫學院附屬醫院)
布魯氏菌病是由布魯氏菌引起的世界性嚴重的人畜共患疾病,其主要臨床表現為流產、不孕不育、發熱、關節炎癥及肝脾腫大等。細菌學診斷和血清學診斷方法是布魯氏菌病的主要診斷方法,其中細菌學診斷是診斷布病的“金標準”,但耗時較長、環境要求高、檢出陽性率低、敏感性不強。血清學檢測技術是現有的診斷布魯氏菌病最廣泛的方法,主要包括虎紅平板凝集試驗、試管凝集試驗、補體結合試驗、酶聯免疫吸附試驗。RBPT法檢測成本低、敏感性強、操作簡單,但特異性較低。SAT法特異性、準確性均較好,可用于布魯氏菌病的早期診斷,適合小量樣本檢測。ELISA法敏感性、特異性均較高,可與RBPT、SAT聯合應用。布魯氏菌病的治療目前主要采用化學療法和中醫療法。
布魯氏菌病;人畜共患疾病;細菌學診斷方法;虎紅平板凝集試驗;試管凝集試驗;補體結合試驗;酶聯免疫吸附試驗;
布魯氏菌病是一種由布魯氏菌引起的以動物和人為傳染源的細菌性傳染疾病,其主要特點是人畜共患[1]。布魯氏菌不僅感染途徑多樣且發病機制復雜,可通過消化道、呼吸道、皮膚黏膜等侵入體內引起一系列變態免疫反應。動物布魯氏菌病可導致不孕、流產、睪丸炎等[2]。人布魯氏菌病的臨床表現十分復雜,最常見的是高熱、肌肉酸痛、關節痛[3]。如病情遷延可導致敗血癥,嚴重者可累及多個器官系統功能受損。布魯氏菌已列入我國乙類法定報告傳染性疾病[4]。近年,布魯氏菌病發病率逐漸升高[5]。現將布魯氏菌病的診斷及治療方法綜述如下。
1 布魯氏菌病的臨床癥狀和診斷方法
1.1 布魯氏菌病的臨床癥狀 布魯氏菌屬共包括9個種,分別為牛種、羊種、豬種、犬種、綿羊附睪種、沙林鼠種等[6]。其中以羊種和豬種布魯氏菌病情最嚴重,牛種和犬種其次,沙林鼠種、綿羊附睪種羊種幾乎不致病[7]。羊種布魯氏菌病患者急性起病多見,常表現為中毒癥狀。豬種布魯氏菌病對患者肝臟、脾臟的損害明顯,主要臨床表現為肝脾炎癥和腫大,容易引起發熱、發汗、全身乏力等急性癥狀[8],病程長且病情遷延難愈、可反復發作,甚至造成器官組織不可逆損害。牛種和犬種布魯氏菌導致的臨床癥狀輕微,可有發熱表現[9]。研究發現,60多種動物能感染布魯氏菌病,主要以牛、羊、豬多見。
10%~30%布魯氏菌病患者急性發病,幾乎所有患者均有發熱,其熱型表現各異,以弛張熱最常見,以波狀熱最具有典型特點[10],部分患者也可出現不規則熱和低熱。多汗也是本病的主要表現和突出癥狀[11],夜間和晨起時為著,多數患者伴有身體軟弱無力。布魯氏菌侵入關節系統時,患者會出現關節炎癥,引起紅腫疼痛,多自訴疼痛難忍,猶如針刺般劇痛常規鎮痛藥治療效果差。男性患者還常并發特征性睪丸炎,多數患者單側發病,睪丸紅腫疼痛,伴有明顯壓痛,嚴重者累及附睪。偶見患者臨床表現為淋巴結腫大、肝脾腫大、頭痛、皮膚斑疹等。
布魯氏菌在體內單核吞噬系統的各種免疫細胞中生存、繁殖,急性期得不到有效治療可導致病情進入慢性期。慢性期布魯氏菌病感染特點為急性期遺留癥狀和全身各個系統的病變。急性期臨床癥狀會繼續惡化,發熱伴寒戰,以低熱多見,不規律出現,夜間盜汗頻繁,全身乏力明顯,精神低落。關節病變可進一步發展為腫脹化膿,甚至出現不可逆的關節損害,可累及膝、肘、髖、脊柱、骶髂等多個關節[12]。
1.2 布魯氏菌病的細菌學診斷方法 細菌分離培養技術是最傳統的布魯氏菌病細菌學診斷方法,也是診斷布魯氏菌病的“金標準”[13 ]。血液、體液、骨髓、關節積液等中檢出布魯氏菌病原體是診斷布病的最直接證據。然而布魯氏菌生長十分緩慢(至少72 h),營養要求復雜,并且需置于5%~10% CO2、37 ℃環境中培養。布魯氏菌屬于高致病性微生物,實驗室要求生物安全等級為二級以上。但細菌學培養的臨床送檢標本陽性率不高。綜上所述,細菌學方法耗時較長、環境要求高、檢出陽性率低、敏感性不強,且危險性大。
1.3 布魯氏菌病的血清學診斷方法 血清學檢測技術是現有的診斷布魯氏菌病最廣泛的方法,尤其是處于慢性期的患者,而且還可以確定患者有無復發情況。其主要包括虎紅平板凝集試驗(RBPT)、試管凝集試驗(SAT)、補體結合試驗(CFT)、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膠體金標試驗(GICA)等。
1.3.1 RBPT RBPT是常規初步篩查布病的檢測方法之一。它的檢測成本低、敏感性強、操作簡單[14], 而且反應快、耗時短(幾分鐘內即可觀察結果),適合于進行布魯氏菌病的大規模血清學初篩檢驗和檢疫。李永霞等[15]對青海省海晏地區2012年~2013年期間布魯氏菌病流產和疑似流產的4428份牦牛血清進行檢測,RBPT檢出率分別約為80.66%和25.78%,這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16]一致。但RBPT以布氏桿菌細胞壁的脂多糖(LPS)上的O-鏈(抗原)作為診斷靶點[17]。而布氏桿菌與小腸結腸炎耶爾森菌O9、大腸桿菌O157、沙門氏菌、霍亂弧菌等部分革蘭氏陰性菌具有高度類似的O-抗原結構[18],容易誘發交叉凝集反應,導致結果出現假陽性;RBPT另一個缺點是檢測過程和結果容易受到許多外界因素(溫度、凝集時間等)的影響,或者采血及檢測人員水平的限制造成假陰性結果[19]。總之,RBPT特異性不強[20],需要加做其它試驗以驗證結果準確性。
1.3.2 SAT SAT是國內法定診斷布病的確定方法,也作為篩選試驗之一。與RBPT比較,SAT需要至少1 d才能對結果進行判讀,耗時長,操作相對復雜,不適合大范圍現場檢疫布病,而更多地用于小量樣本的檢測。但SAT特異性、準確性優于RBPT[21],且對IgM的敏感性高,IgM是感染后6~7 d血清中出現的抗體,所以SAT可用于布魯氏菌病的早期診斷。之后隨著患者血清IgM水平下降,IgG增多且趨于穩定,SAT不能識別血清中的IgG,導致準確率降低呈陰性。
1.3.3 ELISA RBPT和SAT兩種檢測方法均為檢測血清中特異性抗體,各有優缺點,我國的布魯氏菌病實驗室診斷中多采用將RBPT、SAT聯合應用,首先RBPT初篩,再進行SAT確診。而比較之下, ELISA是血清學診斷中比較新穎的一種方法。ELISA不但敏感性、特異性更高,而且具有簡單、快速的特點,已經成為國內外認可的檢驗技術,應用范圍最為廣泛[22]。RBPT和SAT均具有人為誤差問題的缺點,反應時間的長短、溫度對結果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而ELISA對實驗操作、條件要求更加明確精準,結果判定簡捷,可以避免人為的誤差。 但是三種方法針對的抗體類型不同,RBPT和SAT對早期出現的IgM抗體敏感性高,ELISA主要針對IgG抗體,敏感性相對更好。
2 布魯氏菌病的治療方法
2.1 布魯氏菌病的化學療法 對布魯氏菌病患者的化學療法必須遵循早期性、聯合性、足量性、足療程性的原則。具體標準為:①早期性:指需要對布魯氏菌病患者的病情加以早期發現、盡早完成臨床診斷并提供詳細報告,以盡早開展臨床治療。②聯合性:布魯氏菌病的治療需聯合應用細胞內、外殺菌藥物[23];利福霉素、利福噴丁等是常用的細胞內殺菌藥物,其可通過血腦屏障進入患者腦膜內,且具有低毒性;頭孢三代類藥物以及多西環素、四環素等是常用的細胞外殺菌藥物;藥物聯合應用可避免因單一用藥所導致的耐藥性問題,同時增加藥物協同作用[24]。③足量性:針對布魯氏菌病的藥品的用藥必須按照規范足量使用,以免患者短期內產生耐藥性,影響后續治療效果。④足療程性:布魯氏菌病患者均需要按照統一規范的治療方案,先用靜脈滴注給藥15 d,然后用口服藥物干預45~90 d,期間配合使用肝腎功能保護性藥物,以免患者因持續用藥產生肝腎功能障礙或其他并發癥。
2.1.1 利福噴丁、利福霉素療法 利福噴丁、利福霉素可干擾布魯氏菌病患者體內細菌RNA的合成,滅菌作用強,屬于全價格殺菌藥物。同時,利福噴丁、利福霉素藥物可殺滅人體內巨噬細胞,且由于巨噬細胞內濃度高于組織內濃度,故殺菌效果確切。利福噴丁、利福霉素對繁殖期雞間歇期布魯氏菌的殺滅價值均較好,強度高,殺滅速度快。利福噴丁、利福霉素作用于急性期布魯氏菌病患者時可不受環境酸堿度影響,在各種PH值環境下的細菌殺滅效果均較高。研究[25]報道發現利福噴丁治療布魯氏菌病效果優于利福平,且用藥不受環境酸堿度影響,在各種PH值環境下的細菌殺滅效果均可達到滿意狀態。其可能作用機制為:以環戊基取代利福平側鏈上的甲基合成的亞胺甲基哌嗪環戊基利福霉素藥物,對結核桿菌和其他分支桿菌在宿主細胞內外有明顯的殺菌作用,同時兼具低毒性、長效性等優點[26,27]。
2.1.2 舒巴坦鈉、頭孢哌酮療法 舒巴坦鈉、頭孢哌酮藥物對G-桿菌3代頭孢菌的作用效果確切,其中用藥頭孢哌酮能夠抑制布魯氏菌細胞壁的合成,發揮殺菌效果。舒巴坦鈉則為β酰胺酶抑制劑,可抑制患者體內耐藥菌株所產生的各種β酰胺酶成分[11],且能同步增強頭孢哌酮的藥物作用,兩種藥物聯合應用下對耐藥陰性桿菌同樣具有良好的協同作用,且在殺滅敏感菌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1.3 四環素、多西環素療法 四環素、多西環素均屬于廣譜類抑菌藥物,在用藥后起效速度非常快,濃度水平高,且對各類細菌的殺滅效果好[27]。其作用機制是為四環素、多西環素可干擾布魯氏菌中的蛋白質合成,在A位置與細菌核糖體30s亞基產生特異性結合反應,抑制氨基酰-tRNA在A位置的聯結反應,最終抑制肽鏈延長。多西環素用于急性期布魯氏菌病患者具有長效性、速效性、強效性等優點,但其在用藥后體內抗菌效果強,組織穿透力大,抗菌活性優于四環素。四環素可改變細菌細胞膜通透性,使細胞內核苷酸成分漏出,抑制細菌DNA復制,從而短期內發揮對急性期布魯氏菌病的治療價值。
2.1.4 喹諾酮療法 環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是目前臨床證實可用于治療布魯氏菌病的喹諾酮類抗生素藥物。此類藥物為經人工合成處理并含有4-喹酮母核一類抗菌藥物。環丙沙星與左氧氟沙星分別作為典型的第一代喹諾酮類抗菌藥物,與新一代光學活性喹諾酮抗菌素,均具有抗菌作用強、抗菌譜廣以及用藥安全可靠的特點。喹諾酮類抗生素用藥后能夠快速進入細胞內,分布范圍廣泛,起效速度快[28,29]。特別是在其進入吞噬細胞內后,對受體內網狀內皮系統吞噬細胞內布魯氏菌有良好的殺滅效果,對慢性肉芽腫的形成產生阻斷作用,為對布魯氏菌病進行治療的理想藥物,適用于急性期患者的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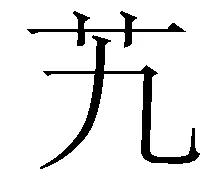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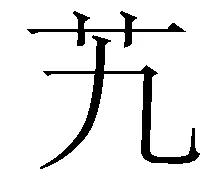
[1] Xavier MN, Winter MG, Spees AM, et al. CD4+T cell-derived IL-10 promotes Brucella abortus persistence via modulation of macrophage function[J]. PLoS Path, 2013,9(6):e1003454.
[2] Li MT, Sun GQ, Wu YF, et al.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a multi-group brucellosis model with mixed cross infection in public farm[J]. Applied Math Comput, 2014,23(7):582-594.
[3] Purwar S, Metgud SC, Gokale SK. Exceptionally high titres in atypical presentation of occult epididymo-orchitis due to brucellosis[J]. Jour Med Micro, 2012,61(3):443-445.
[4] Purwar S, Metgud SC, Gokale SK. Exceptionally high titres in atypical presentation of occult epididymo-orchitis due to brucellosis[J]. J Micro Bio, 2012,61(3):443-445.
[5] Mile B, Valerija K, Krsto G, et al. Doxycycline-rifampin versus doxycycline-rifampin-gentamicin in treatment of human brucellosis[J]. Tropical Doctor, 2012,42(1):13-17.
[6] Elfaki MG, Alaidan AA, Al-Hokail AA. Host response to Brucella infection: review and future perspective[J]. J Infect Devg Count, 2015,9(7):697-701.
[7] Lewis J M, Folb J, Kalra S, et al. Brucella melitensis 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in a traveller returning to the UK from Thailand: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Travel Med Infect Dis, 2016,14(5):444-450.
[8] Naseri Z, Alikhani MY, Hashemi SH, et al. Prevalence of the most common virulence-associated genes among Brucella Melitensis isolates from human blood cultures in Hamadan Province, West of Iran[J]. Iranian J Med Sci, 2016,41(5):422.
[9] Grunow R, Jacob D, Klee S, et al. Brucellosis in a refugee who migrated from Syria to Germany and lessons learnt, 2016[J]. Eurosurveillance, 2016,21(31):52-58.
[10] Peeridogaheh H, Golmohammadi MG, Pourfarzi F. Evaluation of ELISA and Brucellacapt tests for diagnosis of human Brucellosis[J]. Iranian J Micro Bio, 2013,5(1):14.
[11] De Bolle X, Crosson S, Matroule JY, et al. Brucella abortus cell cycle and infection are coordinated[J]. Trends Micro Bio, 2015,23(12): 812-821.
[12] Ulu-Kilic A, Karakas A, Erdem H, et al. Update on treatment options for spinal brucellosis[J]. Clinic Micro Bio Infect, 2014, 20(2): 75-82.
[13]Islam MA, Khatun MM, Werre SR, et al. A review of Brucella seroprevalence among humans and animals in Bangladesh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and control opportunities[J]. Veter Micro Bio, 2013,166(3):317-326.
[14]McGiven JA.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immunodiagnosis of brucellosis in livestock and wildlife[J]. Rev Sci Tech, 2013,32(1):163-176.
[15]李永霞.虎紅平板凝集試驗在家畜布氏桿菌病監測中的應用[J].中國畜牧獸醫文摘,2014,19(6):100.
[16]Asmare K, Sibhat B, Molla W, et al. The status of bovine brucellosis in Ethiopia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exotic and cross bred cattle in dairy and breeding farms[J]. Acta Tropica, 2013,126(3):186-192.
[17]Corrente, Marialaura, et al.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bovine brucellosis using B. melitensis strain B115[J]. J Micro Bio Meth, 2015,119(7):106-109.
[18]Kim JY, Sung SR, Lee K, et al. Immunoproteomics of Brucella abortus RB51 as candidate antigens in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brucellosis[J]. VeterImmun Path, 2014,160(3):218-224.
[19]Saxena HM, Chothe S, Kaur P. Simple solutions to false results with plate/slide agglutination tests in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man and animals[J]. Methods X, 2015,2(4):345-352.
[20]Chothe SK, Saxena HM. Innovative modifications to Rose Bengal plate test enhance its specificity, sensitivity and predictive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brucellosis[J]. J Micro Bio Meth, 2014,97(1):25-28.
[21]Galińska EM, Zagórski J. Brucellosis in humans--etiology, diagnostics,clinical forms[J]. Ann Agric Environ Med, 2013,20(2):233-238.
[22] 張改文,史新濤,郝衛芳,等.布魯氏菌病三種診斷方法的比較[J].中國動物檢疫,2013,30(10):38-40.
[23] Hajia M, Fallah F, Angoti G, et al.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diagnosing brucellosis[J]. Lab Med, 2013,44(1):29-33.
[24] Tekin R, Ceylan TF, Ceylan TR, et al. Brucellosis as a primary cause of tenosynovitis of the extensor muscle of the arm[J].Infez Med, 2015,23(3):257-260.
[25] Ay N, Kaya S, Anil M, et al. Pulmonary Involvement in Brucellosis, a Rare Complication of Renal Transplant: Case Report and Brief Review[J]. Exp Clin Transplant, 2016,10(2):231-236.
[26] Bilici M, Demir F, Yolmazer MM, et al. Brucella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J]. Balkan Med J, 2016,33(5):556.
[27] Lyapina EP, Shuldyakov AA, Evdokimov AV, et al. Inflammatory diseases of scrotal organs in patients with brucellosis: Improvement of therapy[J]. Terap Ark, 2014,87(11):56-61.
[28] Ahmed W, Zheng K, Liu ZF. Establishment of chronic infection: brucella′s stealth strategy[J]. Front Cell Infect Micro Bio, 2016,6(83):157-159.
[29] Albayrak F, Cerrah S, Albayrak A, et al. DRESS syndrome with fatal results induced by sodium valproate in a patient with brucellosis and a positive cytoplasmic antineutrophilic cytoplasmic antibody test result[J].. Rheumatology Inter, 2012,32(7):2181-2184.
貴州省科技廳基金資助項目(黔科合LH[2015]7480號)。
陳澤慧(E-mail: czhtyb@163.com)
10.3969/j.issn.1002-266X.2017.07.034
R516.7
A
1002-266X(2017)07-0104-04
2016-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