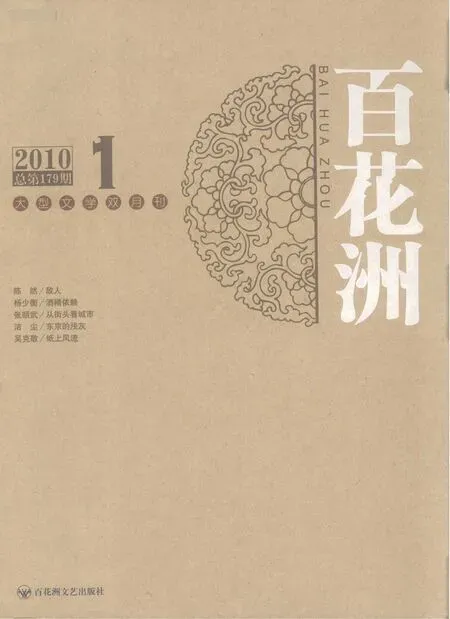疾病與刀子(創作談)
我記得看到過這樣一份統計數據,現在全國的憂郁癥患者已經達到了1.8億人。我覺得自己早就是一個想象力格外發達的人了,但現實生活里的殘酷和嚴重還是讓我感到了慚愧。也就是從那個時刻起,我會時不時地朝自己發問,你該不會也是一個患有憂郁癥的人吧?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社會怎么了,在它看上去一派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下,到底隱藏了哪些讓人憂郁的景象?我們從一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時代里走出來,經過短短數十年的發展,不但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秩序,而且成了這個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不但再也不用擔心挨餓受凍了,而且很多都住進了高樓,開上了汽車,沒事的時候還可以邁出國門去溜達一圈,這樣的盛事又豈是我們那些倒霉的先輩能夠逢得上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之間,我們這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里卻又被1.8億憂郁癥患者充滿了,我寧愿相信是那個做這項統計的人在成心抹黑我們的時代,不僅如此,那些經受不住憂郁癥痛苦折磨而從高樓上往下跳的身影,都是我在真假不明的狀態中產生的可怕幻覺。
我喜歡過一個可敬的日本導演,他的名字叫山本薩夫,看他后期的幾部電影,我覺得他拍攝的簡直就是發生在中國的故事,就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那些左鄰右舍的故事。山本薩夫不僅有一雙格外敏銳的眼睛,能夠從燈紅酒綠的社會表層下看到它所遮蔽著的丑惡和不幸,而且手里握有一把格外鋒利的刀子,毫不客氣地把那層阻隔我們看到真相的表皮切開,讓所有的殘酷和悲摧都一覽無余地袒露在我們面前。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良知、勇氣和擔當。
其實,《大聲呼喊》寫的并不是一個有關“憂郁癥”的故事,雖然里面的主人公的確被不負責任的醫生診斷為憂郁癥患者,故事的發生背景也的確就是我們這個被1.8億憂郁癥患者所充塞的時代。確切說,這部作品其實寫的是一個關于“歷險”的故事:主人公們為了揭開籠罩在自己和身邊人身上的謎團,不得不去遙遠的烏龍鎮去探一次險,因為事情的真相與那個似有若無的村莊相關……當然,你也可以把主人公在這部作品中的所有行為都視為一次歷險,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使用所有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對待他人和社會,這樣的人生行為如果不是歷險的話還有什么能夠算得上是歷險呢?但這些幾乎不能為他人所知曉的可恥行為一旦從主人公們自己的口中說出,卻無形中又給我們增加了幾分理解和原諒的成分,回顧我們自己的人生,難道我們不能從他們身上找到自己奮斗歷險的影子嗎?
沒錯,在《大聲呼喊》中,“憂郁癥”幾乎成了一個解說主人公行為的由頭,正是因為它的作祟,他們當然還有我們那些不堪的行為到底發生過,還是僅僅出自我們的幻覺,他人又怎么能夠說得清呢?說到這里,我不得不和盤托出我使用“憂郁癥”這個讓我倍感興趣的病理學名稱的真實目的了。正像我們認為“魔幻現實”并不僅僅是發生在美洲大地上的現實狀況而已經成了一種創作方法一樣,“憂郁癥”在這部作品中的意義同樣不僅僅是疾病類型而也是一種創作方法了,正是憑著這個方法,作品在不斷地建構的同時,又在不斷地解構,事情剛剛呈現一種看似真實的狀態,卻即刻又被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狀態打破了,正應了那句頗含哲理的俗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相到底在哪里?我們似乎永遠不知道,或者干脆說,真相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這自然離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相去甚遠。在經過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破局和突圍之后,盡管我們現在的文學風尚越來越趨向于保守,但那些呼吁回到現實主義老路上去的叫囂,肯定都是一廂情愿且不切實際的幻想。《大聲呼喊》是我脫離開現實的羈絆后寫作最為自由暢快的一部作品,在此之前,我一直處在戴著鐐銬跳舞的寫作狀態中,對于類似天馬行空的寫作狀態只是視為遙遠不可企及的理想,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一回,但在寫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卻不能不欣喜地告訴你們,我真的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