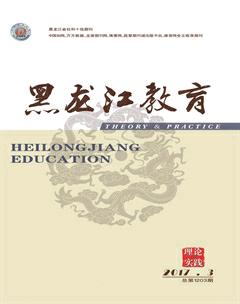李勇杰:17年打造功能神經外科“中國隊”
李穎
外表儒雅、平和的李勇杰卻有著一顆“不安分”的心。當精英們爭先恐后出國時,他回國發展了,理由很簡單:就想回國做點事;當大家熱衷美國綠卡時,他淡然放棄了,理由同樣很簡單:不過是一張居住證;當很多醫學“大咖”安心享樂時,他開始“辦醫”了,理由依然很簡單:探索分級治療。
1998年,在出國潮面前,他帶著前沿技術回國,成為國內“細胞刀”第一人;他用17年時間打造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功能神經外科“中國隊”,讓數以萬計的腦病患者恢復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功成名就后,他選擇“辦醫”,探索分級治療……
他就是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主任、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李勇杰教授,他在2016年獲得了第二屆北京市華僑華人“京華獎”。
對于獲獎,他直言:“真的很意外,不禁反問自己,國內外那么多優秀的人才,我是最優秀的那一個嗎?”
被“細胞刀”震撼 找到事業方向
采訪李勇杰,國內“細胞刀”第一人的稱號是永遠繞不過去的話題。
盡管他不愿再提,但他對十幾年前的那個場景依然記憶猶新。
“哦,它停下來了,10年了。”一位美國原發性震顫癥女患者淚流滿面。在通過“細胞刀”治療后,幾秒之內,患者右手劇烈的震顫消失了。
當時正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李勇杰,被這種手術療效深深地吸引了,那一刻的震撼是如此強烈而復雜,整個世界的喧囂都好像靜了下來,他聽到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一定要掌握這項技術!”
看著“細胞刀”這一先進的醫療技術幫助國外眾多患者解除了痛苦,恢復了健康,李勇杰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前途和得失,而是國內正被疾病折磨、忍受著無盡痛苦的患者。
像當初“走出去”一樣,在美國生活優渥的李勇杰做出了讓周圍人不能理解的選擇—帶著“細胞刀”技術回國。
1998年,作為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留學尖子人才”,李勇杰將世界前沿的醫學理念、理論和技術帶回祖國,他來到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功能神經外科領域的臨床治療和科研機構—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很快,被稱作“細胞刀”的微電極導向立體定向療法風靡全國。而北京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國帕金森病基金會授予“卓越成就臨床中心”,成為當時亞洲唯一獲此殊榮的臨床機構。
嘗試挑戰才能獲得快樂
當一個人在某一領域取得了成功,他往往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享受成功所帶來的一切,安于現狀;一是不滿足于當前的成功,繼續尋找挑戰,在進行新的嘗試的同時也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李勇杰顯然屬于后者。
做一名有科學家氣質的醫生,帶領一支技術過硬的團隊,為醫療領域創建新技術、新理念和新模式,是李勇杰一直以來的追求。
1999年3月,功能神經外科研究所應用丘腦底核毀損技術治療帕金森病獲得成功,同年又開展腦深部電刺激技術即“腦起搏器”治療術治療帕金森疾病;1999年,首例全身性扭轉痙攣的手術獲得了成功;1999年,首例痙攣性斜頸、舞蹈癥以及抽動穢語綜合征等手術相繼獲得了成功。
李勇杰在創造性地把手術的治療范圍拓展到其他運動障礙性疾病之后,又開始了癲癇、椎間盤突出癥和慢性疼痛的治療,至今已拓展到30多種疾病。自2009年起,該研究所的帕金森病“腦起搏器”治療量達到全球第一,該研究所成為“腦深部電刺激全球最大治療中心”。
從“細胞刀”到“腦起搏器”,從帕金森病、癲癇到微創椎間盤手術和慢性疼痛治療,李勇杰不斷嘗試新的挑戰,并從中獲得快樂。追求完美的李勇杰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科學家型的醫生,要有科學家的頭腦,要做研究搞創新。
成為患者求醫的“終點站”
面對為給家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變得一貧如洗的家庭,李勇杰的心情是沉重的。幾經考慮,李勇杰提出了“終點站”概念。“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要不斷跟蹤和通曉國內外的前沿技術,要讓自己的診療成為患者求醫的‘終點站。”
“解除病人的痛苦,是我最大的夢想。在這個過程中,我很快樂,也很享受。”但是一個從7歲就患有腦癱的患者卻讓李勇杰很糾結。“可以說我是看著這個孩子長大的。”李勇杰透露,十幾年過去了,這個孩子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了,他每年都會從安徽來趟醫院,一是為說聲感謝,二是問問是否有了最新的醫療進展。每次見到這個孩子,李勇杰心里都是酸酸的。“明明有辦法可以治這類疾病,但就是因為藥進不來,‘無米下炊,所以患者就要遭罪。”說起患者,謙和的李勇杰突然變得激動起來,“每天100微克的巴氯芬就可以減輕患者的痛苦,就是因為獲利不大且審批煩瑣,藥始終進不了國內市場。”
他懇請媒體幫助呼吁一下:看著他們受罪,我很心痛但卻無能為力。
十幾年來,李勇杰和團隊從帕金森病的治療入手,逐漸將技術運用于其他運動障礙病,拓展了癲癇、疼痛、腦癱以及精神外科領域,累計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患者10余萬人,還積極舉辦學習班培訓了6000多名技術骨干,讓功能神經外科在全國各大醫院落地生根。
探索分級診療的新路
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懈的努力與付出,最終成就了李勇杰。
作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李勇杰時常思索國家的醫療體制改革。“我們一直在說分級診療、雙向轉診,解決大醫院看病難的問題,病人卻只增不減,這不是很奇怪嗎?”愿望和現實的落差促使“愛琢磨”的李勇杰思考問題產生的原因。李勇杰給出的“處方”是“專家不沉下去,改變不了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門可羅雀的狀態。大醫院越建越大,結果是建多大都不夠用”。
李勇杰又一次“不安分”起來,他希望創辦一個“能夠吸引專家”的基層醫療機構,在他的努力下,西典門診于2014年10月應運而生。作為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的醫聯體,西典門診借社會資本辦醫之政策激勵,取美歐之成熟技術和服務模式,讓中國人不出國門,享受國際水準的醫療服務,同時又將其作為分級診療模式的試點。
在李勇杰的規劃中,西典門診還扮演著“平臺”的角色。“北京市衛計委對多點執業的鼓勵是極為正確的,是撬動將來醫療改革的著力點。”李勇杰表示,自己親力親為地建立西典門診,為之配備一流的設備和最好的執業環境,就是想讓醫生們放心將其作為第二行醫地點。
在西典門診,沒必要的藥不開,沒必要的檢查不做,治療同樣病癥的總費用由此得以控制在與公立醫院相當甚至更低的程度,而病人們則享受到層流潔凈和恒溫的空氣,以及一對一全程陪護的就醫體驗。“西典門診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醫保問題上的平等政策。”
“西典門診只做微創局麻手術,急難重病人則轉診回宣武醫院,分級診療就這樣實現了。”
從學醫、從醫再到辦醫,在內斂的李勇杰身上,始終有一抹理想主義色彩。“我就想闖一條這樣的路,在各界期盼醫改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大背景下,做一點東西進行探索。”
西典門診被李勇杰當作自己的一個“孩子”,這里承載著他好幾重的情懷和理念。
(本文轉自《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