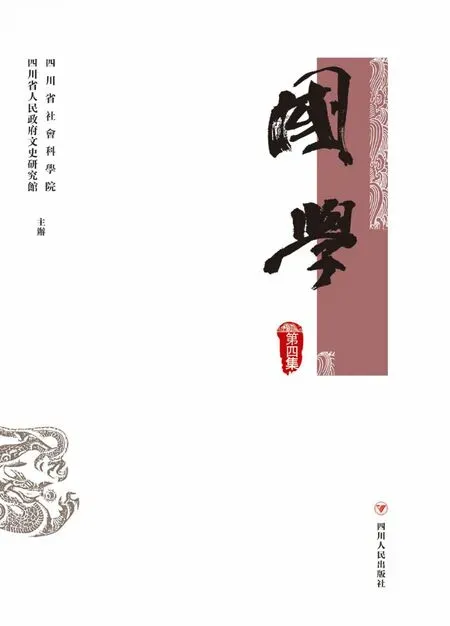《説文》“蝒”“蠜”解詁
——兼議蜀方言三種昆蟲的得名
《爾雅·釋蟲》:“蝒:馬蜩。”《説文》從《爾雅》之説,亦以“馬蜩”釋“蝒”。漢代以後的學者,大多堅持“馬蜩”即“大蟬”的觀點,如《爾雅》“蝒”下郭璞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蟬。”郝懿行疏云:
《初學記》引孫炎曰:“蝒,馬蜩,蟬最大者也。”今此蟬呼爲“馬蠽蟟”,其形龐大而色黑,鳴聲洪壯,都無回曲。《本草》云:“蚱蟬生楊柳上。”此蟬之聲似之。今馬蠽蟟好登樹顛,尤喜楊柳林中噪,殆此是矣。[注]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5頁。
郝疏確認“馬蜩”即《本草》所載之“蚱蟬”。

凡言馬者謂大,馬蜩者,蜩之大者也。《方言》曰:“蟬,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蝒、馬二字誤倒。此篆不與下文“蜩、蟬、螇、蚗”諸篆爲伍,不得其故,恐是淺人亂之耳。[注]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6頁。
段注亦堅信“馬蜩”即“大蟬”。
究竟是許慎並不以“馬蜩”爲“大蟬”,或者《爾雅》的“馬蜩”原本就不是“大蟬”呢,還是《説文·蟲部》的“蝒”篆確係“淺人亂之”呢?此問題之一。
以上兩個問題,既涉及到《説文》“蝒”和“蠜”的確切含義,又關係到《説文》篆文的排序體例,不可不辨。
筆者不揣淺陋,擬對兩個問題試作解答,尚祈時賢不吝賜教以正謬誤。
一、釋“蝒”
要弄清“蝒”爲何物,應當瞭解以下幾個問題。
(一)《説文·蟲部》的排序規律
《説文》一共收録篆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個、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九千三百五十三個篆文被分爲五百四十部,其分部的原則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五百四十部誰先誰後的安排,是按照“同條牽屬,共理相貫”的原則來執行的。至於同一部類中的篆文,則按照“雜而不越,據形繫聯”的原則來安排。至於“重文”(異體字),許氏將它們分別附在正體篆文之後並加以説明。
這裏最需要瞭解的是“雜而不越,據形繫聯”的原則,在《説文·蟲部》篆文的安排上是怎樣體現的。“雜而不越”,是説同一部類中的事物種類繁多,應當使它們各歸其類,不得超越;“據形繫聯”,是説使各類事物歸類的方法是:根據形貌特點及相關特性來歸類。“蟲”類動物種類繁多,記録蟲類名稱及其相關概念的篆文的數量,也比其他許多部首的字要多得多。《説文》是怎樣“據形繫聯”的呢?

用現代昆蟲學分類標準來考察,《説文·蟲部》的小類,已經達到“科”的層次。而《爾雅·釋蟲》和《方言》對“蟲”的歸類,大多僅達到“目”的層次。古代不少學者由於沒有考慮到這種差別,又因爲《爾雅》是“經”,往往是以《爾雅·釋蟲》來規範《説文·蟲部》的篆文排序,勢必會有削足適履的弊端。這是我們介紹《説文·蟲部》篆文排序規律的用意所在。
(二)“淺人亂之”的可能性不大

《説文》流傳到段玉裁生活的時代,已經1600多年。在這1600多年的傳承過程中,縱然有“淺人亂之”,難道會沒有“通人正之”?要知道,《説文》並非一般的文化典籍,它是爲古人“解經”而作的文字學著作,問世之後的一千多年來,早已成爲歷代先儒必備的工具書。以先儒訓釋經典的習慣,對《説文》如此明顯的“謬誤”,絶不會視而不見、聽之任之。


段注難以自圓其説者有三:


第三,段注謂《方言》“蝒馬”係將“蝒、馬二字誤倒”,無非是爲了強調“凡言馬者謂大”,以説明“馬蜩”即大蜩、即大蟬。但是,如果“蝒”即“馬蜩”、即“大蟬”,那麼“馬蝒”當如何理解?難道有“大大蜩”“大大蟬”之説?可見,段氏對“蝒馬”的理解,由於對“蝒”的理解有誤而産生錯誤。
(四)馬蜩、蝒馬與“灶馬”

但“蝒”(馬蜩)究竟是哪一種與蟋蟀形貌相似的昆蟲呢?
根據《説文》排序的規律,“蝒”一定是蟋蟀科昆蟲;從“馬蜩”“蝒馬”都含有“馬”字來看,它讓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灶馬”。“灶馬”是什麼樣的昆蟲呢?請看《辭海》關於“灶馬”的介紹:
灶馬:昆蟲綱,直翅目,蟋螽科;體粗短,長約二十毫米,背駝,觸角甚長,翅退化,後足發達,能跳躍;穴居性,常成群棲於暗濕處,是屋內灶前常見的昆蟲。[注]《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
根據《辭海》對“灶馬”體貌特徵和生活習性的介紹,這“灶馬”應當就是我們川西人叫作“灶雞母”的昆蟲。
有關“灶馬”得名的原因不得而知。至於得名的時間,最晚也在唐代,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七·蟲篇》載:“灶馬:狀如促織稍大,足長,好穴於灶側。俗言‘灶有馬,足食之兆’。”“促織”是北方人對蟋蟀的俗稱。《酉陽雜俎》是將“灶馬”作爲灶神的動物圖騰來介紹的,故引“俗言”爲證。可見早期的“灶神”傳説中,“灶馬”就是灶神。後來的灶神傳説將“灶馬”人格化,但“灶馬”之名被保留了下來,故《漢語大詞典》“灶馬”條載:“灶馬:木刻印刷在紙上的灶神像。”
中國的灶神傳説起於何時不得而知,但不會晚於戰國時代,因爲《莊子·達生》就有相關記載:“沈有履,灶有髻。”司馬彪注:“髻,灶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注]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五,《諸子集成》(三),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8頁。


《爾雅》《方言》在昆蟲介紹上都有兩個很顯著的特點:一是一蟲數名或者數蟲同名,二是一音多字或者一字多形。這樣的後果是:後世的訓釋者各逞臆説,令今天的讀者莫衷一是。下面舉兩個典型的例子來説明。

清人錢繹著《方言箋疏》,關於“蝒馬”的解説文字多達六百餘字,仍不得要領,最後只好作這樣的説明:
諸物並以“馬”字居上,此獨言“蝒馬”者,猶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以螳蜋爲“天馬”耳。郭氏據《爾雅》“蝒:馬蜩”之文以相訾議,不思子雲所採,乃異國殊語,當時必有“蝒馬”之稱,而後載入《方言》,不必盡與《爾雅》相合。故張揖著《廣雅》亦有此文,且其所進《書表》云:“八方殊語,庶物異名不在《爾雅》者,詳録品核,以著於篇。”若以“馬蜩”爲句,則“蝒:馬蜩”三字已見《爾雅》,必不然矣。[注]錢繹:《方言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14~615頁。
按:錢繹的意思是説,如果將《爾雅》中的“蝒馬蜩”三字作兩種斷句來理解,一種是“蝒:馬蜩”,這樣,《方言》説蟬的別名有“蝒馬”,就跟《爾雅》不合;一種斷句是“蝒馬:蜩”,這樣不就跟《爾雅》一致了嗎?
這樣的強爲之解,實屬無奈之舉,用於《方言》尚可,用於《説文》就行不通了,因爲《説文》“蝒”篆下爲“馬蜩也”,“馬”非篆文,不可能合爲“蝒馬;蜩”。使郭璞、段玉裁、錢繹等人疑惑、無奈的根本原因,均在不解“蝒”爲“灶馬”,皆因“灶馬”之名不載經典而不得而知也。
清人郝懿行著《爾雅義疏》,於“蒺蔾:蝍蛆”條下,解説文字多達四百字左右,最後只得説:“未識是何物耳,姑存之俟知者。”關於“蝍蛆”,郭注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郝疏徵引各家,有説是“蜈蚣”的,有説是“蟋蟀”的,有説是“蜻蛚”的,有説是“蚱蜢”的。郝氏均覺不妥,最後只得“以俟知者”。
搜索《百度百科》,獲知“灶馬”有灶馬蟋、灶蟋、灶蟀、灶雞、灶鴨、灶馬蟋蟀等各種稱謂,並且明確指出:“屬直翅目蟋蟀科,體長十五至二十八毫米,身寬五至五點五毫米。”這應當是“蝒”即灶馬、灶馬即“灶雞母”的鐵證。
(五)“灶雞子”的得名
問一個不識字的川西人“蟋蟀”是什麼,至少百分之九十的人回答不了;但是説到“灶雞子”,便很少人會不知道。對川西人來説,“灶雞子”已經不是蟋蟀一般意義上的方言稱謂了。
前人考證説,蟋蟀之名“蛐蛐”“促織”,是源於人們擬其叫聲而得名。那麼,蟋蟀之名“灶雞子”是源於什麼呢?

下面説“灶雞子”的得名。
“灶馬”跟蟋蟀同爲蟋螽科昆蟲,且形貌相似,它們的主要差別是:灶馬長約兩厘米,體型較大,而且背駝;蟋蟀長約一厘米,體型較小,背平。相比之下,灶馬仿佛成年婦女,蟋蟀有如少年兒童。蜀人命名極善聯想,且多諧趣。因此,將灶馬比作母親,將蟋蟀比作子女,這樣的聯想非常自然。灶馬既有“灶雞母”之名,蟋蟀之名“灶雞子”便不難理解。相沿成習之後,民間百姓都將蟋蟀呼作“灶雞子”,以致很少人知道它的學名叫蟋蟀了。從淵源上看,如果沒有“灶雞母”的得名,應該是不會有“灶雞子”的得名。因爲“灶雞子”(蟋蟀)主要活動範圍是在野外草叢中,跟“灶”是毫不沾邊的。
看來,許慎所理解的“馬蜩”(蝒)跟衆人完全不同,或許只有他的理解纔符合《爾雅》“蝒馬蜩”三字的本義。《方言》的“蝒馬”不爲郭璞等人所理解,是郭璞等人既不知“馬蜩”爲何物,卻又泥於《爾雅》“蝒:馬蜩”所致。如今弄清楚“馬蜩”即“灶馬”,上述諸多疑慮便煥然冰釋了。
二、釋“蠜”
郭璞於“阜螽”下注:“《詩》曰:趯趯阜螽。”於“草螽”下注:“《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據郝疏:“草螽,《詩》作‘草蟲’,蓋變文以韻句。蟲、螽,古字通也。”是郭璞不以“阜螽”“草螽”爲一蟲:“趯趯”者是“阜螽”,“喓喓”者是“草螽”。[注]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8頁。
這樣一來,《説文·蟲部》的“蠜”,就既可能是“阜螽”,也可能是“草螽”。
關於“阜螽”的解説,郝疏全文如下:
《春秋·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説文》“螽”“蝗”互訓。螽或作,《春秋》書“螽”,《公羊》作“”。牟廷相説:“《詩》云‘衆維魚矣’,衆疑之省文,蓋、魚相化協於夢占。”牟説是也。“阜螽:蠜”者,阜螽名蠜。《詩》作“阜螽”,《正義》引李巡曰:“阜螽,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然則“螽”爲總名,“阜螽”亦螽之統稱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蝩’。蝩蓋螽之或體,簸蝩即阜螽,聲之轉也。[注]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8頁。
筆者按:以上郝疏文字可以概括爲三點內容:第一,《爾雅》五“螽”無非是各種蝗蟲的分類;第二,“阜螽”也可以理解爲各種蝗蟲的統稱;第三,“阜螽”有可能就是“簸蝩”。不難看出,這樣的解説,説了等於沒説。但有一個資訊還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五“螽”都是蝗蟲。
關於“草螽”,郝疏的全文是:

筆者按:郝疏認爲,“草螽”應當是河北、山東一帶呼作“聒聒”(即“蟈蟈”)的昆蟲。《辭源》從郝疏,於“草螽”條云:“蟲名,雄者鳴如織機聲,俗稱蟈蟈、織布娘。”其“織布娘”,即通常所説的“紡織娘”。
由此看來,《説文》的“蠜”,如果是“阜螽”,那就是蝗蟲類昆蟲;如果是“草螽”,那就是蟈蟈或者“紡織娘”。


那麼,《説文·蟲部》的“蠜”究竟是什麼昆蟲呢?
四川地區有兩種跟蟋蟀非常相似的昆蟲,除“灶雞母”(灶馬)之外,還有一種被川西人叫作“油和尚”或者“和尚頭兒”的昆蟲。“油和尚”與蟋蟀的酷似程度,遠勝於“灶雞母”。“油和尚”的體型、大小、長短、顏色、跳躍方式和速度,以及生活習性等,都跟蟋蟀一般無二,並且經常伴隨蟋蟀出沒於草叢中。筆者兒時跟同伴們一起到野外逮“灶雞子”的時候,常常將“油和尚”當作“灶雞子”,同伴們告訴我:“灶雞子”是“枋子腦殼”(説明:川西人把棺材叫作“枋子”,把棺材蓋子兩端扁平上翹的部分叫作“枋子腦殼”),“油和尚”是圓腦殼。也就是説,“油和尚”跟蟋蟀的主要區別,僅在於頭的形狀。蜀人不知道這種昆蟲的學名,就根據它頭型的特點,叫它做“和尚頭兒”;又因爲蜀人將跳躍速度快叫作“油”,如稱蚱蜢(蝗蟲)叫“油蚱蜢兒”,於是又把這種酷似蟋蟀的昆蟲叫作“油和尚”。
以“油和尚”釋“蠜”,應當最符合許慎的本意。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除“灶雞母”(灶馬)、“油和尚”之外,再沒有能與“灶雞子”(蟋蟀)爲伍的蟋蟀科昆蟲了。蟈蟈雖然“狀類蟋蟀”,但是其體型比蟋蟀要長大數倍(蟋蟀長約十毫米,蟈蟈長約四十至五十毫米),更大的區別還在於,蟈蟈通體青色,而“油和尚”與蟋蟀都是黑褐色並且有光澤。這是斯螽科昆蟲與蟋蟀科昆蟲的主要區別,很可能也是《説文》不讓螽蝗類昆蟲與蟋蟀類昆蟲爲伍的主要原因。
第二,以“油和尚”釋“蠜”,與段注所引《詩經·召南·草蟲》文義相合。如果“蠜”是“阜螽”,但這個“阜螽”並非所謂“蝗子”,而是我們這裏所説的“油和尚”,那麼《草蟲》首章兩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的文義便怡然理順了。按郝疏所云,“草蟲”即草螽,草螽即蟈蟈。蟈蟈善鳴,故謂之“喓喓草蟲”;“油和尚”善跳,故謂之“趯趯阜螽”。

但是,無論是《説文》用字有誤,還是《爾雅》解説有誤,按照《説文》篆文的排序規則來看,用“油和尚”釋“蠜”都無疑是正確的。
結 語
釋《説文·蟲部》“蝒”“蠜”二篆之疑,可謂感慨良多。若非《説文》有“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雜而不越,據形繫聯”之排序宗旨,筆者豈敢妄議段氏之誤?段氏由此生疑,筆者亦由此生疑而議段氏之誤,孰是孰非,尚待時賢及後之博雅君子。

釋“蝒”“蠜”二篆之疑,得蜀語三蟲之實,若非妄言,豈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