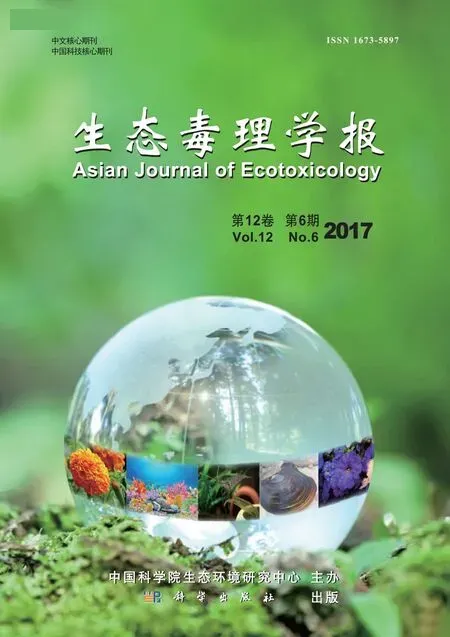獸藥類環境內分泌干擾效應及評價研究進展
姜錦林,單正軍,卜元卿,韓志華,王娜
國家環境保護農藥環境評價與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南京 210042
獸藥也稱獸用藥或動物用藥,是指用于預防、治療、診斷動物疾病或者有目的地調節動物生理機能的物質(含藥物飼料添加劑);根據使用目的,獸藥大致可歸納為4類:1)一般疾病防治藥;2)傳染病防治藥;3)體內、體外寄生蟲病防治藥;4)飼料添加劑(包括促生長藥)。其中除防治傳染病的生化免疫制品(菌苗、疫苗、血清、抗毒素和類毒素等),以及畜禽特殊寄生蟲病藥和促生長藥等專用獸藥外,其余均與人用醫藥相同,只是劑量、劑型和規格有所區別。
獸藥在保障動物健康、提高畜禽產品質量尤其在畜牧業集約化發展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獸藥和飼料添加劑的大量使用成為生態環境污染和人體健康損害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大量外源性化學物進入畜禽產品中,使動物性食品中藥物殘留越來越嚴重,對人類的健康和公共衛生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大部分獸藥和添加劑以原藥和代謝產物的形式經動物的糞便和尿液進入生態環境中,對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造成污染,影響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正常生命活動,并通過食物鏈最終影響人類的健康。研究表明,很多作為促生長劑而廣泛應用于養殖業的人工合成雌激素類獸藥是典型的環境內分泌干擾物。這類物質脂溶性強,在水源和土壤中很難降解,可以通過食物鏈進入生物體內,對人類的健康及生物的生存產生巨大影響[1-5]。
所謂內分泌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ors),一般是指環境中存在的能夠干擾生物體內源激素的合成、釋放、轉運、結合、作用或清除,從而影響機體的內環境穩定、生殖、發育及行為的外源性物質[6];環境中存在的多種內分泌干擾物與生物體內天然激素受體選擇性結合而產生的如上所述的多種生物效應,即內分泌干擾效應。環境中的許多化合物具有內分泌干擾作用,這些化學物質性質差異極大,包括難降解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如多氯聯苯、二噁英、有機氯農藥等)和易分解的極性殺蟲劑、除草劑、洗滌劑降解產物、動物及人類排泄的激素、天然植物激素、微生物毒素以及某些重金屬等。值得注意的是,廣泛使用的口服避孕藥和一些用于家畜助長或免疫的同化激素(獸藥)中含有大量的人工合成雌激素,如己烯雌酚、乙烷雌酚、炔雌醇等[2]。近年來,人們認為許多健康受損現象的發生均與環境雌激素有關,包括:人類隱睪癥與尿道下裂等疾病發病率提高,男性平均精子數量減少,女性不孕明顯上升,水生動物出現雌性化現象等[7-9]。獸藥污染造成的內分泌干擾風險因此引起國內外政府機構、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調研了典型獸藥的污染現狀及其內分泌干擾效應研究最新進展,并以傳統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研究方法為基礎,較全面地評述了可用于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的快速篩選、檢測及評價方法,并對該領域未來研究提出了展望和建議,以期為環境和農業等管理部門制定獸藥的使用、排放、管理政策提供科學依據,促進我國畜禽養殖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1 獸藥在環境中的殘留現狀(Veterinary drup residus in the environment)
隨著集約化養殖業的發展,獸藥和飼料添加劑的使用量正日漸增加,動物在使用藥物以后,藥物將以原形化合物或代謝產物的方式從糞、尿等排泄物進入外界環境,造成環境土壤、表層水體、植物和動物等的獸藥蓄積或殘留。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中都有低濃度的獸藥檢出,抗生素及驅蟲藥物對生態環境的潛在危害尤為突出。
抗生素和激素類獸藥也可通過污染食品而進入環境,如預防和治療畜禽疾病用藥和促進生長、泌乳、甚至肌肉脂肪分配而使用的藥物,這些藥物主要通過口服、注射、局部用藥等方法給藥,藥物由于殘留動物體內而污染食品;此外,殘留大量獸藥的動物糞便和污水處理廠的污泥用于農田施肥,也會污染土壤和水體;在水產養殖業中,藥物作為飼料添加劑或通過水中撒藥形式給藥而被直接投加到水中,據統計,70%以上的藥物可通過這種途徑直接進入到水環境。20世紀90年代末,歐洲的一些國家開始比較系統地調查、研究環境中獸藥的殘留和污染問題,我國起步較晚,直到近年來才開始廣泛關注獸藥殘留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危害。表1顯示了常見抗生素和激素類獸藥在環境中的殘留現狀[4,10-12]。此外,與其他環境介質相比,一些抗生素和激素類獸藥,如氟喹諾酮類(FQs)抗生素,在污泥中的污染更加嚴重。對北京8個污水處理廠的調查發現,污泥中氧氟沙星殘留濃度高達21 mg·L-1,而國外FQs在污泥中普遍檢出濃度在0.04~8.3 mg·kg-1范圍內[13-14]。畜禽糞便中,抗生素和獸藥污染更是普遍嚴重,曾有學者檢測到我國豬糞中恩諾沙星濃度高達33.26 mg·kg-1[14]。可見,我國抗生素和獸藥類污染已相對嚴重。
由此可見,獸藥污染已成為一個全球性普遍存在的問題,大多數獸藥具有較高的生物活性,其必然存在一定的潛在生態環境風險。尤其是抗生素和激素類獸藥殘留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的威脅日益暴露。
2 獸藥內分泌干擾效應研究現狀(Research status of veterinary endocrine disrupting effects)
2.1 內分泌干擾物分子作用模式
內分泌干擾物的分子作用模式主要是具有與生物體內源激素相似結構的外源化學物質通過結合細胞外受體,轉運至細胞核內同啟動子位置結合,從而啟動目的基因的表達,因而可模擬、阻止或干擾雄激素、雌激素、甲狀腺激素等內分泌過程,此途徑稱之為受體介導途徑[6, 15]。此外,環境中還存在大量化學物質,其化學結構與生物體內源激素結構并不相同,但也可表現出內分泌干擾物效應。這可能是污染物直接影響了生物體內的與激素合成相關酶的活力,以及通過破壞內源激素及其受體的生成、代謝、轉運、信號轉導等途徑,從而干擾生物體內內分泌,如許多化學物質可通過干擾與類固醇激素生物合成路徑中相關的基因表達和酶的活力影響性激素的含量,這些作用稱之為非受體介導途徑[6, 15]。
對于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研究,長期以來集中在污染物對動物生殖器官的作用。然而,生物機體的生長發育、繁殖等受內分泌系統和體內復雜信號通路的調控,這種調控方式常以網絡的形式存在,互相影響并相互補償,以應對環境因子的影響。在脊椎動物體內,下丘腦-垂體-性腺/甲狀腺/腎上腺軸在動物的繁殖、生長發育、免疫等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大腦作為控制內分泌系統的核心綜合部位,發育中的神經系統對于內分泌干擾物的作用非常敏感。因此,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可能對動物完整內分泌系統產生作用,影響動物的生長發育及繁殖等。另外,神經內分泌系統也是許多有機污染物作用的主要靶器官之一,這些物質可以引起大腦永久性的結構及功能的改變,直接影響內分泌功能[6]。

表1 常見抗生素和激素類獸藥在環境中的殘留Table 1 Veterinary antibiotics and hormone residues in the environment
2.2 典型獸藥的內分泌干擾效應研究
2.2.1 己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DES)
DES是一種非甾體類雌激素,能產生與天然雌二醇相同的所有藥理與治療作用。DES曾作為促生長劑而廣泛應用于畜禽生產中,Lorenz等[16]首次報道給小公雞皮下植入DES,8周后公雞的胸部和腿部肌肉脂肪含量增加了3倍;Rumsery等[17]試驗結果證明肉牛通過每日口服10 mg DES,能增強體內蛋白質沉積和增加日增重,可以很快產生顯著和直接的經濟效益。除歐盟以外的許多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都曾把人工合成雌激素(主要是DES)用作促生長劑。
DES是親脂性物質,性質較穩定,不易降解,易在人和動物脂肪及組織中殘留,長期服用會導致肝臟損傷。DES具有明顯的毒副作用,DES應用早期就曾有人報道過DES對小鼠具有致癌性,但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大量的動物試驗才證明在孕期服用DES會增加其后代患生殖道癌癥的風險,如陰道和子宮頸透明細胞腺癌、陰道癌、子宮內膜癌、睪丸異常等。研究表明,與DES致癌性關系最密切的是女性陰道和子宮頸透明細胞腺癌。此外,DES還會導致陰道癌、子宮內膜癌和乳腺癌等,現在大多數女孩月經初潮明顯提前也與DES有關;孕期服用DES不僅對女性后代造成嚴重危害,對男性后代的危害更是不可忽視。婦女孕期服用DES易導致男性后代睪丸異常、發育不全、精子計數減少和精子活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殖系統問題;孕期服用DES會導致胎兒早產,影響胎兒性別分化和生長發育,還會導致胎兒腦癱瘓、失明和其他神經缺陷[18]。
動物實驗表明,Mikkil?等[19]就新生小鼠睪丸組織對DES的敏感性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所有接觸過DES的小鼠其血液中的睪丸激素均減少。長期攝入DES會導致雄性雌性化,造成嚴重的“陰盛陽衰”。Shukuwa等[20]發現,DES會導致雄鼠催乳素細胞密度明顯增加。當水體中DES 濃度為1 ng·mL-1時,可導致雄性日本青鳉兩性化,5~10 ng·mL-1則完全雌性化[21]。對真鯛幼魚的雌激素效應研究表明,暴露于一定濃度(0.08、0.8、8.0 μg·L-1)DES 42 d,真鯛幼魚的肥滿度均極顯著下降,血漿中卵黃蛋白原被誘導產生,肝胰臟指數和血漿蛋白總量顯著升高,顯示DES具有明顯的雌激素效應[22]。新生期注射DES后在BALB/c小鼠中脾細胞黃體生成素的表達顯著減少,且雌性小鼠對DES的敏感性大于雄性小鼠,表明DES能影響小鼠的免疫器官[23]。用量為0.3和3 mg·kg-1的DES能促使幼年香豬睪丸生殖細胞數顯著增多,而使睪丸支持細胞數量顯著減少;不同劑量的DES都具有促進幼年香豬睪丸和附睪中肥大細胞增多的作用,且具有劑量相關性[24-25]。此外,己烯雌酚還能誘導泥鰍紅細胞產生異形細胞、異常核和微核,說明己烯雌酚對泥鰍紅細胞的形成有明顯的致突變作用[26]。
2.2.2 喹乙醇
喹乙醇屬于喹噁啉類,是一種曾在畜禽及水產養殖中廣泛使用的抗菌促生長劑,是我國養殖飼料中最常用的獸藥及飼料添加劑之一,其不僅對于魚類和禽類具有較強的急性毒性作用,而且作用于動物后會嚴重損害動物肝腎組織,引起機體生理生化指標的變化等亞慢性毒性反應。喹乙醇以原形或代謝物的方式從動物糞、尿等排泄物進入生態環境,或者以漁場水體直接用藥的方式,造成土壤環境、表層水體、水生和陸生生物的喹乙醇殘留蓄積,進而引起生態毒性。在實際生產中,喹乙醇由于不當用藥而引起養殖動物中毒甚至死亡的現象時有發生。
據報道,喹乙醇對大型蚤(Daphnia magna)的急性毒性較強,作為漁場的飼料添加劑,喹乙醇對水環境有潛在的不良作用[27]。此外,喹乙醇還可顯著影響斑馬魚的胚胎發育過程,有明顯的致畸作用;可以引起鯉魚腎細胞DNA的明顯損傷,致染色體斷裂,具有潛在的遺傳毒性,應該嚴格控制喹乙醇在水產養殖中的使用,消除其對魚類等水生生物、人體和環境的潛在危害[28]。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喹乙醇還對內分泌免疫系統產生作用,通過原代細胞培養,高于0.3 μg·mL-1濃度的喹乙醇可顯著導致草魚肝細胞和胰腺外分泌部細胞的脂肪積累,抑制草魚胰腺外分泌部細胞胰蛋白酶原的合成;當添加喹乙醇1.8 μg·mL-1時,可導致部分草魚胰腺外分泌部細胞形態發生病理變化[29]。給小鼠灌喂不同劑量喹乙醇,發現大劑量喹乙醇會抑制機體的紅細胞免疫功能;小鼠的胸腺指數和脾指數隨著喹乙醇劑量的增大均不同程度降低,說明大量使用喹乙醇可能會抑制胸腺的發育,對脾臟的重量也有一定影響,致使小鼠的免疫機能下降[30]。
2.2.3 大豆異黃酮
大豆異黃酮是植物雌激素,黃酮類化合物中的一種,主要存在于豆科植物中,大豆異黃酮是大豆生長中形成的一類次級代謝產物。由于是從植物中提取,與雌激素有相似結構,可通過與雌激素受體(ER)結合表現出雌激素的生物學活性,緩解圍絕經期婦女的臨床癥狀;可促進和誘導淋巴細胞的轉化與增殖,維持自身免疫穩定性和巨噬細胞的吞噬能力,增加圍絕經期婦女的免疫功能[31]。大豆異黃酮作為一種新型的飼料添加劑,具有良好的抗病和促生長作用,能增強機體免疫力,提高產奶量,改善乳品品質,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有無污染、無殘留、無抗藥性等優點,但是就其是否會增加乳腺癌、子宮內膜癌以及對生育能力產生影響仍存在很大的爭議,還需進一步研究。吳靜等[29]研究表明,大豆異黃酮可增加卵巢大鼠血清E2水平,作用稍弱于傳統雌激素,但可以明顯增加CD3+淋巴細胞數、CD4+淋巴細胞數、CD4+/CD8+細胞比例的值和胸腺的重量。近期研究表明,大豆異黃酮能影響雄性生殖激素分泌、睪丸和附睪組織的生長發育、睪酮合成相關酶的活性以及大腦中生殖激素基因的表達,并與劑量有關,對雄性動物生殖系統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不容忽視。
大多種內分泌干擾藥物的長期毒害效應體現在它們具有傳代效應,這其中牽涉到表觀遺傳狀態的改變。激素類獸藥引起傳代效應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引起DNA甲基化圖式的改變。烯菌酮是一種殺菌劑,也是環境激素的一種,暴露于烯菌酮或其他幾種物質中的水蚤的DNA甲基化水平會發生穩定持續地降低,且這種變化可在其后代沒有受過其影響的世代中出現[33]。烯菌酮處理F0代鼠后,在F3代鼠的精子中也會發現DNA甲基化狀態的改變,證明潛在的間接遺傳異常現象和表觀遺傳傳代繼承的存在[34]。暴露于17α-炔雌醇一段時間后,成年斑馬魚肝臟中卵黃蛋白原I基因的5'側翼的甲基化水平下降,表明由雌激素誘導的卵黃蛋白原表達涉及到DNA甲基化水平的改變[35]。
從目前的研究報道來看,大多數試驗得到的獸藥對生態環境的毒性效應經常是在大大高于實際環境濃度的情況下得到的,觀察到的多數是藥物的急性毒性結果,而實際環境濃度條件下獸藥的生態毒性較小,但是應該考慮到,部分獸藥持續地進入環境且難以降解,加之環境污染物常以低劑量復合形式存在,其對生物的潛在影響常常是難以通過短期的試驗觀察到的,因此需建立可靠的低劑量復合長期暴露的方法學,關注激素獸藥的低濃度復合作用下的內分泌干擾作用研究。為降低獸藥應用風險,應該研究減少、避免和消除獸藥在生態環境中殘留的方法和措施。通過完善獸藥監控體系,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優化畜禽的給藥方案,研制和推廣使用天然藥物等方法,減少或避免獸藥殘留。
3 可應用于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篩選的方法建議(Proposal of screening method for veterinary drug class of endocrine disruptors)
就目前已建立的較成熟的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快速篩選和檢測方法,可以歸為4大類研究方法:模型動物篩選法、組織器官篩選法、細胞篩選法和分子篩選法[36]。具體篩選和檢測方法可應用于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的研究,下面就其中可用于評價獸藥內分泌干擾效應的指標,分別闡述如下:
3.1 模型動物篩選法
主要包括大鼠子宮增重法和水生生物形態學變化觀察法。大鼠子宮增重法步驟固定且篩選程序簡單,是最為成熟的篩選檢測環境雌激素的體內實驗方法之一,選用未成熟的雌幼鼠或摘除卵巢的雌成鼠為研究對象,以口服或皮下注射的方式,將實驗動物連續3~4 d暴露于待測化學物質,然后剝離受試對象的子宮并測定對照組與實驗組子宮的脂肪、干重或濕重與體重的比值,進而評價待測化學物質是否具有促進子宮生長的作用,判斷其是否具有雌激素效應[37,38]。而水生生物形態學變化觀察法則是選用魚類或甲殼類動物等水生生物作為模型生物,根據其形態特征的改變用于篩選具有雌激素活性及雄激素活性的化學物質,但這種形態學指標不如細胞或分子水平上的指標精確度高。
3.2 組織器官篩選法
主要是競爭性雌激素受體結合法(Competitive Estrogen Receptor Binding Assays):具有雌激素效應的內分泌干擾物可以在特定器官內(如肝臟)與雌激素受體結合,啟動信號傳導途徑,誘導產生細胞應答,并最終表現為卵黃原蛋白(vitellogenin,VTG)等終端產物的生成,既可以通過測量受體結合力,又可以通過監測終端產物的產量,較為靈敏地監測出待測物對生物體造成的內分泌干擾影響。美國環境保護局(EPA)已將雌激素受體結合法廣泛應用于環境內分泌干擾物的前期快速篩選步驟中。
3.3 細胞篩選法
包括細胞培養檢測法和酵母雌激素篩選測試法。前者除了能夠通過特定器官內的細胞應答誘導生成生物標志物以外,具有雌激素效應的內分泌干擾物還可以對含有雌激素受體的人乳腺癌細胞系產生細胞應答[39],這其中應用最廣泛的即為MCF-7細胞增殖實驗(MCF-7 cell proliferation bioassay)[40];酵母雌激素篩選測試法則是利用特定生物標志物,如卵黃原蛋白等建立重組酵母篩選系統,將轉基因酵母作為生物模型,利用受體-配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內分泌干擾物的檢測,該方法操作簡便、耗時短、靈敏度極高,一般比MCF-7 細胞增殖實驗和子宮增重方法高出2~5個數量級。
3.4 分子篩選法
主要是免疫檢測法,其基本原理是生物分子(受體)與相應的特異性抗體(單克隆抗體或多克隆抗體)結合,然后利用同位素、酶、熒光或化學發光底物等標記技術加以顯示,根據生物分子被誘導產生的水平判斷化學物質是否具有內分泌干擾特性[41]。免疫檢測方法主要包括放射免疫分析法、酶免疫測定法、熒光免疫分析法、時間分辨熒光免疫分析法和化學發光免疫測定法,其中以酶聯免疫法(EIA)和放射免疫法(RIA)最為常用。選取方便高效的生物標志物是各種免疫檢測法中的關鍵所在,卵黃原蛋白是應用最早也是最為廣泛的篩選類雌激素化合物的生物標志物,其中卵黃原蛋白的酶聯免疫吸附方法最為方便,檢出限可達2~6 ng·mL-1。此外,卵殼前體蛋白(choriogenin,CHG)也是魚類中研究得較多的一種生物標志物。隨著內分泌干擾分子機制研究的進展,芳香化酶mRNA、ERβ mRNA等越來越多的分子標志物被發現可用于內分泌干擾物質篩選[36]。
這4種研究水平的檢測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動物模型整體水平的檢測法可以較為真實可靠地反映出獸藥是否能夠作為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對生物體造成危害,但耗時耗材、精確度低;組織與器官水平的檢測法較動物活體檢測要方便,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檢測出某些需要經過體內代謝活化才會發揮性激素作用的化學物質;細胞檢測法同樣采用宏觀指標,但更為快速、便捷,應用較廣泛;分子檢測法敏感度最高、耗時最短,可大大提高檢測效率,并越來越多地向實踐應用方向發展[36]。
3.5 實驗動物選擇原則
在干擾物篩選方法的應用中,選擇的實驗動物種類不但包括嚙齒類和靈長類,還涉及到魚類、鳥類和兩棲類、爬行類等。模式生物的選取應遵循一定的原則:1)實驗動物易于獲得并易于在實驗室培養;2)生長迅速,生活周期短;3)基礎生物學研究比較深入,前期研究實驗數據較豐富。不同實驗動物靶標有著不同的優缺點,如現有的一些脊椎動物靶標,其中大鼠就有個體太大和飼養周期太長的缺點。就目前的研究現狀和水平,國內實驗室較易開展的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篩選研究的模型生物有小型魚類模型和兩棲類模型,前者包括黑頭軟口鰷魚(fathead minnow,Pimephales promelas)、日本青鳉(Japanese medaka,Oryzias latipes)和斑馬魚(zebrafish,Brachydanio rerio)。根據不同水平的評價體系,魚類內分泌干擾效應的評價終點可見表2。兩棲動物生活周期比較復雜,幼體生長速度快,食物鏈中具有水陸兩棲的獨特地位,卵、鰓和皮膚具有滲透性,能對污染物富積和放大,從而成為環境污染的前哨物種。目前適用于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篩選的兩棲模型動物種類有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和熱帶爪蟾(Xenopus tropicalis),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近年來,也有學者推薦家蠶可作為內分泌干擾效應的動物靶標[42],可通過調查家蠶的性腺指數、性腺的組織病理學變化,產卵能力、子代孵化率、以及生殖發育關鍵基因的變化等指標,篩選可用于生殖毒性評價的生物標志物。但是,昆蟲與哺乳動物在進化程度上有較大差異,將其內分泌干擾效應借鑒到哺乳動物甚至人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目前關于獸藥內分泌干擾效應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有關內分泌干擾物的篩選方法很多,并且日趨豐富,在今后的研究上應重點加深對干擾作用機制的研究。針對不同類型的獸藥種類,根據其可能干擾內分泌系統的不同途徑,選擇合適的實驗動物模型以及合適的篩選方式,并結合使用其他方法來輔助研究其潛在的內分泌干擾作用。
4 內分泌干擾物評價方法進展(Advances in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endocrine disruptors)
發達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對內分泌干擾物進行研究,并相繼發表了專題報告。OECD、美國、歐盟、日本等均建立了內分泌干擾物篩選檢測的基本框架,并不斷完善。目前,OECD內分泌分級篩選和檢測框架草案已提出,美國一級篩選各試驗的指導原則已完善,歐盟在建立優先名錄上取得了不錯的進展[43]。我國包括獸藥在內的潛在內分泌干擾物的內分泌干擾效應的評價方法和篩選體系可參考美國EPA和OECD等發達國家和組織的經驗建立。US EPA提出的內分泌干擾物篩選和檢測的基本框架包括初級分類(Initial Sorting)、優先選擇(Priority Setting)、一級篩選(Tier 1 Screening,T1S)、二級檢測(Tier 2 Testing,T2T)[44]。歐盟對內分泌干擾物篩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優先名錄的確定[42]和內分泌干擾物對水生生物的研究[46]。歐盟于1999年制定了內分泌干擾物的策略包括短期、中期和長期措施。短期和中期的重點是為優先名錄收集相關資料,以指導研究和監測,確定消費使用的具體情況和生態暴露情況。
OECD于2002年制定了內分泌干擾物檢測與評價基本框架,并于2012年對其進行了修訂[47],包括5個層次評價,其中第一層次為利用化合物現有數據和非試驗信息進行初篩,包括化合物的物理化學特性,從標準和非標準測試得到的所有可用(生態)毒理學數據;交叉參照、化學分類、定量-活性關系(QSARs)和其他電腦模擬預測,以及藥物代謝性質(ADME)模型預測等。第二層次為體外測試,要求對提供特定內分泌作用機理/途徑數據進行篩選,包括雌激素或雄激素受體結合試驗、雌激素受體轉錄激活、雄激素或甲狀腺激素轉錄激活、體外類固醇生成和MCF-7細胞增殖測試(ER拮抗劑/興奮劑)等。

表2 魚類內分泌干擾效應評價終點Table 2 Assessment endpoints of endocrine disruption effects on fish
第三層次為體內測試(哺乳類和非哺乳類方法),對提供特定內分泌作用機理/途徑數據進行篩選,其中哺乳類測試包括子宮增重法和赫什伯格法;非哺乳類測試包括爪蟾胚胎甲狀腺激素信號通路測試、兩棲動物變態測試、魚類繁殖篩選測試等。第四層次也是利用更多體內測試(哺乳類和非哺乳類方法),提供更加豐富的內分泌相關終點的有害效應數據。第五層次為體內測試(哺乳類和非哺乳類方法),對提供大量生物體生命周期更多內分泌相關重點的有害效應數據進行判斷,其中哺乳類測試包括一代延伸繁殖毒性測試和兩代繁殖毒性測試;非哺乳類測試包括魚類生命周期毒性測試(FLCTT);青鳉多代測試(MMGT);鳥類兩代繁殖毒性測試和大型溞多代測試等。
我國尚未建立相關內分泌干擾物篩選和檢測體系指導原則,因此包括獸藥在內的潛在內分泌干擾物均無成熟的評價體系。截至目前為止,一般針對獸藥的毒理學檢測評價方法也只主要包括急性毒性、慢性毒性、遺傳毒性、致畸性和致癌性毒理學試驗等,許多獸藥具有內分泌干擾作用,用現有的毒理學評價方法標準有可能檢測不到其潛在的毒性作用。國內開展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的研究相對較晚,未來需要借鑒國際上已有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在國外研究評價的基礎上,對國內可能有內分泌干擾效應的獸藥進行全面研究,做出科學評價,并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內分泌干擾物篩選和評價體系,進而應用在獸藥類潛在內分泌干擾物的管理當中。
5 展望及建議(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1)雖然我國獸藥污染現狀及其潛在內分泌干擾風險已經引起相關管理部門和研究人員的重視,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針對包括激素類獸藥在內的具有潛在內分泌干擾性質的污染物的篩選研究還遠遠不夠,且對不同種類動物的內分泌干擾作用機制的研究并不透徹,在今后的研究上應重點加深對干擾的作用機制的探討;
2)需要借鑒國際上已有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建立起符合我國特點的獸藥分泌干擾作用的評價體系,這需要開發靈敏高效的離體評價體系,并需要分別以不同的實驗動物,包括魚類、兩棲類、鳥類及哺乳動物的活體評價模型,為潛在獸藥類內分泌干擾物的危險控制提供可靠的實驗方法和技術;
3)包括獸藥在內的環境污染物常以低劑量復合形式存在,因此建立可靠的低劑量復合長期暴露的方法學,以便開展污染物對實驗動物低劑量復合暴露下的內分泌干擾作用的研究。
[1] Colborn T, Clement C. Chemically-induced Alterations in Sexual and Functional Development—The Wildlife/Human Connection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Scientific Pub Co, 1992: 403
[2] 安婧, 周啟星. 藥品及個人護理用品(PPCPs)的污染來源、環境殘留及生態毒性[J]. 生態學雜志, 2009, 28(9): 1878-1890
An J, Zhou Q X. Pollution sources, environmental residues, and ecological toxicity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A review [J].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9, 28(9): 1878-1890 (in Chinese)
[3] 張志美, 郭時金, 張穎, 等. 獸藥殘留對環境的影響[J]. 動物醫學進展, 2011, 32(8): 104-107
Zhang Z M, Guo S J, Zhang Y, et al. Advanc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J]. Progress in Veterinary Medicine, 2011, 32(8): 104-107 (in Chinese)
[4] 馬驛, 孫永學, 陳進軍, 等. 獸藥殘留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研究進展[J]. 中國獸醫科學, 2010, 40(6): 650-654
Ma Y, Sun Y X, Chen J J, et al. Advanc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J]. Chinese Veterinary Science, 2010, 40(6): 650-654 (in Chinese)
[5] 趙丹宇. 食品中激素類、抗生素類物質的殘留污染及管理[J]. 中國食品衛生雜志, 2003, 15(1): 58-64
Zhao D Y. Contamination and control of hormone and antibiotic residues in foods [J].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ealth, 2003, 15(1): 58-64 (in Chinese)
[6] 史熊杰, 劉春生, 余珂, 等.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毒理學研究[J]. 化學進展, 2009, 21(Z1): 340-349
Shi X J, Liu C S, Yu K, et al. Toxicolog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J]. Progress in Chemistry, 2009, 21(Z1): 340-349 (in Chinese)
[7] 張信連, 楊維東, 劉潔生.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對生物和人體健康的影響[J]. 國外醫學: 臨床生物化學與檢驗學分冊, 2005, 26(6): 349-351
Zhang X L, Yang W D, Liu J S.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to organisisms and human health [J]. Foreign Medical Sciences (Section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2005, 26(6): 349-351 (in Chinese)
[8] 解美娜, 張才喬, 曾衛東, 等.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對動物繁殖機能的干擾作用及其機制[J]. 中國獸醫學報, 2004, 24(1): 101-103
Xie M N, Zhang C Q, Zeng W D, et al. Mechanisms of the disrup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ers on animal reproduc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Veterinary Science, 2004, 24(1): 101-103 (in Chinese)
[9] 劉菲, 蒲力力.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對男性生殖健康影響的研究進展[J]. 生殖醫學雜志, 2006, 15(6): 425-428
Liu F, Pu L L. Research progress i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on male reproductive health [J].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2006, 15(6): 425-428 (in Chinese)
[10] Karci A, Balcioglu I A. Investigation of the tetracycline, sulfonamide, and fluoroquinolone antimicrobial compounds in animal manure and agricultural soils in Turkey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9, 407(16): 4652-4664
[11] Watkinson A J, Murby E J, Kolpin D W, et al. The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s in an urban watershed: From wastewater to drinking water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9, 407(8): 2711-2723
[12] 邰義萍. 珠三角地區蔬菜基地土壤中典型抗生素污染特征研究[D]. 廣州: 暨南大學, 2010
Tai Y P. The study on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antibiotics in soil from vegetable fields of Pearl Delta Area [D].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2010 (in Chinese)
[13] Gao L, Shi Y, Li W, et al.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s in eight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in Beijing, China [J]. Chemoshpere, 2012, 86(6): 665-671
[14] 孟磊, 楊兵, 薛南冬, 等. 氟喹諾酮類抗生素環境行為及其生態毒理研究進展[J]. 生態毒理學報, 2015, 10(2): 76-88
Meng L, Yang B, Xue N D, et al. A review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ecotoxicology of fluoroquinolone antibiotics [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2015, 10(2): 76-88 (in Chinese)
[15] 伍吉云, 萬祎, 胡建英. 環境中內分泌干擾物的作用機制[J]. 環境與健康雜志, 2005, 22(6): 494-497
Wu J Y, Wan Y, Hu J Y.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Health, 2005, 22(6): 494-497 (in Chinese)
[16] Lorenz F W. Fattening cockerels by stilbestrol administration [J]. Poultry Science, 1943, 22: 190
[17] Rumsey T S, Oltjen R R. Fate of radiocarbon in beef steers implanted with 14C-diethylstilbestrol [J].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1975, 40: 550-560
[18] 黃芬, 葉紹輝, 龔振明. 己烯雌酚的研究進展[J]. 中國畜牧獸醫, 2007, 34(2): 51-54
Huang F, Ye S H, Gong Z M. The development of diethylstilbestrol [J]. China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2007, 34(2): 51-54 (in Chinese)
[19] Mikkila T F, Toppari J, Paranko J. Effects of neonatal exposure to 4-tert-octylphenol, diethylstilbestrol, and flutamide on steroidogenesis in infantile rat testis [J]. Toxicological Sciences, 2006, 91(2): 456-466
[20] Shukuwa K, Izumi S, Hishikawa Y, et al. Diethylstilbestrol increases the density of prolactin cells in male mouse pituitary by inducing proliferation of prolactin cells and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gonadotropic cells [J]. Hist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2006, 126(1): 111-123
[21] 李俊鎖, 邱月明, 王超. 獸藥殘留分析[M].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2: 1
[22] 吳翠琴. 己烯雌酚和辛基酚對真鯛幼魚的雌激素效應研究[J]. 水產科學, 2008, 27(12): 611-614
Wu C Q. Estrogenic effects of diethylstilbestrol and octylphenol on juvenile genuine porgy Pagrosomus major [J]. Fisheries Science, 2008, 27(12): 611-614 (in Chinese)
[23] 朱虹, 衛蘭, 王文彥, 等. 己烯雌酚對小鼠脾細胞黃體生成素表達的影響[J]. 現代預防醫學, 2008, 35(22): 4446-4449
Zhu H, Wei L, Wang W Y, et al. Effect of diethylstilbestrol on the expression of luteinizing hormone in cell of mice spleen [J].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2008, 35(22): 4446-4449 (in Chinese)
[24] 田興貴, 李江森, 主性,等. 己烯雌酚對幼年香豬睪丸細胞的影響[J]. 畜牧獸醫學報, 2010, 41(11): 1510-1514
Tian X G, Li J S, Zhu X, et al. The effects of DES on the testis cell of Xiang Pig [J]. Acta Veterinaria et Zootechnia Sinica, 2010, 41(11): 1510-1514 (in Chinese)
[25] 田興貴, 李江森, 主性,等. 己烯雌酚對幼年香豬睪丸肥大細胞數量的影響[J]. 西南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2011, 33(8): 27-30
Tian X G, Li J S, Zhu X, et al. Effects of DES on the number of mast cells in the testis of immature Xiang Pig [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1, 33(8): 27-30 (in Chinese)
[26] 葉盛群, 唐正義. 乙烯雌酚對泥鰍紅細胞的誘導作用[J]. 內江師范學院學報, 2006, 21(6): 52-54
Ye S Q, Tang Z Y. Inductive effects of diethylstilbestrol in erythrocytes of Misgurnus anguillicadatus [J]. Journal of Neijang Teachers College, 2006, 21(6): 52-54 (in Chinese)
[27] Wollenberger L, Halling-S?rensen B, Kusk K O. Acute and chronic toxicity of veterinary antibiotics to Daphnia magna [J]. Chemosphere, 2000, 40(7): 723-730
[28] 李兆利, 陳海剛, 徐韻, 等. 3種獸藥及飼料添加劑對魚類的毒理效應[J].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 2006, 22(1): 84-86
Li Z L, Chen H G, Xu Y, et al.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three veterinary drugs and feed additives on fish [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06, 22(1): 84-86 (in Chinese)
[29] 何春鵬, 王恬, 劉文斌. 喹乙醇對草魚肝細胞和胰腺外分泌部細胞的毒理研究[J]. 浙江大學學報: 農業與生命科學版, 2006, 32(6): 651-657
He C P, Wang T, Liu W B. Toxicological effect of olaquindox on liver cells and pancreas exocrine cells of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gricutural & Life Science, 2006, 32(6): 651-657 (in Chinese)
[30] 尹榮煥, 白文林, 吳長德, 等. 喹乙醇對小鼠免疫器官及紅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J]. 安徽農業科學, 2007, 3(3): 717-718
Yin R H, Bai W L, Wu C D, et al. Effect of olaquindoxl on the immunity organ and red cell function of mouse [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7, 3(3): 717-718 (in Chinese)
[31] Ryan-Borchers T A, Park J S, Chew B P, et al. Soy isoflavones modulate immune function 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06, 83(5): 1118-1125
[32] 戴述誠, 李志業, 葉勇, 等. 新型綠色飼料添加劑——大豆異黃酮[J]. 中國動物保健, 2013, 15(9): 15-18
Dai S C, Li Z Y, Ye Y, et al. A new green feed additive, soybean isoflavone. [J]. China Animal Health, 2013,15(9): 15-18 (in Chinese)
[33] Vandegehuchte M B, Lemiere F, Vanhaecke L, et al. Direct and transgenerational impact on Daphnia magna of chemicals with a known effect on DNA methylation [J].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Part C: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2010, 151(3): 278-285
[34] Guerrero-Bosagna C, Settles M, Lucker B, et al. Epigenetic transgenerational actions of vinclozolin on promoter regions of the sperm epigenome [J]. PLoS One, 2010, 5(9): e13100
[35] Stromqvista M,Tooke N,Brunstrom B. DNA methylation levels in the 5' flanking region of the vitellogenin I gene in liver and brain of adult zebrafish (Danio rerio) —Sex and tissue differences and effects of 17 alpha-ethinylestradiol exposure [J]. Aquatic Toxicology, 2010, 98(3): 275-281
[36] 康亦珂, 汝少國, 王蔚.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快速篩選方法研究進展[J]. 科技導報, 2010, 28(12): 99-103
Kang Y K, Ru S G, Wang W. Progress in the rapid screening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2010, 28(12): 99-103 (in Chinese)
[37] Kang K S, Kim H S, Ryu D Y, et al. Immature uterotrophic assay is more sensitive than ovariectomized uterotrophic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estrogenicity of p-nonylphenol in Sprague -Dawleyrats [J]. Toxicology Letters, 2000, 118(1/2): 109-115
[38] Markey C M, Michaelson C L, Veson E C, et al. The mouse uterotrophic assay: A reevaluation of its validity in assessing the estrogenicity of bisphenol A [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01, 109(1): 55-60
[39] Korner W, Hanf V, Schuller W, et al. Development of a sensitive E-screen assay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strogenic activity in municipal sewage plant effluents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9, 225(1/2): 33-48
[40] Soto A M, Sonnenschein C. The role of estrogen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breast tumor cells (MCF-7) [J]. The Journal of Steroid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1985, 23(1): 87-94
[41] Estevez-Alberola M C, Marco M P. Immunochemical determination of xenobiotics with endocrine disrupting effects [J].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2004, 378(3): 563-575
[42] 沈衛鋒, 孟智啟, 蔡磊明. 家蠶——新的內分泌干擾物篩選靶標[J]. 生態毒理學報, 2015, 10(2): 154-158
Shen W F, Meng Z Q, Cai L M. Silkworm—A new target for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screening [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2015, 10(2): 154-158 (in Chinese)
[43] 譚彥君, 李寧. 國內內外分泌干擾物篩選評價體系研究進展[J]. 衛生研究, 2011, 40(2): 270-272
Tang Y J, Li 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screen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endocrine disrupters [J]. Journal of Hygiene Research, 2011, 40(2): 270-272 (in Chinese)
[44] US EPA.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chemical selection approach for initial round of screening, EPA-HQ-OPPT-2004-0109. [R]. Washington DC: US EPA, 2005
[45]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Strategy for Endocrine Disrupters“—A range of substances suspected of interfering with the hormone systems of humans and wildlife (COM (1999) 706), (COM (2001) 262) and (SEC (2004) 1372), SEC (2007) 1635 [R].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46] REACH.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 7b: Endpoint Specific Guidance [R]. Helsinki: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2008
[47] OECD. OEC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testing and assessment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Guidance Document 150 (Annex 1.4) [R]. Paris: OECD,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