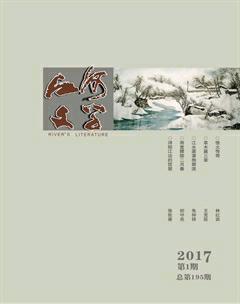江水潺湲抱郭流
朱仲祥
我生活在川西南的古嘉州樂山。這是一座傍水而居的城市,而且這座城市所依傍的不止一條兩條河流,而是很多條大小不等的江河溪流。這些縱橫交錯、汪洋恣肆的河流,織就一張巨大的水網,將我的城市嚴嚴地網在其中,形成水繞著城走、城漂在水上的獨特景觀。因此清代大詩人、大書畫家張船山寫詩贊道:“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湲抱郭流”。
這座以水為基調的城市,其發軔就與水有關。由于它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匯處,古時候這里經常發大水,給這片魚米之鄉帶來不少災難。戰國時期,開明王鱉靈,率領族人從荊楚之地沿長江而上,來到古蜀國的凌云山下,劈開烏尤山的阻遏,疏浚三江之水,并在這里扎下根來,在岷江東岸的三山九頂之上建起了開明王城。因水而生的開明故城,便成了其后犍為郡城和嘉定府城以及現代樂山城市的發軔之地。秦時蜀郡守李冰在這里二次治水,深挖了麻浩河床,增大了岷江的行洪能力,也進一步形成了“綠影一堆飄不去,推船三面看烏尤”的離堆景觀。到唐代,這里的先民為鎮三江水怪,在高僧海通和尚的倡議和川西節度使韋皋的主持下,經歷近90個春夏秋冬的艱苦鏖戰,在三江匯流處的絕崦丹崖上,修建了70多米高的凌云大佛,從此成為這座城市的地標。
“山水在城市中,城市在森林中”,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樂山的贊譽。凌云連綿的山峰如屏障一般橫亙在岷江對岸,白巖山、尖子山、虎頭山、老霄頂諸峰錯落在樓宇之間。但水依然是這座城市的主題元素。岷江從川西北高原逶迤而來,流經成都、眉山之后進入樂山,在城市北面稍作停留后,便在大佛腳下擁抱了青衣江、大渡河,然后攜手奔向滾滾長江一瀉東去。素有“川西玉帶”美稱的青衣江,穿過川西北高原的重重阻遏,越過“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的夾江千佛巖,在樂山城郊草鞋渡和大渡河相會。而發源于貢嘎山麓的大渡河,流經康巴藏區和小涼山區,進入沫若故里沙灣城區,再串起數十個翡翠般的沙洲后,在樂山中心城區與青衣江深情牽手。
圍繞這三條江河,城市周圍分布著由溪流河汊構成的若干水系。主城區鱗次櫛比的樓宇間,清澈的竹公溪由北向南穿城而過,形成一道綠蔭夾岸、小橋流水的水景觀;而青衣江西岸的蘇稽城區,秀麗的峨眉河帶著峨眉仙山的靈氣,在這里繞了一個優美的彎,留下一段田園牧歌般的風光之后,急切地撲進青衣江的千重碧波之中。從凌云山、烏尤山之間劈出的麻浩河,向南在牛華古鎮與流花溪匯合,涂抹出一片水鄉江南的圖畫后,再牽手涌斯江再注入滔滔岷江。同時,在樂山城郊的這些水系上,水庫、湖泊、堰塘星羅棋布,如古代有著名的明月湖、西湖塘,如今有佛光湖、碧山湖等,如仙女遺失的一面面銅鏡,給城市平添了幾多靈氣。
樂山市除三江匯流處的主城區外,還有沙灣和五通橋兩個傍水而居的城市組團。
來到位于城南十余公里的五通橋,你會被那里“十里山水十里城”的風光所迷住。你看,滔滔岷江繞城而過,茫溪河和涌斯江盤桓城中。在城里的兩河交匯處,形成一片數百畝的水域,綠水湯湯,碧浪千重,風光瀲滟,美不勝收。蔥蘢俊秀的菩提山矗立在城中,一道道綠水繞在山下。在青山和綠水之間,散布著童話般的城市樓宇。整個五通橋城區,仿佛被水托舉著、親吻著、擁抱著,城市矗立在水上,河水蕩漾在城中,山、水、樹、城相交相融,形成獨特的景色。清代詩人李嗣沆贊道:“垂楊夾岸水平鋪,點綴春光好畫圖;煙火萬家人上下,風光應不讓西湖。”五通橋因此有了“小西湖”的美譽。因了水的緣故,城市之間便出現了若干的橋,包括上百年的石拱橋、很現代的水泥橋、很別致很民俗的浮橋和彩虹橋。不僅橋多,水碼頭也著名。這里自古生產鹽巴,是享譽一方的鹽碼頭,自古鹽商云集,百帆競發,商貿活躍,百姓富庶,因而有了“金犍為”的美譽。五十年代,這里因水路暢通、鹽業發達、商貿繁榮,曾一度被周恩來總理特批為五通市。
沙灣城區位于主城區西南二十余公里,緊傍古稱沫水的大渡河,城下波濤拍岸,城后青山聳立,古人常用“綏山毓秀,沫水鐘靈”來描繪這里獨特的地理風貌。當你信步走過飛跨大渡河上的彩虹橋,站在河對岸看城市的風景,錯落十里的沙灣城區如海市蜃樓一般,那種漂浮在水上的感覺就特別明顯。這里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出生地,少年時郭沫若最愛去的地方,就是站在大渡河邊看飄逸的船帆和拉纖的船夫,到大渡河邊的茶溪垂釣,或者到溪邊的茶土寺折臘梅。有次他在茶溪釣魚,因專心讀書而忘了垂釣,魚竿不知什么時候被魚兒拖了去。他在生氣之后隨口吟出四句詩來:“閑釣茶溪水,臨風頌我書。釣竿含了去,不知是何魚。”(《茶溪》)而郭沫若的名字,就是取自故鄉的大渡河和古稱“若水”的青衣江,他故居前的明清古街也被叫做“沫水街”。洶涌狂放的大渡河一過沙灣,便進入平緩的嘉農、水口沖擊小平原,水流由一條分散成三條、四條,變得慵懶漫漶起來。這些漫漶的河流,給沙灣城區和主城區之間留下了星羅棋布的沙洲和濕地。
河流眾多,水系發達,灘涂濕地便多。站在赭紅色的樂山城垣上,便可望見凌云大佛對面的江心,一抹沙洲如綠色的鳳凰,翔舞在萬頃波濤之上,被當地人稱為“鳳洲島”。原來島上全是沙石,夏天洪水一來,便淹沒得沒有蹤跡,大佛腳下汪洋恣肆、茫茫一片。近十來年的夏天漲水,沖來了不少植物淤積在上面,水退后便魔幻般長出了一大片樹林和蘆葦叢,成了城市的一道景觀。如今,這里已打造成以鳳洲島為中心的城市濕地公園。而在大佛上游嘉定坊外,一到枯水季節便露出一片亂石雜陳的灘涂,這便是神話傳說中鱉靈斬殺惡龍的九龍灘。九龍灘盡管寸草不生,卻是野鴨、沙鷗、白鷺等水鳥們的天堂。它們或飛翔在河灘上,或信步在江水邊,成群結隊,野趣盎然。每當游船經過,它們就表演似的成群飛起,贏得中外游客一片喝彩。
在樂山近百平方公里的城區,像鳳洲島、九龍灘這樣的江心沙洲還有很多,單是從沙灣到老城區的一段河面,就有大小不一的島數十個,翡翠一般散落在大渡河上。其中不少沙洲都無人居住,成了被保護的天然濕地。這些濕地上,灌木遍地,蘆葦叢生,野花盛開,鷗鳥云集。也有一些有人居住的島,島中間是耕地和人家,島周邊是灘涂和濕地,人和野生動物在沙洲上和諧共生,構成一幅動人的圖畫。在這兩年進行的城市開發中,樂山人又在城市的“綠心”中,開辟了若干人工濕地,修建了不少水景觀,同樣吸引了許多白鶴、野鴨、沙鷗等水鳥來此棲息。正是這些灘涂和濕地,調節著城市的氣候,蘊育了城市的生機。
樂山人對水的熱愛和崇拜與生俱來,水圖騰和碼頭文化也應運而生。古時候,三江之濱建有龍王廟不下十處,沿江的居民都把風調雨順和行船平安的希望寄托于龍王,祈求神佛的保佑,如今只有五通橋的龍神廟碩果僅存。但每年端午賽龍舟的習俗保留至今,他們舉辦了若干屆聲勢浩大的樂山國際龍舟賽,賽龍舟、放河燈、搶鴨子等民俗活動豐富多彩。因為水上交通的順暢,商業貿易也非常繁榮,古代為“南方絲路”的交通要沖,三江之上舟楫往來,絡繹不絕。直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樂山水運還非常繁榮,郭沫若有詩云:“三兩漁火疑星落,千百帆檣載月收。”寫的就是那時樂山港的繁盛境況。
生活在樂山這座水城是幸運的。圍繞著水,我便多了許多生活的閑情逸致。比如邀約朋友到江邊親水的茶園喝茶,靜聽濤聲陣陣,閑看蘆葦飄雪;比如獨自漫步在赭紅的古城垣上,靜靜放飛思古之情懷,細心體驗劉禹錫“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詩句的深邃意味;比如到江邊散步,看人們打漁、垂釣或搬罾,感受水城的別樣風情;再比如去那些沙洲、灘涂和濕地,觀察鳥們詩意地飛翔和棲息。我最喜歡的還是看大渡河落日。每當天晴的黃昏時分,一輪落日便出現在城市西邊,燦爛的晚霞勾勒出峨眉清晰的山影,將大渡河映照得酒醉般緋紅,江心的波濤、沙洲以及山崖上的大佛、岸邊的城市,都被霞光涂抹得輝煌壯麗,整個畫面既熱烈又凝重,寫意著“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的古詩意境。隨著晚霞的漸漸消失,城市的華燈漸次亮了起來,夢幻般的燈光倒映在水中,閃閃爍爍如躍動的金子。此時你會想起郭沫若著名的詩句來:“遠遠的街燈明了,好像閃著無數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現了,好像點著無數的街燈。”
三面臨水,一面靠山。行走在這座山環水繞的城市,我更能感受到水對于生活非凡的意義。我想,正是因了水,才有了這座城市,才有了威鎮三江的樂山大佛;正是因了水,因了水中珠串般的沙洲濕地,城市的景色才多了幾分潤澤和生機,多了幾許內涵和魅力。
責任編輯:鄧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