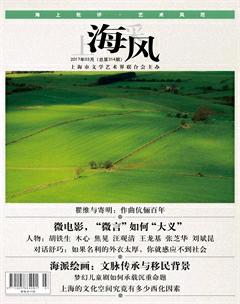瞿維與寄明:作曲伉儷百年文
馬信芳
作曲家瞿維與寄明同歲,今年是他倆的百年誕辰。此時此刻,不朽的作品——耳熟能詳的歌劇《白毛女》、歌曲《工人階級硬骨頭》、電影《鳳凰之歌》《燕歸來》《英雄小八路》的主題歌等等,一曲曲一首首在我耳邊想起。而寄明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來更是越發親切,因為它是今天每個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必唱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
我與瞿維先生相識于1983年。那年市文聯組織文藝家去安徽采風,期間上了黃山。同行的還有作家馮崗、艾明之、李楚成、費禮文,電影美術師韓尚義,淮劇表演藝術家筱文艷、漫畫家蔡振華、音樂家譚冰若等。想不到,66歲的瞿維先生竟還同我們小青年一起爬上了天都峰,領略了“鯽魚背”的險峻。當然,我責無旁貸地充當了先生的護衛。也因這段對于老年人來說有點“冒險”的經歷,我與瞿維先生成了“忘年交”。面對這位享有盛名的歌劇《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我自然沒有放過他,采風七天,一有空閑,我們就沉浸于交談中。他那不平凡的經歷令人起敬、令人難忘。回滬后,瞿維先生邀我去了復興西路上的寓所,也就在那里,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他的夫人、同為作曲家的寄明老師。以后,由于工作關系,我多次去寓所看望這對音樂界有名的伉儷。
出生于江蘇,相識于延安
瞿維,1917年5月出生于江蘇常州。自幼喜愛音樂和戲曲的他,讀初中時就積極參加學校的京劇愛好小組活動。1931年畢業于武進縣中學(今常州市實驗中學)。1933年隨姑媽來到上海,進入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學習音樂、美術和勞作。瞿維師從鐘慕貞教授學習鋼琴,打下了鋼琴演奏的良好基礎。在新華藝專期間,聶耳、冼星海成為他的楷模。1935年畢業后,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學音樂、美術教師。1938年5月于湖北宜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此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并以音樂藝術為武器,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1939年9月,經音樂家任光介紹,瞿維奔赴陜西宜川第二戰區民族革命藝術學院任音樂系主任。次年2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行的還有后來與他一起創作歌劇《白毛女》的作曲家馬可。
而此時,有“延安第一位女鋼琴家”之稱的寄明,早他半年來到了延安。1941年,兩位同為江蘇人,又是同齡的年輕人在這里相遇。寄明原名吳亞貞,江蘇淮安人,1917年6月出生于蘇州。來到延安之后,為了表達“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改名為寄明。
吳亞貞從小喜歡音樂,在中學求學的時候,已是學校業務樂隊的骨干。中學畢業后,報考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范科,并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在這里她主修鋼琴和琵琶。1937年畢業后,很有主見且有理想的她,告別家庭,從沿海深入內地,輾轉于貴州和四川,先后在貴陽、達縣的中學以及重慶教師服務團任音樂教師,并在重慶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任干事。民族的苦難,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腐敗,使她的藝術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聶耳和冼星海對她很有影響,她積極地宣傳和推廣兩位作曲家的救亡歌曲,并投身于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之中。
1939年8月,吳亞貞懷著追求光明的決心,沖破層層障礙,到達革命圣地延安,進入中共中央創辦的培養婦女干部的中國女子大學學習。改名為寄明的吳亞貞,1942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與瞿維一起成為延安魯迅文學藝術學院的教員。
鋼琴成“紅娘”,新歌劇誕生
1941年,在重慶的周恩來將一位愛國人士贈給他的德國鋼琴,轉送給了延安魯迅文學藝術學院。鋼琴在當時可謂是珍貴的樂器。林伯渠同志不知從哪里得到消息,得知寄明稱得上鋼琴演奏家,于是便把她從延安中國女子大學調到了魯藝。當時還規定,只有三個人有資格彈這架鋼琴,其中兩人就是寄明和她后來的丈夫瞿維。建國后,曾同在延安的音樂家黃準還回憶,“那琴,我們碰都不能碰的!”
在1980年第5期的《群眾音樂》上,瞿維、寄明夫婦合寫的《魯藝的一架鋼琴》講述了當年這架鋼琴的故事,文中兩人共同回憶了他們當時如何把這架鋼琴作為“武器”,為抗日戰爭服務的史實。當時,不僅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而且許多抗日將士都聽過他們的演奏。寄明還參加了《黃河大合唱》的伴奏,她演奏的樂曲曾鼓舞著很多革命戰士奔赴抗日戰場。
與此同時,這架鋼琴也成了瞿維與寄明的“紅娘”。1942年初,兩人在延安寶塔山下的窯洞里結為伴侶。可惜遠在常州和蘇州的兩老家家人都沒能看到這喜慶的場面,直到解放后,兩人才回到江蘇探親完婚。而極為珍貴的是,在延河畔,他們的好朋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和《延安頌》的曲作者鄭律成為寄明和瞿維拍下了一張合影——兩人穿著肥肥的棉衣棉褲,坐在小土堆上,臉上都架著斯斯文文的眼鏡,眼神中閃耀著對光明的憧憬和理想的光輝。照片是一個見證:當時,許多有志青年、知識分子披荊斬棘,沖破艱險,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兩個音樂人此時此刻的這張合影記下的是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同年5月,享有盛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這里召開。瞿維、寄明夫婦作為代表雙雙參加了座談會,并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20年后,1962年6月10日,寄明撰寫的《指路明燈》一文刊于《解放日報》上。文中,她深情回憶當年毛澤東在座談會上與他們交流的情況。合影時,現場氣氛輕松活躍。毛澤東和朱德同志分坐在近當中的地方,其他領導散坐在最旁邊,倒是藝術家坐在中間。前排,瞿維悠閑地架起了二郎腿,寄明則端莊地站在后排中間。寄明稱這次座談會使自己深刻認識到了創作與深入生活的關系。于是,她走出琴房,熱情學習陜北民間音樂,并開始用這古樸的音樂素材,豐富自己的創作。這種深入民間采風的作風貫穿了她的一生。
毋庸回避,作為“座談會”的產物,三年后,中國新歌劇的代表作《白毛女》,在魯迅文學藝術學院誕生。這是瞿維與馬可、張魯等人共同合作的重要作品。在當時及后來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此創作被稱作“中國歌劇創作的一個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劇在當時延安連演30多場,反應極為強烈,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斗志。《白毛女》的創作不僅對中國歌劇和其他藝術形式的創作產生過廣泛影響,而且對瞿維后來的創作也具有重要意義。
1946年馬可與瞿維寫的《〈白毛女〉音樂的創作經驗》一文中,他們這樣總結:“今天的新歌劇的作者必須深入群眾,體驗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和感情,熟悉他們的語言,在忠于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吸收民間形式的一切優點;同時也需要參考(不是硬搬)前人的和外國的經驗來創造真正代表人民大眾的新歌劇。”
這不但是當時的經驗之談,而且對瞿維后來的創作,乃至新中國音樂的創作一直影響、貫穿。1951年,瞿維與張魯合作了電影《白毛女》的音樂。1961年,他創作完成的管弦樂幻想序曲《白毛女》,以及于1974年根據舞劇《白毛女》的音樂編成的管弦樂組曲《白毛女》等,都可視為對同一題材的不斷深化和對相同音樂材料的更絢爛多彩的發揮。
打開國家文化部“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作品”名冊,芭蕾舞劇《白毛女》赫然在目。據不完全統計,自1965年這部完全由中國藝術家打造的芭蕾舞劇正式上演,到今天已演出二千多場。此劇主要編導、前上海舞蹈家協會主席胡蓉蓉和作曲家嚴金萱生前曾告訴我,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成功,除編導、作曲、演員等外,還有兩位大家功不可沒。一位是該劇的藝術指導、戲劇大師黃佐臨,是他提出將楊百勞喝鹽鹵自盡改為與黃世仁、穆仁智抗爭中被打死的意見;增加了喜兒由黑發變灰發、變白發的“荒山野林”的戲,這被贊為“春風吹又生”的創意,才使舞劇表演更加盡善盡美。另一位就是瞿維先生,他不僅參與了整部芭蕾舞劇音樂的修改工作,而且整整花了三個多月為總譜定稿。
《花鼓》慶勝利,教學赴東北
瞿維在這時期還有一部創作值得一提,那就是寫于1946年的鋼琴曲《花鼓》。這是一首極富中國民間特色、描寫解放區人民新生活的代表作。20世紀40年代,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苦難的年代,又是一個獲得新生的年代。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中國革命戰爭的開始,給我國民族帶來了希望的曙光,全國人民歡欣喜悅,作曲家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創作了這首表現解放區人民愉悅心情的鋼琴獨奏曲。
音樂表現了一個民間熱烈的歌舞場面。樂曲開頭的引子,摸擬民間鑼鼓的節奏和音響:一段開場鑼鼓過后,仿佛場面已經打開,而《鳳陽花鼓》的主題出來,歡悅的舞蹈才正式開始;中間段是輕歌曼舞,曲調是《茉莉花》的演變;中段過后,再現第一段的曲調,但通過新的鋼琴織體,音樂比開始時更為熱烈、歡騰。《花鼓》與此前的中國鋼琴曲相比,不僅具有更濃重的民間氣息,而且不失鋼琴的華美。專業人士當時就認為,這是用鋼琴這件洋樂器表現中國鄉土氣的成功創作,它開拓了鋼琴音樂美的新天地。
瞿維在回顧當年創作此曲時說:“我在這方面還注意到借鑒《牧童短笛》的寫作經驗。例如,那首樂曲中有一個在三和弦上附加六度音的和弦,我在《花鼓》中也采用了這種處理辦法。”因此,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可以說《牧童短笛》是中國音樂界20世紀30年代產生的一部有深遠影響的鋼琴作品,那么,誕生在40年代的《花鼓》,可以說是中國作曲家沿著探索民族風格的途徑,產生的又一部極有代表性的鋼琴佳作。
此曲于1946年由寄明在哈爾濱電臺首次廣播演出。建國初期,上海中國唱片廠灌制了鋼琴家李嘉祿演奏的《花鼓》唱片,同時,又出版了《花鼓》的樂譜,于是得以在國內廣泛地傳播,成為我國音樂舞臺上一首常演不衰的鋼琴樂曲。1950年代后我國鋼琴家周廣仁、劉詩昆等將此曲帶到國際舞臺上演奏,開始了它的海外之旅。1960年代初《花鼓》被編入《高等音樂院校鋼琴教學選曲》中,這就更體現了《花鼓》在中國鋼琴史上的意義。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年底,瞿維、寄明夫婦倆隨魯藝的大隊人馬徒步前往東北。由于東北交通線受阻,寄明便一人留在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音樂系任教,并擔任收集民間音樂和演奏工作。1946年7月,寄明北上到達哈爾濱與瞿維匯合,在那里參加了《黃河大合唱》、歌劇《白毛女》的演出。同年9月,到達佳木斯,在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任教。12月,寄明參加工作隊,到牡丹江寧安地區開展土地改革以及肅清國民黨土匪的斗爭。1947年5月,寄明先后擔任魯藝牡丹江文工團的負責人。1948年4月任東北音樂工作團的研究員兼少年班主任。1948年11月,還先后任東北藝術學院音樂系教師、主任。1952年起,寄明擔任東北音樂專科學校副校長兼教務主任。在東北期間,寄明對“二人轉”音樂發生了興趣,利用業余時間開始整理和研究二人轉音樂,走訪民間藝人郭文寶、闞昌五、郭希德、陸憲文等。歷經三年,出版了中國第一本“二人轉”的書《東北蹦蹦音樂》。
接著,寄明逐步把工作重點從鋼琴演奏及教學工作轉向創作領域。她深入斗爭生活,向民眾學習,向民間音樂學習,寫了《翻身秧歌》《莊稼人小唱》《干活好》《歌唱劉胡蘭》等歌曲以及秧歌劇音樂,受到人民大眾的歡迎。
1953年8月,寄明上調到北京中央電影局音樂處工作。自此,她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電影作曲創作。
留學莫斯科,奏響交響詩
為造就新中國的國際音樂優秀人才,1955年9月,瞿維作為國家特別選修生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作曲、復調和配器。
莫斯科音樂學院是世界最優秀的音樂學院之一,有最為嚴格、全面的音樂教學體系。
瞿維說,能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是自己的幸運。上世紀50年代,俄羅斯的老一輩音樂巨匠在學院執教,各藝系都有頂級的大師領銜授課。學生們經常可以在樓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維奇,在走廊里見到哈恰圖良、奧依斯特拉赫,還可能與柯崗比肩而過。
瞿維師從巴巴扎年。在這聞名的學府里他刻苦學習各種音樂理論和作曲技法,同時不忘創作。他留學進修期間寫成的主要作品有管弦樂組曲《秧歌場景》《G大調弦樂四重奏》和鋼琴獨奏曲《序曲》等,從中可以看到他對以往積累的生活素材和民間音樂材料的純熟處理,以及在磨練專業創作技巧方面所作的努力。
1959年,進修四年的瞿維學成回國,以后他一直在上海交響樂團擔任專職作曲。此刻他的專業藝術已越發成熟,而要報效祖國的心愿也越發強烈。
交響詩(symphonic poem)是一種單樂章的標題交響音樂,脫胎于19世紀的音樂會序曲,強調詩意和哲理的表現。交響詩的形式不拘一格,常根據奏鳴曲式的原則自由發揮,按照文學、繪畫、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等構思作成大型管弦樂曲。它是標題音樂的主要體裁之一。瞿維敬畏中國人民追求光明的奮斗歷史,滿懷對先烈們的緬懷、歌頌之情,要表現他們,“交響詩”可謂是最好的樣式。于是,他用了數年時間,以深沉、熱情的音樂筆觸,在1963年創作完成了又一部新作品,那就是膾炙人口的交響詩《人民英雄紀念碑》。在“上海之春”的匯演上首次公演,就獲得巨大的成功。評論家稱作是繼歌劇《白毛女》后,作者廣泛地反映中國人民的斗爭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又一代表作。
全曲用奏鳴曲式寫成。緩慢的引子先由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齊奏深沉嚴肅的低音曲調,表現人們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時的悼念和沉思;然后小提琴和中提琴奏出清澈明朗的和弦進行,表現對人民英雄的敬仰心情。主部是一首英勇果斷的戰斗進行曲,運用了模仿復調的手法。各聲部此起彼落,表現英雄們為革命事業勇往直前的斗爭形象。副部是一個民歌風格的主題,表現英雄們寬廣的胸懷和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副部通過變奏發展表現熱情激動的形象,隨后情緒逐漸平靜下來,音樂進入了展開部。在展開部中,主部的斗爭形象得到了積極的發展,變得氣勢奔騰,銳不可當。
瞿維在發展主部時用了“賦格段”的手法。展開部的最后一段用擴大了的節奏發展主題,在定音鼓和低音弦樂器的伴奏下,四個吹著阻塞音的圓號互相模仿,一步步走向高潮,描寫革命斗爭的風起云涌,再接再厲。再現部就在高潮上開始,其中主部和副部互相滲透,都有了新的發展。當主部進入最高潮時,小號和長號用激昂慷慨的音調,吹出副部的旋律,伴隨著一聲鑼鳴,描寫人民英雄的壯烈犧牲;然后音樂轉入慢板,木管樂器和弦樂器奏出引子的主題,和圓號互相對答,表現出無限悲痛的心情。這是再現部中一個富于戲劇性的轉折。再現部中副部的音樂形象,由回憶變為景仰,中間加進了主部的音型,表現出踏著烈士血跡繼續前進的思想。尾聲是主部主題的變形,變成了大調的莊嚴快板,表現廣場上人民群眾對英雄們的歌頌。
史詩性的交響詩《人民英雄紀念碑》得到海外音樂界的重視,后來由華裔指揮家林克昌指揮名古屋交響樂團在香港灌制成唱片,在全世界發行。
瞿維是個勤奮的音樂家,其間創作不斷:1959年為電影《革命家庭》音樂作曲;1962年完成了交響幻想曲《白毛女》;1963年應鋼琴家顧圣嬰的約請,創作了鋼琴曲《洪湖赤衛隊》幻想曲,次年又改編成管弦樂曲;1964年創作了組曲《光輝的節日》;1965年,他深入大慶生活,鐵人王進喜等先進工人的事跡深深感動著他,不僅創作了大合唱《油田頌》,還寫出了歌曲《工人階級硬骨頭》,在全國廣為流傳,影響至今。
粉碎“四人幫”后,瞿維煥發了新的藝術青春,新作品不斷:室內樂《仙鶴舞》、交響詩《紅娘子》(與王久芳合作)、鋼琴與樂隊《音詩》等。1988年,他還應邀為海南建省創作了管弦樂《五指山隨想曲》。
插曲傳四海,歌自采風來
再說寄明,1955年從北京調入了上海電影制片廠,先后擔任音樂創作室副主任、作曲組組長。自此她開始為一部部電影作曲配樂。《李時珍》《平凡的事業》《鳳凰之歌》《魯班的故事》《金沙江畔》《燕歸來》等影片留下了她創作的美妙音樂,同時,她寫就的一首首電影插曲傳遍大街小巷。老年觀眾記憶猶新,由張瑞芳主演的電影《鳳凰之歌》插曲《山中的鳳凰為何不飛翔》;由達式常、高英主演的電影《燕歸來》插曲《燕歸來》《歡迎你遠方的客人》等被廣為傳唱,其作者都是寄明。
除了鋼琴,寄明還能演奏多種樂器。由于自己是四個孩子的媽媽,她還十分關注兒童歌曲的創作。我還記得,寄明曾從一位教師那里聽到說,現在好聽的歌太少,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們對祖國的熱愛,能幫助他們樹立崇高的理想,那該有多好啊。講者無意,聽者有心。巧事還真有,1981年的春天,正忙于為電影作曲的寄明收到了郵遞員送來的信,拆開一看,原來是一位作者寄來的一首歌詞,順著題目《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她朗讀起來:“我們歡樂的笑臉,比那春天的花朵還要鮮艷;我們清脆的歌聲,比那百靈鳥還要婉囀……”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譜曲的歌詞嗎?她讀了一遍又一遍,終于,一個動人的旋律隨口飛了出來,她馬上記錄下來。《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隨著全國各省市的電臺傳播,飛向全國各地,成為千百萬少年兒童愛唱的歌曲。不久,在文化部、團中央向全國征歌中,這首歌被評為一等獎的優秀歌曲。
《好阿姨》《我愛我們的班級》《新中國少年進行曲》《浪花親著我的小腳丫》等,是寄明先后為兒童創作的歌曲,受到孩子們的喜愛。而其中最令人稱頌的,無疑是寄明為電影《英雄小八路》譜寫的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那是1958年,廈門和金門之間發生了臺灣“8·23”炮戰,它讓全國人民知道了廈門何厝小學13名小學生穿行炮戰中支前的故事。一年后,廈門第三中學語文老師王添成,根據他們的故事,創作了話劇《英雄小八路》。第二年的5月20日,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陳耘帶了該校創作系、表演系畢業班100多人來到廈門三中采訪,王添成正好負責對接。王添成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把自己的劇本交給了陳耘老師,沒想到對方看后,非常欣賞。幾天后的六一兒童節,上海戲劇學院排演的話劇《英雄小八路》就在福州公演了,演出迅速引起了轟動并引發了連鎖反應。原來,“英雄小八路”的故事引起了上海影劇作家周郁輝的關注,他把話劇改編成了同名電影劇本。上海天馬電影制片廠認為這是熱門題材,馬上決定拍攝,而把譜寫這部影片主題歌的任務交給了寄明。
在復興西路的寓所里,寄明翻看著還帶著油墨香的劇本。對兒童歌曲創作多一份母親情懷的寄明,那天他向丈夫瞿維商討該如何寫?為讓主題歌能真正反映影片所依據的事實和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變化,瞿維建議寄明到實地采風,豐富素材。一向對深入生活十分重視的寄明,馬上采納了瞿維的意見,從上海專門來到廈門。她尋找到那些已經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們,聽他們講述當時冒著炮火上陣地,給解放軍送飯、送開水的英勇故事。寄明不時被孩子們那種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激動。新中國少年兒童身上那種為實現革命先輩理想,愿意無私奉獻自己一切的純潔而崇高的心靈,真的把她打動了,她時刻在尋找最能體現影片主題的旋律。
采風快結束了,一個熱情奔放節奏和起伏度較大的曲調在寄明耳邊縈繞,她連忙揮筆直書,《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初稿一氣呵成。寄明高興地帶著它回到家中,馬上哼唱給孩子們聽。孩子們一邊學唱,一邊連說好聽。寄明并不滿足,反復修改后,最終才定了稿。
1961年,電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以其鮮明、朝氣蓬勃的音樂形象,受到少年兒童的喜愛。這個為新中國少年兒童抒發內心誓言和遠大抱負的歌聲很快離開電影不脛而走,傳唱在大街小巷,飛揚在祖國大地。1978年,此歌榮獲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同年,共青團中央在征求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后,將《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正式確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快四十年了,戴著紅領巾的中國少年兒童唱著這首不朽的作品——隊歌,為理想而發憤圖強,走向美好的未來。
才女患重病,抗爭見真情
誰也不會想到,一個才女,一個享譽樂壇的作曲大家,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期,竟會患上老年癡呆癥。這天,寄明上街,走到淮海中路時忽地迷失了方向,終于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發現,送她回到家中。經檢查,被診斷為早期老年癡呆。瞿維心中的難過是可以想象的。他四處奔走,百般求醫。可是病情不見好轉,卻日益嚴重。寄明漸漸地變得什么都不明白了。只見她哭了一陣又笑一陣,而瞿維卻在一旁不住地對她說話,可憐的寄明癡癡地望著與她相伴一生的丈夫,什么也沒聽懂。后來不能走路了,瞿維扶著她每天早晚外出散步。漸漸這也不行了,瞿維就輕輕地摟著寄明在家里散步,仿佛在走慢步舞。瞿維嘴里不停地哼著伴唱:寄-明-同-志-叮-格-咚,寄-明-同-志-叮-格-咚……此時的寄明臉上顯出安詳的微笑。可后來,她連聽覺、語言能力也完全喪失了。到1991年,她就像嬰兒一樣,完全要別人護理了。
瞿維和寄明開始共同向命運作抗爭,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頁。每天一早,瞿維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邊,捧著她的臉拍拍她的雙頰,親親她。他輕輕抱起她,放在一張為她特制的椅子上,為她洗臉,用柔軟的小毛巾為她擦洗口腔,由阿姨捧住寄明的頭使她稍稍后仰,瞿維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時喂蒸雞蛋。中午和晚上,瞿維親自把魚和肉、蔬菜、水果咬碎,分別裝進小小的杯里,放進冰箱,餐前拿出蒸熱,再給妻子喂食。丈夫就是用這樣的辦法維持著親愛的妻子的生命。后來有了榨汁機,不必再這樣辛苦了,但瞿維仍然盡力親身去做這一切。年復一年,失去自理能力的寄明只能生活在床上。為了防止寄明長期臥床生褥瘡,瞿維特意設計了一種特別的床,在棉墊下加了一層氣墊,又在下面放了一條電熱毯,既有彈性,又保暖。有朋友去看望他們時,瞿維常摸著寄明的身體說:“她的面部肌肉還有感覺,吞咽、消化功能完好。人生在世,總會遇到各種挫折,我不怨天,不尤人,能為寄明服務,延長她的生命,我的心理也就得到平衡。”
對于“老年癡呆癥”,有人稱它為是通往深邃無光的隧道盡頭,人們會對此感到疲憊和沮喪,因為你無法掌握情況,且感到完全無助。可瞿維沒有感到妻子痊愈無望,更不要說另抱琵琶。相反,只要寄明還有一口氣,或偶然出現一點小動作,他就快樂得像孩子那么開心。寄明是不幸的,得了這樣的不治之癥;寄明又是幸福的,她有一位始終愛她,和她相伴終生的丈夫。
對此“真正漫長的告別”(南希語),瞿維依然不離不棄,照顧寄明整整10年。1997年1月13日,寄明在上海逝世,享年80歲。
瞿維和家人為她送行,追悼會挽聯的上聯是寄明到延安時留下來的——“寄希望于明天”,下聯是瞿維為他親愛的妻子作的一生概況——“寓理想于現實”。
無日不動筆,圓滿音樂夢
對青年一代的音樂教育,是瞿維晚年一直關心的問題。他不顧年事已高和社會工作繁重,在1981年8月上海交通大學成立音樂研究室時欣然應邀擔任教授和主任,滿懷激情地為交通大學的音樂教育,為國家培養復合型人才獻計獻策,發揮余熱。
這個消息讓高等教育工作者們欣喜如狂,他們沒有想到一個享譽海內外的音樂家會走進校園與他們共同奮斗。于是,1984年,全國理工大學音樂教育經驗交流會召開之際,瞿維被應邀參加。這次會議決定成立全國高等學校音樂教育學會,大家一致推舉瞿維擔任籌備小組的組長。1986年全國高等學校音樂教育學會成立,毫無懸念,他被推舉為理事長。1988年國家教委創辦《中國音樂教育雜志》他又被任命為主編(后為顧問)。瞿維不是空頭的主編和顧問,他為高等學校的音樂教育和社會普及性的音樂教育,撰寫和組織了不少文章。他關心群眾的音樂生活,不斷出席群眾性的歌詠活動和文藝演出,毫無保留地給群眾團體的音樂演出作指導,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全國各大學音樂欣賞課教學示范課和研討會、全國各大學合唱團匯演和工作經驗交流會;天津大學舉辦的全國高等學校銅管樂隊的匯演和工作交流會;青島海洋大學舉行高等學校音樂教育的研討會和教學經驗的交流會、青島市高校音樂教師聯合演出的抗洪救災音樂會;為全國500萬大學生普及交響樂,開好“交響樂欣賞課”而由北京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上海交大和上海音樂學院聯合舉辦的教師培訓班,等等,都能看到瞿維的身影,他的書面意見細致、詳盡。他的現場指導生動、具體。老師們、學生們傾聽著大師的教導,興奮激動,自覺地化為了行動。
我曾問過瞿維先生,你早就離休了,八十多高齡的你該歇歇了。可瞿維先生卻笑笑答道:“貝多芬說過,我的箴言始終是:無日不動筆;如果我有時讓藝術之神瞌睡,也只為要使它醒后更興奮。樂圣的話說得好!真的,我也說不上為什么,好像一天沒有音樂,我就活不了。”
沒想到,一語成讖。2002年,為音樂出版社的成書出版,瞿維要將《白毛女》歌劇的音樂部分進行新的管弦樂配器。為避免干擾,他來到他的老家常州,尋找了個清靜的地方開始工作。5月20日,他上午還扒在總譜上工作,當天卻發生了大面積腦溢血。經醫生搶救無效,不幸于19時40分在常州逝世,終年85歲。
瞿維生前對自己的子女留下過遺愿,要把音樂遺產捐贈給他長期工作和奮斗過的上海交響樂團。瞿維子女尊重父親的遺愿,已前后三次捐贈了父親瞿維的創作手稿、樂譜、書籍和唱片等多年來他珍藏的音樂資料。
瞿維的好友、作曲家和音樂活動家孟波先生生前總結我國的音樂創作時說:“西歐的交響音樂傳入中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它對我國現代音樂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和有益的影響,但即使是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作曲家的作品,也是由于作曲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彼時彼地的人民思想感情,并與音樂形象的表現相似、表現手法(旋律、節奏、調式、和聲、配器及其它方面)的民族特點相結合的結果。”
瞿維和寄明實踐了以中國民族風格反映民族精神的思想,創作出人民大眾歡迎的作品。這是我們時代所孕育出的優秀的藝術成果。穿越百年歲月,歌劇《白毛女》《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它們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代人的共同回憶,更難忘的是他們在神州大地上譜寫中華華美樂章時的澎湃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