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感與不斷突圍的寫作
鄭潤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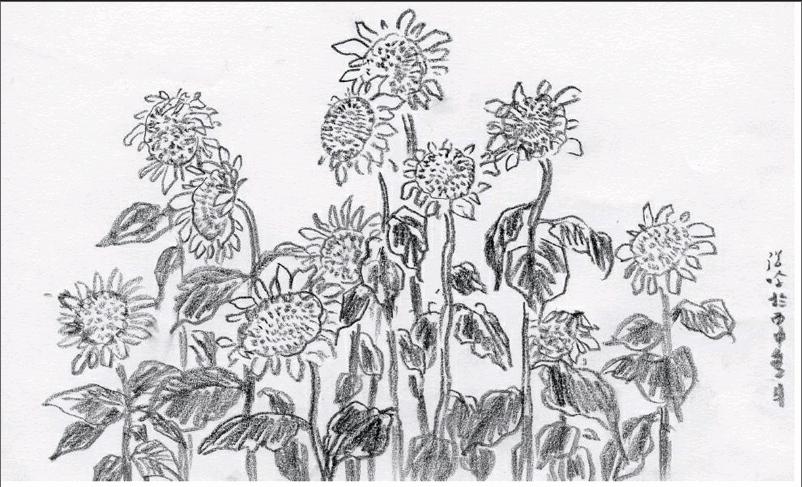
70后軍旅作家西元應該說是近年軍旅文壇闖出的一匹“黑馬”。至少在2012年之前,我沒有特別注意到新生代軍旅作家或者70后作家的隊伍里有這樣一個特別令人注意的身影。但是2013年之后,西元連續在《當代》《解放軍文藝》等刊物刊發作品,并接連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選刊轉載,中篇小說集《界碑》被列入“當代中國最具實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選”叢書,并獲得2014-2015年度《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等榮譽。作為一個70后作家,西元出道應該說比較晚,但他近期小說創作所體現的旺盛的創造力、題材的多元令人驚奇。在我看來,西元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引起文壇的普遍關注,關鍵在于他創作中鮮明的歷史感及其在寫作中對自身寫作范式的不斷突圍的創新意識。
與50后、6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的歷史感相對薄弱。這一點基本上已經成為評論界的共識。50后、60后作家由于其人生的重要階段剛好與20世紀中國的一些特殊的、重要的歷史階段相遇加之長期的創作經驗積累,使得他們的小說創作在歷史感方面有其獨特優勢。70后作家出生在承平時代,也是一個混沌無名的歷史時期,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尤其是新時期之前的歷史,更多只能通過閱讀、想象等間接經驗獲得,因此在歷史感的生成方面確實有一定的難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70后作家就無法形成自己的歷史感。正如史鐵生所言,“歷史感不是歷史本身。歷史是過去的事,歷史感是過去與現在與未來的連接。”歷史感是作家對自己處身的時代與歷史、與未來的關聯的認識,說到底是史識的問題。只要作家有這方面的意識,直接經驗的不足仍然是可以彌補的。西元是70后作家中歷史感方面有著相當強烈的自覺追求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僅要表述個體的感受與悲歡或者比較抽象的人生感悟,而且試圖描述他處身的軍隊、他所站立的時代、社會正處在什么樣的歷史方位,歷史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而未來我們又將可能走向何方,這樣一些既宏觀又與我們每個人其實息息相關的問題。
當然,要在作品中處理這些關鍵性的問題,肯定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從西元近年的創作情況來看,他也是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一步步摸索,一步步拓展自己的小說疆域,逐漸達到對時代與歷史的核心命題的深度理解的。
2013年發表的《遭遇一九五〇年的無名連》應該算是西元較早將歷史的維度引入現實的一部作品。小說的場景發生在西部的戈壁灘上。指導員王大心帶領幾個“弱兵”去完成一個比較艱巨的任務,去離營區三百公里外的荒廢小站上搬五車皮水泥。這幾個弱兵包括白白胖胖、軍事素質幾乎為零的朱毛威武,吊兒郎當、憤世嫉俗、準備退伍的羅三闖,娘娘腔外號“郭美美”的郭抗美,加上通信員張五四。正如很多評論者所指出的,西元筆下的軍人形象很少是“高大上”的英雄形象,而往往是有著種種缺點與世俗煩惱的普通人形象。按照一般的敘述套路,王大心帶領這一班人經過艱苦任務的淬煉使得他們身心經歷一次洗禮獲得成長,小說的敘述目的也就達到了。在這一點上,西元與一般的軍旅作家在處理手法上并無本質的不同,不同的是,作者經由王大心曾經參加過朝鮮戰爭的爺爺引入了1950年的無名連的故事,從而將歷史的維度引入現實。應該說,在這篇作品中,作者試圖用朝鮮戰場上一個無名連的集體犧牲的英雄主義光芒來折射和觸動當下的庸常現實,多少顯得有些生硬,這一敘述意圖并沒有很好地與作品中人物心理的發展、情節設置融合在一起,但這篇小說在西元的作品中仍然具有格外的意義。首先,主人公王大心這一形象在西元后來的軍旅題材作品中反復出現,形成一種“互文”。在這些作品中,王大心的形象大致是類似的,一個剛從軍校畢業的年輕人,有著軍人的血統,類似于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的主人公,帶著一種審視的目光看待自己的軍營生活,對現實中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充滿憂慮,但并沒有磨滅自己內心的理想主義情懷與歷史憂患意識。其次,這篇作品預示西元的小說文本非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相互映照與內在關聯,歷史的維度成為作者思考現實的重要考量。
之后發表的《界碑》在情節與人物設置上與《遭遇一九五〇年的無名連》有幾分相似,同樣是年輕基層軍官王大心和幾個人臨時組成一個組織參加一個遠離營區的艱巨任務,這次他們是去建一個檢查導彈毀傷效果的效應物工程。題目中的界碑指的是當年漢武帝的軍隊打敗匈奴人的地方,在王大心從小生活以及后來工作的基地附近。小說中歷史感的營造還包括特意提到基地辦公樓墻壁上第一任基地司令員、開國中將留下的“死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等標語。與《遭遇一九五〇年的無名連》相比,《界碑》中歷史維度的引入在敘述手法上要成熟得多,關鍵在于“界碑”一語雙關,既指歷史遺留下來的界碑,更指新時期軍人心中的界碑。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魏大騾子、白潔、鋼釘都經歷了內心中的各種彷徨、動搖,但最終都堅守住了心中的界碑。魏大騾子作為工程的直接負責人,只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接受承包商的暗示,就可以得到他此前無法想象的巨額財富;白潔面臨是否犧牲貞潔換取自己夢寐以求的演唱事業的成功這一艱難的選擇;鋼釘作為一個技術嫻熟的老兵,在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即將退伍時,他需要決定是否一如既往地為部隊奉獻自己的才華與熱血。作者毫不避諱書寫他們在誘惑與選擇面前內心的糾結與各種私心雜念。這絲毫沒有降低我們對他們的敬意,反而使得這些人物的形象更加真實可感。在這篇小說中,歷史的維度在無形中成為人物現實選擇時內心的一個重要砝碼。
但西元顯然不滿足于此,《z日》將歷史與未來串聯起來,表達了一種濃厚的歷史憂患意識。在此前作品中主要作為敘述者的王大心在這篇作品中一人分飾多角,成為真正的主角。小說第一句,“2041年深秋的某天清晨,我醒得很早,一身冷汗,身體里卻很燥熱,心很慌張。”一下子把讀者帶到未來。這篇有著科幻色彩的作品似乎一下子打通了西元的任督二脈,使得他作品的氣象與格局驟然打開。小說中的主人公王大心在北方深山的某個軍事基地工作,是基地作戰指揮中心的負責人,也就是最后執行核武器攻擊命令的人。小說分別敘述了處在不同歷史時段的軍人王大心與日本女間諜英子之間的交往與情感糾葛。這些歷史時段包括甲午海戰、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勝利以及作品主要敘述的2041年。在跳躍性的歷史穿越中,不同身份的軍人王大心同樣保有一顆愛國心與憂患意識,但卻在未知的情況下與日本女間諜之間相互產生了情愫的萌動。當然,小說的結尾告訴我們,所有的歷史穿越以及主人公與日本女間諜之間的情感交往只不過是王大心酒醉入睡后的夢中片段。但在虛虛實實中,作者意在抒發作為一名中國軍人對一水相隔的那個民族的復雜難言的情感與歷史憂患感。之后不久發表的《死亡重奏》也是一篇大氣磅礴、形式新穎的作品。通過這篇作品,作者回到了“1950年的無名連”,回到歷史現場,以殘酷的戰壕真實寫出了歷史中中國軍人面對強敵時的抵死反抗,寫出“你把苦難強加于我,我把苦難變成武器”,寫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那些沉默而堅實的脊梁。小說以朝鮮戰場上一個連據守無名高地與美軍殊死對抗為圓心,輻射出連長魏大騾子、指導員王大心、戰士二斗伢子、上官富貴、王盡美等人的苦難人生。這些人恰恰在最有可能擁抱幸福曙光的時刻義無反顧地走向死亡的深淵。作者對戰爭殘酷場景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戰場環境的惡劣甚至使得年輕的血肉之軀寧愿選擇快意的死亡。一曲《死亡重奏》足以引發我們對戰爭與和平、歷史與今天更深沉的思考。在中篇小說《枯葉的海》中,西元以近十幾年來軍隊政治生態的變化為聚焦點,試圖把軍隊放在一個較大歷史尺度下進行考量,通過人物心理的細膩刻畫書寫時代變化,是繼陶純《一座營盤》之后抨擊部隊舊習氣、迎接新的政治生態的又一部軍旅現實主義力作。
但軍旅題材似乎還不能完全滿足西元對時代的思考,在新近發表的《色·魔》中,西元通過主人公黃某某——一個新時代的“成功人士”的“文革”前后經歷與荒唐行徑,思考、對比兩個時代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這篇作品中的黃某某事實上與他最新作品《瘋園》中精神病院的老人是同一種人。只不過前者麻醉自己,后者精神崩潰而已。兩個人的遭遇都是時代癥候的體現。雖然這些作品還不同程度存在理念大于感性的問題,但作品中開闊的時代視野、明晰的歷史感都預示著西元的創作將會越來越令人期待。正如西元所言:“軍旅文學從精神上和技術上需要雙重突破,不要總是怨天尤人,做自己該做的,別人不理解,你就拈花一笑,也不失為一種境界。更重要的是,此時要堅持走下去,和地方上的70后、80后相比,要本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思路,不要把軍旅文學一些根本的東西丟個精光,五年十年后再看,想必總會走出一片天地。”相信堅持不斷突圍的西元會為軍旅文學和當代文壇不斷貢獻更美的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