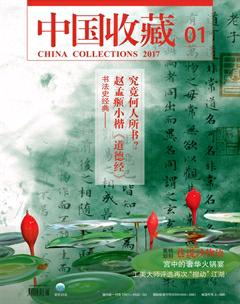我與『雜志大王』的交往
謝其章



前不久收到中國書店海王村拍賣公司的圖錄,我已經許多年不在拍場上買東西,可還是經常收到贈送的圖錄,心里頭是感謝人家的。不買東西,所以圖錄到手只是大略翻翻,這一翻不禁一驚,第一頁一行黑體大字“琉璃廠的‘雜志大王”!上面一張“劉廣振先生工作照”,我看了之后,往事如煙似夢—劉廣振先生,我終于親眼見到您啦。本場拍賣1-81號拍品為劉廣振舊藏,所以特于卷首推舉。
我的第一本書《漫話老雜志》,第一篇就是《北京琉璃廠的“雜志大王”》,內中寫道“幾年來,我通過‘雜志大王之手買過不少民國老雜志,卻從未見過老先生一面,心中總覺得欠了人情。有一天,我終于找了個借口進到了戒備森嚴的中國書店總店書庫,到了二樓,人家攔著不讓再往里走了,我解釋說就是為了看一眼劉廣振老先生,那位工作人員指著一間堆滿書刊的屋子里的一位埋頭書案的老者說:‘那就是劉廣振,老者年逾古稀,滿頭銀發,伏案理書。我隔著玻璃窗望著老先生的側影,沒有打招呼,我只不過是無數買書人中的一個罷了,心中滿懷謝忱。”寫書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劉廣振先生去世了,所以接著寫道,“幾代‘雜志大王的故事結尾了,每當夜深人靜,拿出心愛的老雜志翻閱,隨意地讀上幾段,想到它們是如何得來的,眼前總會浮現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老人的情景。”
必也正名乎。說來“大王”的稱呼并不恰當,總給人以嘯聚山林的匪盜氣味,卻能使人留下強烈印象,也只好由著口口相傳吧。曾見到一份1961年北京市手工業管理局關于《琉璃廠文化街調整恢復方案(草案)》的文件,其中第一部分第三條這樣寫的:“恢復松筠閣(經營雜志)的銷售業務(過去專營收購),并將后邊庫房改為內柜(以上已辦);擴充內柜,把舊雜志都陳列出來,發揮其‘雜志專家的特點(需增撥用房)。”正式文件的稱謂“雜志專家”,實質即“雜志大王”,可見約定俗成的力量。我跟藏書家姜德明先生講到這份文件,他說恢復琉璃廠老字號的經營特色,是鄧拓的建議。如今我們看到,松筠閣匾額的題寫者正是鄧拓。
“雜志大王”聲名鵲起,并非始自今天,那要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松筠閣開設于光緒年間(最早的題匾額者失考),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內記“松筠閣,劉際唐,字盛虞,衡水縣人,于光緒二十幾年開設,在地藏庵內。民國元年,遷徙琉璃廠路南槐蔭山房,經營數年,民國六年,又遷移南新華街路東。民國十五年在廊房頭條第一樓內開設集文閣分號數年,二十六年又遷徙迤南路西。近盛虞子殿文繼其業。”于此可知,松筠閣那時的店址并不在如今琉璃廠東街路南的位置。劉殿文繼承父業(劉際唐1942年病逝),卻正趕上北平淪陷生意慘淡,無奈之下,只得另辟蹊徑,專門經營起古舊期刊雜志來,居然做得有聲有色“獨此一家,別無分號”,書肆同行便送給劉殿文一個“雜志大王”雅號。公私合營之后,松筠閣并入中國書店,劉殿文任期刊門市部主任,劉殿文編撰有中國第一本雜志目錄《中國雜志知見目錄》,每周一次,在店內講授雜志的目錄學。松筠閣也繼續以經營期刊雜志為主業。1963年10月27日的《北京晚報》曾有報道松筠閣的專題文章《萬種雜志任君選配》。余生也晚,上世紀60年代初還是個小學生,距離松筠閣最近的地方,只到過春節的廠甸。未能親睹松筠閣環壁皆期刊雜志的鼎盛景象,連一張照片也未見過,一直都是我的遺憾。
至于劉殿文的年紀,60年代初,藏書家唐弢《書林即事》里寫過“松筠閣專營期刊,曾有‘雜志大王之稱的劉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現在是中國書店期刊門市部主任。”70多歲,仍然在工作崗位。其時,已后繼有人,唐弢接著寫道:“后起的有王中和、劉廣振等,王中和新舊版本,都有素養;劉廣振是劉殿文老人的兒子,記憶力強,對期刊知道的較多。”我知道劉廣振的時候,老先生也該“年逾七十”了吧。
我在《海王邨書肆之憶》里寫道“我的舊書刊初旅,即在東廊展開,這是永記終生的。我后來能夠寫作出版十幾本書,還是要拜東廊所賜。感謝種金明先生耐心地一次次給我集配舊雜志,使我走上了與大多數愛書人不一樣的藏書路徑。”海王邨的北面主樓是中國書店總店,西廊是中國書店下轄的邃雅齋書店,東廊也隸屬中國書店,但是“很僻也很暗,終日射不進多少陽光,昏昏暗暗,與四壁的古舊書顏色倒是水天一色,終年在這里的店員,好像現代人發配到了荒寺野廟。”這是我保留至今的印象。30年前一個悠閑的下午,我走進了東廊,毫無目的在書架上翻書,有位上了歲數的店員用疑惑的眼光瞄著我。
東廊書架陳列的古書,我是不翻的,幾排舊書也沒有入眼的貨色,多是些不古不今的書,直到我看到柜臺里一小捆民國出版的《萬象》雜志那一刻,才決定了要走的路。店員告訴我《萬象》訂出去了,買家還沒來取貨。從那兒以后,我去一次就看一眼《萬象》,三番五次之后,種師傅說:“賣給小謝吧,這么長時間某某也不來取,大概是不要了。”任何商品交易,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際,舊書買賣更是離不開交際能力,而這恰恰是我的弱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種師傅是管事的(好像是科級),我想找什么雜志,門市沒有的,種師傅就拿著我開的書單去大庫里找配,而大庫那邊為我配雜志的正是第二代“雜志大王”劉廣振,所謂交往,就是這么點兒關系。有年夏天,我想給劉廣振送個西瓜表示一點兒謝意,到底還是沒送,冷不丁拎個西瓜去,自忖冒失。
姜德明曾說:“大約十多年前,中國書店的朋友曾經向我打聽,有位姓謝的常買舊雜志,開的書單胃口不小。”最近跟姜先生聊起舊書業的衰落,他說幸虧你動手早,買了不少舊雜志,還說據他所知除了唐弢開過集配雜志的單子外,我是第二個。姜先生的這番話,讓我小小得意了一番。干脆曬幾張留有劉廣振手跡的單子,原件不知放哪個文件夾了,隨便抄上幾筆吧。
大風 4冊 48元
天地人 4冊 60元
天地 3冊 18元
子曰 3冊 36元
家 4冊 32元
談風 3冊 30元
紫羅蘭 4冊 48元
半月 4冊 48元
幸福 4冊 48元
少女 2冊 20元
家庭 4冊 60元
合計11部 39冊 448元
需要說明一點,有些雜志不是我開的單子里的。448元好像打了九折。
另一張書單
六藝(1:1-4) 4冊 80元
萬象(1:1,3,4) 3冊 30元
萬象十日刊(2,4,5,6,7) 5冊 50元
萬象周刊 1冊 12元
萬象十日畫刊(3,4,6) 3冊 30元
萬象(1,3) 2冊 30元
萬象 1冊 12元
大偵探 9冊 100元
茶話 28冊 550元
大眾 精裝8冊 700元
雜志 24冊 500元
共計11部 88冊 2094元
我記得這張單子是這么回事,我不是喜歡《萬象》么,所以請種師傅將凡是“萬象”名字的雜志每樣來幾本,居然找來這么多,也可見我當時漫無邊際的搜刊方法。《茶話》(35期全)和《雜志》(37期全),后來我自己通過別的途徑居然給配全了。
還有一張劉廣振寫的雜志清單,不寫價錢了,把刊名列一下吧:《星期畫報》《京報副刊》《立言畫刊》《見聞》《西風》《民間》《晨報副刊》《永安》《老實話》《人間味》《女聲》《上海生活》《小世界》《宇宙》《藝術生活》《三六九畫報》,總共130余冊。這樣“想要什么有什么”的黃金日子,維持了兩年多的光景,書單十幾筆吧,好日子永遠是短促即逝。
劉廣振手下有個高徒,姓韓,雜志業務精熟,年輕,寫得一手娟秀的鋼筆字。劉廣振之后,韓先生幫了我不少忙,但是“雜志大王”之美譽,到劉廣振為止了。
最后回到本場拍賣劉廣振舊藏雜志來,在我的印象中,中國書店老店員舊藏書刊成批量的公開拍賣,這回似乎是第一回。這里面牽扯到一個敏感問題,我打這么個比方吧,過去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郵電部的高級官員是不準集郵的,通俗點講即“近水樓臺不準先得月”。雷夢水是舊書業大名人,姜德明先生曾經寫道“他(雷夢水)雖賣書,也自備一點心愛的書在手邊。出于潔身自愛,也是為了避嫌。購來的每本書上或貼有單據,或留有購書日期,定價和單據號碼。這種處世之道亦帶有一點儒雅之風。”我跟了一句,終歸經歷過那么多的運動,養成了“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的處世哲學。
這81件雜志,沒有一件是我特別想要的,或能補我之缺,可見雜志世界品種之繁復,類型之多樣,每個人都能憑著興趣各求所愛。這些雜志有5件流標,拍價最高的一件是《國學季刊》抽印本《北平方音析數表》,著者劉復(劉半農)簽贈本,拍了2.53萬元,書只值300元,“劉復”值2.5萬元;同樣的27冊《國學季刊》(1-7卷)只拍了10925元,證明名家手跡的威猛。另一件簽贈本(1947年《五月》雜志“沙鷗兄收存 弟丁力敬贈 卅七,八,廿”)由于“丁力”名頭小,只拍到1035元。受贈者沙鷗(1922年至1994年)是很有名的詩人,我求證止庵先生這是你父親的《五月》嗎,他說是,“文革”中抄家抄走的。抄家抄走的,沒有焚燒掉,卻流失到劉廣振手里,進而堂而皇之地被拍賣,我知道原書主也知道后書主,真是有意思。
劉廣振似乎另有集郵的雅好,81件藏品中竟有14種郵票雜志,專場沒有一件藏品稱得上是頂級之物,同樣,14種郵刊里也未出現《郵乘》這樣的頂級刊物。我也曾經癡迷郵票(后為籌資購買雜志大部分賣掉了),也曾經盡心搜集過郵刊。劉廣振賣舊雜志,我買舊雜志;劉廣振喜好集郵,我亦喜好集郵,這或許要算我與“雜志大王”的共同愛好了,是一種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