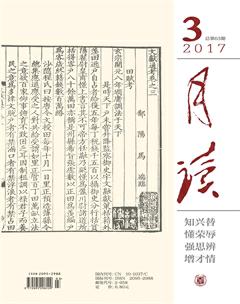對比與反思:為何“明治維新”勝過“洋務運動”?
吳敏文
歷史上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經歷了中強日弱—勢均力敵—中弱日強的演變過程,分別以一場發生或引發于朝鮮的戰爭之勝負為標志。公元663年,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高句麗等三國混戰。唐高宗應新羅王的請求,出兵助其打敗百濟。日本天智天皇命人護送百濟王子回國重建。中日之間展開激烈海戰,日軍大敗,天智天皇向唐朝臣服,并以中國為師謀求自強。公元1592年,剛剛完成日本統一的豐成秀吉,率軍占領從釜山到漢城的大片朝鮮領土。明朝政府出兵援朝,與日軍在朝鮮苦戰七年,直到豐成秀吉病死,日軍撤退,中朝才贏得勝利。公元1894年,朝鮮“東學黨”起義,中日出兵朝鮮并爆發甲午戰爭,清朝完敗,公元1895年,李鴻章赴日簽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之間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此,世界各國的實力對比開始有了全球坐標。事實上,西方對中國的關注度遠超日本。早在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就在他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中,對中國進行了田園詩般的描述和贊美。最先崛起的西方大國葡萄牙和荷蘭,也率先來到了中國。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抵達廣東;1557年,通過賄賂廣東官吏,葡萄牙人獲得了在澳門租地建屋的準許。明朝天啟四年(1624),荷蘭殖民主義者侵占中國臺灣。1656年,荷蘭使團到達北京。入主中原才八年的大清朝廷,以一種興奮的態度接待了他們。荷蘭人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在覲見皇帝時行三拜九叩大禮的要求,順治皇帝高興地賞賜給這個來自世界上最富庶國家的使團大量禮物。一個叫約翰·尼·霍夫的使團成員寫下了他們答應跪拜的原因:“我們只是不想為了所謂的尊嚴,而喪失重大的利益。”公元1661年,在大陸步步敗退的南明王朝,派鄭成功率兵兩萬從金門出發,越過臺灣海峽,在澎湖休整后直取臺灣。公元1662年,被圍困八個月之久的荷蘭侵略軍被迫投降。這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最先碰撞,但中國并沒有對這兩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西方小國產生研究的興趣,當然也就什么也沒有學到。
荷蘭人在侵占臺灣的同時,也基本上壟斷著日本的對外貿易。此時的日本,正處于由德川家康建立的江戶幕府時代。幕府政權僅在長崎港外建了一個大約1.5公頃的人工島(出島),并在島上建了荷蘭商館。由此可見,此時整體上仍然閉關鎖國的日本,對荷蘭人采取的是非常有限的開放政策,但是,日本人通過與出島的荷蘭人的交流,創立發展出了一門專學:蘭學。日本的士族階層紛紛學習和使用荷蘭語,用來研討歐洲近代的天文、地理、醫學等新興學科。日本由此得以奠下早期的科學根基。當時日本人的識字率已達70%~80%,數千部有關蘭學的刊物得以出版,并在日本人之間廣為傳閱。一些商鋪專門向大眾售賣西洋珍奇和工業制品(如時鐘),以及展示這些西洋的新發明(如展示電動制品以及在19世紀初的熱氣球升空)。荷蘭因素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
雖然這時沒有任何依據來直接評判中日之間的實力對比,但在對于西方文明的態度上,兩國還是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日本雖然限制荷蘭人的活動范圍,但表現出了如饑似渴的學習精神;清朝的統治者呢,以向當時世界上最發達和富有的荷蘭人賜予大量禮物的方式,贏得了荷蘭使者三拜九叩的“天朝上國”的面子。了解這一點,對于理解其后西方勢力大舉入侵時,中日的應對之策—“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之間的截然不同,也就有了心理基礎。
在1793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與中國建立國家間關系的外交訪問鎩羽而歸之后,1816年嘉慶朝時,英王再次派遣阿美士德勛爵帶領600多人的使團訪華,來訪目的與馬戛爾尼相同。但因為嘉慶帝在接見英使要求三拜九叩的所謂禮儀問題上比乃父乾隆更不通融,阿美士德及其代表團連嘉慶帝的面都沒有見著,就被驅逐出境了。
面對19世紀的工業文明和科學技術,清王朝自身仍處于落后的農業文明之中而不自知;自己不抓住機會學習,別人送上門來還視而不見,結果就只有被動挨打了。公元1840年,由于貿易糾紛,特別是鴉片貿易給清朝帶來的白銀流失和國民健康損害,清朝決定查禁鴉片,英國人強勁的武力叩門就開始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朝軍隊無役不敗,最后被迫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割香港島給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中國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等等。中美簽署《望廈條約》,中法簽署《黃埔條約》,其本質與《南京條約》無異。與西方諸國簽署了多個條約,客觀上使中國從此進入“條約時代”。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都高度期望清朝能夠切實履行所簽條約,但在道光帝的繼任者咸豐帝及其大臣看來,既然是你強迫我簽署的條約,我就沒有遵守的義務。因為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蠻橫,也因為咸豐帝的無識和莽撞,造成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并劫掠、火燒圓明園。第二次鴉片戰爭慘敗,英法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開天津為商埠,割九龍司地方給英國,準許外國人在中國買賣人口,對英、法兩國各賠款800萬兩白銀。
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動搖了清朝統治的經濟基礎。泱泱中華帝國為何屢屢挨打?有識之士為了救亡圖存,開始向西方學習。在奕?、李鴻章等重臣的倡導下,從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歷時30年的“洋務運動”開始了。但中國洋務派的改革指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自強”。此時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慈禧認為:“外國之陸海軍及機器,我亦稱之,但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如果說慈禧短視狹隘是因為缺少文化,當朝一時無匹、飽讀詩書的能臣干吏李鴻章應該算視野開闊見識上乘吧?李鴻章在他的《籌議海防折》中強調的是:“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當時擔任清朝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著有《局外旁觀論》,署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亦有《新議論略》,系統地提出了改革中國內政外交的建議。兩個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二月遞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后,奉上諭交各地督撫詳慎籌劃,結果是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湖廣總督官文斥之為“包藏禍心”,江西巡撫劉坤一則認為“斷不可從其所請”,兩廣總督瑞麟和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說“自強之道,不待外求”,“毋庸變其法”。要知道,這些人在清代大吏中并不以頑固著稱(頑固派首領倭仁對西學西人的排斥,到了偶遇洋人都要以扇遮面的程度),尚如此排斥,則其他頑固派重臣的態度,可想而知。
洋務派企圖以器物之用,來維護封建之體,在大量購買洋槍洋炮的同時,還向外國購買機器等設備,在全國范圍內興建兵工廠;與此同時,大批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形式的民用廠礦企業也開始興辦。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對落后的社會制度進行改革,企業的管理體制一如封建衙門,人浮于事,腐敗盛行。這與日本放手扶持三菱這樣的民營企業大異其趣。1873年,曾經游歷西方的33歲的澀澤榮一,已經成為主管國家預算的大藏少輔,仕途前程似錦;但他卻做出了一件在當時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遞交辭呈,棄官從商。辭官后的澀澤榮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銀行,并由此開始了自己極具傳奇色彩的企業家生涯。他的企業組織活動逐漸向海運、造船、鐵路、紡織、啤酒、化學肥料、礦山等產業部門全面展開。終其一生,澀澤榮一創辦了500多家日本企業,被稱為“日本的現代企業之父”。
同樣面對西方的武力叩門,日本人的反應與清人大相徑庭。日本人以極其謙恭的態度,認真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1853年7月8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修·佩里將軍率領共有六十三門大炮的四艘軍艦強行駛入日本的江戶灣口,以武力威脅日本幕府政權開放國門。由于日本火炮威力大遜于美艦,加上日本一直師事之的中國早在十多年前就被英國打敗,盡管日本國內對選擇開放還是開戰有過爭論,但最后還是以歡迎的態度接受了佩里的要求。直到今天,在佩里艦隊的登陸地,樹立著一座由當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開國紀念碑”。這或許是日本人的獨到之處:對強手入侵本國非但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認為給自己帶來了文明進步的機會。
但西方列強對日本沒有客氣,美日雙方在橫濱簽訂了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美親善條約》,其他西方國家隨即跟進,紛紛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1863年發生了英艦炮轟日本鹿兒島事件,1864年發生了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占領日本下關地區的戰爭。日本與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簽定了不平等的親善條約,國門被打開。
隨著鎖國政策的結束,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關注起外面的世界。1867年,日本派出代表團參加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新奇的工業產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機械設備,西方的工業化成果讓日本人大為震驚。1868年,日本睦仁天皇受到《周易》“圣人向明而治”的啟發,改年號為明治,4月15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圖強大幕的總綱領。由此,日本以“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發”為口號的“明治維新”開始了。
1871年,一支以日本最高領導階層人物巖倉為首的近百人的政府使節團從橫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使節團中包括49名高官,這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2%。在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里,他們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實錄。此次出訪,在政府投入之大、官員級別之高、出訪時間之長等方面,在日本乃至亞洲國家與西方世界交往史上,都可稱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動。而訪問的效果,可以用“始驚”“次醉”“終狂”三個詞來概括:“始驚”就是他們到了歐美,看到了西方發達的文物制度以后,那種吃驚的程度;“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這種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終狂”就是下決心發瘋似地學習西方一系列的文化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樣。在德國,日本使節團找到了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幾千年來一直以強者為師的日本人,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新的老師。
回國后主導日本工業化進程的,正是巖倉使節團的副團長大久保利通。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產興業”計劃,政府直接從西方拿來了法國式的繅絲場、德國式的礦山冶煉廠、英國式的軍工廠。除了購買機械,政府還聘請了大量國外技師。當時,一個外籍專家的月薪最高可以達到兩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在開辦國營工廠的同時,大久保利通還大力扶持民間企業。三菱是日本最著名的商標之一。今天的日本國內有一百多家三菱企業,海外還有數百家三菱的分支機構。而在1870年,三菱還只是一個擁有三艘小船的默默無名的小公司。但是,它很快獲得了明治政府委托經營的13艘輪船和海上軍事運輸業務;一年后,政府干脆將這13艘輪船送給了三菱,每年還撥給經營補償費;此后,政府又購買了郵政輪船公司的18條輪船,無償交給三菱經營。
在大力推進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同時,日本也沒有放松與現代工業社會相適應的政治改革。1885年,日本實行內閣制,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將日本從一個封建的農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1893年,日本近代化企業數達到3344個,遠超中國。明治維新的碩果之一是國民素質大大提高,1898年,日本學齡兒童就學率達97%,為當時世界最高水平。教育立國成為國策,使日本在諸多跟進西方工業化的國家中顯得出類拔萃,成為學習西方的“優等生”。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之后十年,日本打敗俄國。從學習唐朝到學習荷蘭,再到學習近代工業化的西方,日本完成了由弱到強的華麗轉身。
對中日而言,從1840年到1894年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是難得的改革窗口期,兩個國家兩個民族對于學習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一方如饑似渴,一方淺嘗輒止;一方謙恭惟謹,一方仍以“天朝上國”自居;一方主動應變、奮力趕超,一方被動應付、亦步亦趨。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習態度以中日甲午戰爭為大考,優劣分明。
學習態度的不同是中日強弱異勢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治維新”勝過“洋務運動”的關鍵之處。但當我們將眼光放長看遠,就會發現,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如長江黃河匯百川而歸滄海,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華文化具有包藏宇內的包容性和融匯八方的融合能力,若非如此,中華文化在元和清入主中原之際就絕流了,何以歷經五千年風云激蕩而不滅?在盛唐的都城長安,外國人不僅靡集街市,甚至成為朝廷高官。甲午敗于日本之后,中國也曾出現過學習日本的高潮,孫中山、梁啟超、陳天華、秋瑾、魯迅等民族精英,都有過駐留或留學日本的經歷。中日之間的近鄰關系無法改變,中日之間合作與對抗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慘痛和深刻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日在各領域的競合仍將在一定的軌道上向前延伸,而吸取歷史的教訓,對今天的中日關系,仍具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