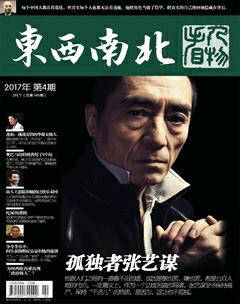挖坑埋線,美國總統權力交接時的黑洞
自民主黨人卡特任總統時起,很多美國總統會在任期最后時刻推出所謂“子夜法例”和行政令,以確保自己的政績不被繼任者輕易推翻。
前任給后任“挖坑”的歷史淵源
在美國歷史上,總統交接過程中,前任給后任“挖坑”的事情并不少見,但是多數都是類似于小布什接任時候,克林頓的幕僚們扣走了白宮電腦上的“W”鍵(小布什的中間名首字母)這種惡作劇性“撒氣”,能采取如此激烈的態度確實不多見。
如果往前追溯,大約也只有“大蕭條”時期擔任總統的克拉克·胡佛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之間發生的故事可以與之相比。當時美國面對長達4年的嚴重危機,國內經濟長期乏力、社會分裂深化,國際格局中軸心國集團日益表現出強烈的擴張勢頭。在美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主張“自由經濟”的胡佛和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新政”才能拯救美國的羅斯福之間在價值觀上有著深刻的分歧。這一次奧巴馬和特朗普之間的分歧,與這段往事頗有類似之處。
兩任總統政策分歧的深層原因
奧巴馬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政治精英階層代表,依靠民主黨的黨派機器從一個“政治新星”順利地入主白宮。他在任職期間嚴守各種“政治正確”,既重視社會福利對于美國社會底層的安撫作用,又傾聽華爾街的意見試圖以對亞太的和對歐的兩個“自由貿易協定”來確保美國經濟霸主地位。在對外關系上奧巴馬仍然遵循傳統路線,依靠盟友對被視為潛在對手的中俄進行遏制,但是在遏制的同時奧巴馬顯然是有著明確的底線,不會干出來挑戰“一個中國”等原則問題。
另外懾于小布什政府一頭扎進中東泥潭的錯誤,奧巴馬在使用武力解決問題上明顯更加慎重。不過奧巴馬的一切努力對于美國目前面臨的社會再次分裂的危機并無明顯的改善,同樣也不可能真的遏制中國崛起的步伐。
特朗普正是利用了奧巴馬在解決國內問題上的無力和應對國際關系問題上的“軟弱”,他競選期間喊出了要顛覆美國的“政治正確”,依靠對于美國現狀極度不滿的“沉默多數”撇開了傳統政治黨派,沖破層層阻隔之后當選了美國總統。但是顛覆以后如何做,特朗普現在也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僅就他目前言論和組閣的努力看來,“保守主義”和“鷹派”的標簽可能不算冤枉。
從特朗普提出的“制造業重振美國經濟”策略出發,他很可能讓中美之間爆發一場貿易戰。而他在對外關系上,既挑戰了“一個中國”的底線又力主以武力為后盾去解決恐怖主義威脅,這兩個選擇都是美國現有的軍費開支水平難以支持的。
特朗普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局外人”,可以不顧既往的規則或者“潛規則”,但是華爾街及其代表美國傳統政治的精英階層不會喜歡如此多的不確定性。他們難以接受4年后面對一個政治上盟友離心離德、經濟在貿易戰后玉石俱焚的爛攤子。
奧巴馬和特朗普代表的美國不同勢力之間的分歧如此深刻,那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必然會有所體現。即如此,前任給后任“挖坑”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聯合國內通過“棄權”警告以色列,安撫阿拉伯國家親美勢力,并且不斷的強調“一個中國”政策不是可以輕易挑戰的,這既可以理解為奧巴馬給特朗普“挖坑”,更可以理解為美國政治精英層在為未來美國的中東政策預留更多的“空間”。
奧巴馬在任期還剩不多之時,做得越多給特朗普挖的“坑”越多越大,也就意味著美國傳統政治精英對特朗普制約的機會越多,給自己預留的空間越大。而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吃瓜群眾紛紛表示,許多年之后,已經離開工作崗位的特朗普也許會回想起這個新舊年之交的日子,手邊放著自己寫的幾本回憶錄,《我的前任奧巴馬是奇葩》《與奧巴馬同行的最后日子》《奧巴馬那些比較坑的事兒》……
(綜合摘編自《人民日報海外版》、瞭望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