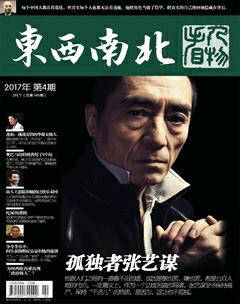保衛豆瓣評分,保衛我們的精神病角落
熊阿姨
這是中國互聯網的一個安定醫院,用戶默默在這里留下讀書、看電影、聽音樂的記錄,在微博微信喧囂的社會性之外,分裂出另一個私人品味的人格。
1
豆瓣用戶,可以說是中國互聯網上最矯情的一個群體了。
自從2005年成立以來,這個網站見識過無數次流行風潮的起起落落。10年前這里發源了“小清新”,法寶是日式膠片風格照片、陳綺貞、獨自旅行、光腳穿帆布鞋。還沒等用戶們減肥成功投身進去,整個網站風向一變,又集體開始了對歲月靜好的集體嘲諷。
最早也是在豆瓣,父母輩的“文學青年”一詞演化出了“文藝青年”這個第二代變種,概念大體相似:喜歡讀書、熱愛生活、關注美好的事物,以及窮。還記得這詞兒剛起來時,豆瓣滿屏幕都自詡文青,覺得彼此都是春風吹過的王彩玲。
結果幾年不到,“文青”這詞兒就迅速貶值,新的浪潮是卯著勁兒地自我挖苦,很長一段時間內,但凡是嘲諷文青的日記就會被頂到首頁,大家每天幸災樂禍地刷新,看又有什么尖酸刻薄的文章正等著罵自己。
外界對豆瓣用戶有很多污名,實際上最早的源流都來自豆瓣自己。從書影音起家的這群用戶跟你生活中的很多年輕人很像:有點悶騷,喜歡自嘲,他們對文娛生活比普通人講究,但又掀不起什么大風浪。
這個成立了12年的網站是國內互聯網界的一個奇葩,“Web2.0”概念早就過時了,豆瓣一直沒找到新的突破點。用戶們在消費升級概念之前,就在這里談論Kindle 3、iPod、黑膠唱片、日本手賬;談論女權、父母皆禍害、在日記里使用表情包。但當消費主義和移動互聯網的大潮席卷而來,坐擁上億用戶的豆瓣卻毫無變現能力。
大批志存高遠的用戶早已陸續離開,在公眾號上發家致富了(有的還要恨恨寫篇絕筆,埋怨自己被耽誤了)。這里超過3萬粉絲就已經是了不得的紅人,而在微博、知乎上,這個數字連個中V都算不上,再跟公眾號篇篇10萬+的大號相比,已然要低到塵埃里。連網絡營銷都很少在這里涉足,去中心化的設計太難制造病毒性傳播。
如今留在這里的人樂得自稱廢柴,2016年春天,豆瓣第一次做了一個宣傳廣告,自稱是“我們的精神角落”,不到一天時間,又被用戶們解構,變成了“我們的精神病角落”——這就是中國互聯網的一個安定醫院,用戶默默在這里留下讀書、看電影、聽音樂的記錄,在微博微信喧囂的社會性之外,分裂出另一個私人品味的人格。
2
然而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書影音里,音樂早早衰落,圖書不溫不火,而電影市場正爆炸式增長。作為國內唯一一個類似IMDb評分網站的平臺,在購票網站、視頻平臺和互聯網電視上,電影介紹里大多會帶上一個豆瓣評分,一旦跟銷售掛上鉤,上億用戶的打分突然變成了一塊香餑餑,精神病人的囁囁私語頓時有了商業價值。
在2015年12月,豆瓣CEO阿北就發了一篇《豆瓣電影評分八問》,當時回應的還是如何處理水軍,核心觀點是:豆瓣評分一人一票,全靠程序計算平均數;新注冊的水軍評分會被程序篩掉;影視業的施壓不會影響豆瓣評分。
然而商業終將會以另一種方式影響到互聯網最后一塊自留地。
2016年12月27、28日,《中國電影報》、人民日報客戶端、CCTV6《中國電影報道》共同提出了豆瓣、貓眼等電影評分網站“惡評傷害電影產業”的說法,稱兩個網站惡意給國產電影打低分,導致觀眾拒絕觀看國產影片。
值得玩味的是,三家發布的內容高度雷同,步調整齊劃一。再往根上追,很容易發現一些更有意思的共性:《中國電影報》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管、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辦的報紙。
CCTV6電影頻道,并不是由央視主管,而是由廣電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直屬機構,“電影衛星頻道節目制作中心”制作、運營和播出的。
人民日報客戶端看起來與廣電總局沒什么關系,結果有一天,人民日報評論部自己發了一篇反對文章:《中國電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并在微信評論里蓋章論定:(人民日報論調)“以此為準”。
——事情至此,一場烏龍的路線就清晰了。
關心電影票房的不光有各家影視公司,還有利益相關的管理者。中國電影的總票房也是一種業績,2015年國內電影總票房達到440億,照前一年增幅達到了48.7%,而2016要結束時,卻只達到了450億的總票房,僅僅2%的增幅創造了近10年的新低,要知道原本的期待可是要達到660億。
2016年12月份的《長城》《擺渡人》《鐵道飛虎》,本來是最后一套救市組合拳,光《長城》一片就帶了30億的預期。沒想到傻了好幾年的中國電影觀眾突然變聰明了,幾部片子齊齊撲街,觀眾們的興趣都在討論景甜的世界第八大未解之謎,在猜測張嘉佳如何一年內喝下400瓶伏特加,為什么成龍新片宣傳只字不敢提房祖名……嬉笑怒罵動靜不小,就是不進電影院。
唯一出氣的辦法,就是找個豆瓣這樣的軟柿子捏一捏。
3
沒想到軟柿子捏爆了。
互聯網輿論的環境也早就變了,官方媒體一篇有失公允的評論文章,按理說也起不來這么大風浪。從《中國電影報》、到人民日報客戶端、到央視,整個鏈條都只是在慣性上出軌了一點點,但被輿論主動捕捉到后,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
很難說大眾義憤填膺的反響,到底是引爆了哪根導火索——政治干預文藝這件事,其實在一輪一輪的干預里大家早就習以為常了;官方媒體為國產票房站臺,看起來也并不出人意料;電影口碑不好罵水軍,這幾年這種事兒還少嗎?
而且豆瓣式微已經太久了,流量不占優勢,熱度也不夠。讓人不無陰暗地想,如果是微信、淘寶這種巨頭社區也有打分功能,恐怕那篇評論也是不敢隨便拿來舉例的。而豆瓣看起來最窩囊,沒錢沒地位,一盤散沙的用戶能有什么反擊之力呢?
然而之所以豆瓣的電影評分這么值錢,就是因為沒有巨頭在電影業的資本影響力,又被算法死死鉗制著,才留下了互聯網最古老的真實評價體系。
票房去哭哭啼啼假裝潘金蓮,我們沒有說話;票房埋怨觀眾不愛惜自己的藝術家,我們沒有說話;票房在圣誕節要渡人渡己,一大群流量明星齊刷刷轉發好像受了多大委屈,我們還是沒有說話。票房最后要拿最后的精神病角落開刀,被惡心了一年的患者們終于不干了:請還給我們不辣眼睛的權利!
指鹿為馬的環境待太久了,還以為正義感早丟了。集體憤怒里,豆瓣用戶的呼聲其實還是很小,但助拳的人卻遠遠比想象中多。
經過了憤怒,豆瓣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用戶們又開始罵阿北的改版,刷2016讀書報告。一場飛越瘋人院的憤怒,煙消云散,精神病人們各歸其位,在工位上摸魚。
(劉持重薦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