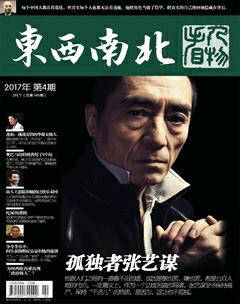吃屎的邏輯
貓亂
如何把大便送進人體并不是治療的關鍵,而如何將產品規范化卻成了噩夢。并且,沒有人知道一個人的腸道菌群會對另一個人的健康產生什么影響。
坐落在馬薩諸塞劍橋鎮的塞雷斯制藥一度是糞便研究界響當當的名字,甚至它的鄰居也個個名聲在外——且不提此地兩所知名常春藤高校,僅同處一幢大樓的就包括引領基因編輯風潮的Crispr Therapeutics。沒錯,塞雷斯確實在用糞便制藥,確切地說,是想辦法利用人體腸道中的億萬個細菌,來治療消化道疾病甚至更多。
這些細菌再加上其他生活在人體內部和表面的所有細菌,共同構成了無形卻龐大的人體菌群,一個近年來才逐漸進入科學家視線的嶄新世界。細菌之中有好有壞,但只要整個系統維持平衡,你的腸道就是健康的。衰老、旅行和藥物治療都有可能造成紊亂,這正是一系列麻煩和痛苦的源頭。
塞雷斯是最早想要主動構建療法,來調控人體菌群的創業公司之一。2015年,他們的估值就達到1.3億美元,這多半是因為手握一個前景看好的候選藥物:從健康人的糞便中提取一組菌群,用酒精潤洗過后制成濃縮藥丸。
這種手段被專業人士稱為“糞菌移植”,而塞雷斯的口服藥丸在那時已經初現成效。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耐抗生素細菌之一,叫做艱難梭菌,感染它的患者往往在之前經歷了多次抗生素療法,以致腸道內的原住民細菌被掃蕩一空。早期臨床試驗顯示,塞雷斯的“菌群藥丸”對艱難梭菌感染的治愈率高達97%,這是傳統制藥公司需要仰視的數字。
所有人都覺得,美國食品藥監局(FDA)大概要批準第一種糞菌移植的藥物了,而塞雷斯自然搶得了先機,并且有望繼續攻克其他腸道疾病,比如病因不明、無可靠療法的克羅恩病。但2016年7月的二期臨床試驗結果不妙:接近半數的患者陸續重新感染,在統計上與未接受任何治療的對照組無異。
看來,實驗室精制的菌群藥丸是失敗了。
距離塞雷斯車程20分鐘的地方,另外一家叫做Open Biome的公司也想找到治愈艱難梭菌感染的法子,而且他們的產品已經先于塞雷斯奏效好幾年了。從附近居民管這里叫做“便便銀行”可以看出,他們打的也是糞菌移植的主意。
所不同的是,Open Biome篤信純天然無加工的糞便。上百名捐獻者每月來到這里,匿名留下一個個密封袋,里面裝著他們新鮮的屎。實驗員們為樣品稱重,并用布里斯托大便分類法(請自行搜索)分別歸類。然后加一點鹽溶液搖晃均勻,再冷凍起來。
大功告成。這些充其量就是冷凍大便的東西,接下來會被郵寄給各個研究所和醫院。自2012年成立以來,Open Biome已經成功地治好了超過1.5萬名艱難梭菌感染患者,而且重要的是,復發率很低。
如何把大便送進人體并不是治療的關鍵,灌腸、腸鏡或者口服膠囊都可以(是的,里面就是冷凍干燥的大便,馬特·達蒙在火星上用來種土豆的那種),按照研發主任史密斯的話來說,“任君挑選”。
然而,如何將產品規范化卻成了Open Biome的噩夢。除去為了活命豁出去的重癥患者,沒有人會認為這可以作為常規療法,更別提FDA那些堅持安全第一的保守人士了。雖然便便銀行排除了攜帶有害病原體的捐獻者,但沒有哪種測試能夠反映一個人體內菌群的全部信息——即使有,光是列表中的大腸桿菌數目就能把你嚇死。
而且,沒有人知道一個人的腸道菌群會對另一個人的健康產生什么影響,因為其個體差異之大,甚至可以達到90%。FDA在2013年宣布規范糞菌移植,受到沖擊最大的就是Open Biome這樣的公司了。
雖然便便銀行還能繼續存在,但一旦有新的更安全的療法出現,它就會慢慢被取代。
相比做法近似巫醫的Open Biome,塞雷斯在這一點上頗具自信,至少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來解釋,到底是什么擊退了艱難梭菌。根據塞雷斯的說法,艱難梭菌依靠膽汁酸為生,如果引入另一種與之競爭食物的細菌,比如芽孢桿菌和梭菌,艱難梭菌就會逐漸餓死。
所以塞雷斯的做法是,從健康人的大便中提取特定的50種競爭細菌,并且用酒精殺死其他的病原體。這樣生產出來的藥丸成分明確,如果療效尚可,應該是連FDA都會喜歡的糞便制品吧。
“一開始芽胞桿菌起作用了,大家都深受鼓舞”,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艱難梭菌的流行病學家戈丁對同行的失敗心有戚戚,他目前的公司Rebiotix也在研制糞便藥丸。他指出,所有建立在菌群基礎上的藥物研發都需要重新考量,因為糞便的神奇效果令醫學界產生了盲目自信,以為菌群的調控易如反掌。
Open Biome的史密斯也同意這個觀點,但他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塞雷斯的失敗反而對這個領域有著重要的貢獻。“當然這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但之前人們覺得只要是大便,不管怎樣都有用。現在我們起碼知道,它什么時候不起效。”
早在2008年就開始探索糞菌移植的凱利,是美國最早這么做的胃腸病學家之一。在數年的臨床經驗中,她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副反應,比如一位同時患有普禿的艱難梭菌感染者,自16歲起就不長任何毛發,連腋毛和眉毛都沒有,然而在接受糞菌移植后,新的毛發竟然開始生長。
直到凱利偶然跟同事提起,她才發現這并不是孤例。可惜的是,她無法倒回去分析兩名患者治療前后的菌群,看看究竟是哪種細菌的變化讓他們長出了頭發。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腸道菌群不僅對胃腸病有影響。一些患者移植之后體重發生了顯著變化,另一些則反映他們的抑郁癥消失了,而醫生們對此無從解釋。
這也是為什么,在國立健康研究院新近宣布的一項計劃中,所有接受糞菌移植的患者都要在移植前后進行體內菌群的測序:不僅是那些擊退艱難梭菌的,還包括所有其他可能帶來副反應的細菌。
而這是韋丹塔生命科學正在忙活的課題。在他們的實驗室里,數十臺桌面儀器在夜以繼日地分析來自世界各地的糞便樣本,并且復制出相同的菌群。有人懷疑,該公司25平方英里土地上的糞便濃度是地球上最高的。
他們的算法為每個糞便樣本給出最適合治療的疾病,其中匹配度最高的將進入臨床試驗。他們也有了自己的候選藥物,一個治療炎癥性腸病的細菌組合,包括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當然,是FDA喜歡的那種藥丸。
也許這才是糞菌移植的未來:自動化的儀器在無菌室里培養出對癥菌群,不需要健康的捐贈人,與新鮮冒熱氣的糞便無關。
(管月薦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