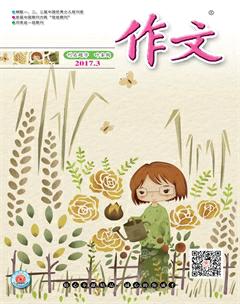家鄉啊,你可還是記憶中那般模樣
李儀
我的家鄉在湖南郴州,一個傳說中神農氏嘗百草的地方。
我從小生活在北京,對于故鄉郴州的印象模模糊糊,可是,那濃濃的故鄉情懷,卻像是深入到骨子里,鐫刻在靈魂深處,不曾因為距離遠而變淡變薄。
最能體現我對家鄉不變情懷的,就是我那一口帶著北京味兒的鄉音。雖然說著北京話,但自小在家庭的熏陶下,我對郴州話也不陌生。父親有時會用一口地道純正的家鄉話與我交流,那較為軟糯又抑揚頓挫的語調,郴州方言那特有的句式結構,在我并不是異常難懂。郴州方言那特有的n、l不分的輕柔與滑潤,形成了我對家鄉話最初的認知。“吃飯了沒有?”“吃掉了。”“累不累啦?”“不累嗷。”在“吃掉了”等簡潔的日常對話中,我的家鄉話一點一點流利起來。每每回到故鄉,當我用不夠原汁原味的家鄉話與鄉人交流時,彼此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能很快地熟絡起來。尤其是與我同齡的孩子,我們常常會在交友的煩惱、考試的困惑等方面迅速找到契合的話題,而后不生分地說著笑著。這種交流上的親近感有時甚至使我產生一種恍惚的感覺——我是打小就在這片土地上長大的,北京才是我漂泊寄居的地方。
我對家鄉的另一種情懷,就是對故鄉吃食的留戀。我并不是貪食之徒,處在繁華的大都市,從小到大可以說吃了不少美食,有的家鄉沒有,有的家鄉人則根本沒有聽說過,但我好像對這些美食都沒有什么特別的記憶。可是,只要雙腳一踏上故鄉的土地,一聞到故鄉美食的味道,我就沉醉其中,流連忘返。郴州有一些吃食,是北京沒有的,蘿卜條、糯米糍粑、倒缸酒……單是讀一讀這一個個滲透著故鄉特色味道的名字,已讓人饞涎欲滴了。就說那最常見的米酒,喝起來也與北京的不一樣。郴州人家幾乎每家都會自己釀米酒,用一個大缸放上米、水和上次釀酒剩下的米酒,經過長時間的發酵,大缸自然而然地就會分成兩層:甜酒、醪糟。老家說喝酒是“吃酒”,甜酒是可以直接飲用的。甜酒,入口時是甜的,慢慢地便會嘗出一絲辣意。在陰冷的季節里,這酒不會讓人不適應,反而會讓人感到一種暖意。剩下的醪糟一般用來做醪糟湯圓。再說糯米糍粑,它是故鄉人用特有的古老工具做出來的,特別好吃。做時先用木樁反復捶打煮熟的糯米,讓它不僅有黏性,而且還有嚼勁。烹飪的時候,用小火加少許水把甘蔗榨制的磚糖熬化,再放上糍粑去煎,最后做出來的糯米糍粑軟成了一攤水似的,有點黏牙,還裹著糖漿。當然,還有那咸咸辣辣的壇子菜腌蘿卜條,吃起來脆生生的,辣得過癮,咸得爽口,使我常常不忍放下手中的筷子。
故鄉讓我眷戀的,還有那特有的梅雨季節。很多人都反感它,覺得雨拖拖沓沓、反反復復下個沒完,三天一大雨,兩天一小雨。持續的時間久,不給人個痛快,還會覺得濕氣太重了,悶熱難受。但是,我卻很喜歡,因為只有在這樣悶熱潮濕的天氣里,吃很多咸咸辣辣的食物才不會上火,反而會有祛濕的效果。
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郴州。人在北京,遠離故土,隔著千山萬水,走不上那熟悉的山路,聽不到那親切的鄉音,吃不到那故鄉的美食,但故鄉的風物卻時不時出現在我的夢中。我且知曉自己真正的心意了,我當明了自己內心的牽掛了!人生漫漫,且行且珍惜,只是,我深愛的家鄉啊,你可還是我記憶中的那般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