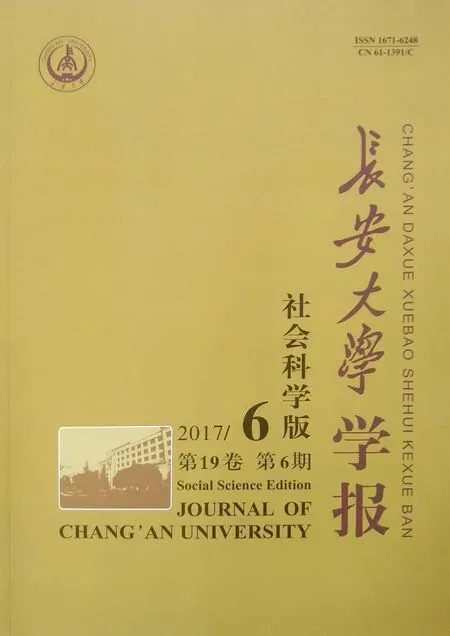張豈之與侯外廬學派
杜運輝
(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24)
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典型代表,“侯外廬學派”的產生與發展是當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方克立從嚴格意義上的學脈傳承來界定侯外廬學派,認為第一代以侯外廬為核心,包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等人,代表作為《中國思想通史》;第二代是新中國成立后隨侯外廬編著《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的“諸青”及他在1966年前培養的研究生和助手,包括張豈之、李學勤、何兆武、林英、楊超及黃宣民、盧鐘鋒等人,代表作是《中國近代哲學史》《宋明理學史》;第三代是侯外廬1976年后招收培養的研究生以及第二代學者培養的學生,包括姜廣輝、陳寒鳴等,代表作有《中國經學思想史》《中國儒學發展史》等[1]。而從廣義來說,侯外廬學派還應包括認同侯外廬研究范式的其他學者,如黃宣民曾提出劉澤華“與他的合作者的思想和學術研究成果可歸之于‘侯外廬學派’”,并得到劉澤華的當場首肯[2];蕭萐父與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認為“呂振羽、杜國庠、侯外廬等……使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與中國哲學發展的特點初步結合,……這就為中國哲學走向科學化開辟了道路,奠下了基石”[3],蕭萐父還莊嚴地宣稱:“我們自愿繼承侯門學脈,自愿接著侯外老的啟蒙說往下講。”[4]吳光亦提出:“我內心始終把外老看作我的第一導師,我的主要學術研究成果也打上了先生學術思想的烙印……在學派上是甘居侯門的。”[5]此外,如田昌五等人都自承為侯外廬的弟子。在群星燦爛的侯外廬學派群體中,張豈之可謂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和最主要代表,如姜廣輝指出:“在侯外廬的弟子中,大家都公認張豈之先生是掌門人。”[6]張豈之與侯外廬學派的傳承與發展,本身已經構成中國當代思想史的重要篇章。本文嘗試對此進行初步探討,以期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進行。
一、侯外廬學派第一代學術共同體的重要成員
侯外廬史學的最大特色,是鮮明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西、馬融合會通精神。1928~1938年,他以十年之功譯讀《資本論》德文第四版,獲得“思維能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寶貴訓練”[7],“真正力圖以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路數來理解馬克思并研究歷史”[8];1934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開始確立社會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路徑與注重原著、善于決疑、獨立自得的治學特色。1941年“皖南事變”后,他在周恩來勸導下全力轉向史學研究,先后出版《中國古典社會史論》(1943)、《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1944)、《船山學案》(1944)、《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1944、1945),1947年與杜國庠、趙紀彬合著出版《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編),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949年2月,在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原中央城市工作部)的周密安排下,侯外廬與郭沫若、馬敘倫、翦伯贊等由香港經東北抵達北平,4月被任命為解放后的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第一任系主任,10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期間,他組織出版《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修正版)和《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和新哲學座談會。他還與郭沫若、范文瀾、胡繩、艾思奇等應邀到北京大學講學,并在北大開講“中國思想史”選修課,這對哲學系學生張豈之產生了深刻影響,張豈之在比較后感到“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分析問題非常深刻,能夠把某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深層原因挖掘出來,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的表層,給人的啟發很大”[9]、“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學術思想進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強的說服力,他是我走向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引路人”[10]。此后,張豈之經常到侯外廬家中去請教,從此開始了38年的師生情誼。侯外廬也許想到了自己當年向李大釗請教的情景,根據李大釗“搞理論應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從原著中汲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真諦”[7]的珍貴教誨和自己多年的治學體會,希望張豈之研讀《共產黨宣言》等經典原著。1950年3月,侯外廬被任命為西北大學校長,而張豈之則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哲學碩士研究生。短短一年多的接觸,張豈之的治學旨趣和學術修養引起了侯外廬的深切關注。
主持西北大學期間,侯外廬高度重視師資隊伍和新校風建設,高揚“求實創新”的大學理念,倡導愛國主義教育和“實事求是、嚴肅工作的新校風”“師生互助、教學相長的新學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新研究風”的“新三風”,使西北大學的面貌煥然一新。為了加快充實青年教師隊伍,這位遠見卓識的引路人特意選調尚在清華大學讀研究生的張豈之到西北大學任教。侯外廬在生活上對青年人關懷備至,在工作上則倡行“我看你們能挑50斤,我立即加碼到60斤;你能挑60斤的擔子,我就讓你挑70斤”的“層層加碼法”和“在水中學習游泳”的“下水游泳法”。張豈之到校僅兩三個星期,侯外廬就安排他給法律系學生講邏輯學,并站在窗外聽課,下課后對他說:“錯誤還沒有發現,大體上還是清晰的,不過舉例都是(蘇聯)教科書上的老一套。其實,關于邏輯的舉例,實際生活中有的是,你可以找一找,這樣,你的講課可能會生動一些。”[11]他不僅主張“在學術研究中首先要把握正確的研究方向,找好‘生長點’”[12],而且特別強調青年教師要教學與科研并重互進,這既是為了引導新時代青年避免自己被“文字晦澀難懂”[7]、“不善于用明確的語言來表現明確的思想”[13]等善意批評的艱澀文風,也是他培養人才的有效舉措,這對我們今天的大學學科建設仍有重要啟迪。
1954年4月,侯外廬調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并兼任西北大學校長(至1958年7月)。從1954~1957年,他以宏偉的戰略眼光精心籌劃和有效組織,迅速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中國思想史研究室組建了一個中青年學者結合、多學科人才兼備、中西馬文化會通的學術共同體。他不僅聘請韓國磐、白壽彝、賀昌群、王毓銓、邱漢生等著名學者,而且連續借調張豈之及選調李學勤、楊超、林英、何兆武等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工作,1955年底還招收祝瑞開為副博士研究生。侯外廬精心挑選的這幾位年輕人不僅具有文史功底較厚、異常勤奮、學風樸實的共同特點,而且各有所長:“豈之哲學基礎扎實,歸納力強;學勤博聞強記,熟悉典籍;楊超理論素養突出;林英思想敏銳,有一定深度;兆武兼通世界近現代史,博識中外群籍。”[7]侯外廬深謀遠慮,把張豈之的編制仍留在西北大學,他說:“你半年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帶回去講半年。”[14]可以說,侯外廬的史學成就“吸引了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并在長期的共同學術實踐中熔鑄了“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15]的研究范式。與同時代的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相比,侯外廬最善于組織和領導多樣性統一的學術共同體,最善于發現并在學術共同體中培養青年人才,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侯外廬學派得以葆有生機的重要原因,是其能夠以堅強的理論自信走一條中西馬融合會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學術民族化高度統一的學術道路的組織保證。
為了使年輕人盡快轉變為成熟學者,侯外廬努力培養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選擇、彼此切磋、信任友誼等優良作風。他要求大家集體坐班,既放手讓學生們承擔較多科研任務,又嚴格要求而一絲不茍。他最初是每天指導大家逐條核對、修訂《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及《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早期著作的引文,考察所引材料與觀點是否相合,這不僅鍛煉了大家的古文獻工夫,而且通過查對和思考使他們“逐漸了解他的研究成績和治學途徑”[16],如中國古代文明路徑說和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從而達到學術研究范式的思想認同和信念認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之余,侯外廬幾乎每天都要抽出一兩個小時與學生們討論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問題,從不因看法不同或觀點有異而責備學生或發脾氣,“關于一些思想家的評價,往往在師生的交談中產生出新的觀點和論斷”[17],而學生們更從這種平等友愛的親切交談中深受教益。侯外廬的崇高人格使大家深深感動,都很驚奇他能在艱困危險環境中寫出那么多學術著作,特別是切身體會到他如何在研究工作中投入全部精力,如李學勤回憶:“有一天,侯外廬打電話要我晚上去幫他查一些材料。他坐在書桌前振筆疾書,一面指示我查閱幾個問題的史料,翻檢了許多書籍,通宵達旦。”[16]侯外廬深切關懷著每一個學生,這個新型科研集體“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署名或因稿費而發生爭執的現象。助手們做的工作,外廬先生記得很清楚,從來沒有虧待過同志們。一種在共同事業中結成的師生情誼,歷久不衰”[17]。如他在1956年新版《中國思想通史》序和《韌的追求》中都高度評價“諸青”的重要貢獻。值得稱道的是,這個學術共同體不僅有侯外廬、邱漢生等的親切指導,而且青年人之間也互敬互愛、互為師長,如張豈之說:“我從其他中青年同志那里也學到不少東西。我們寫完稿子,往往互相傳看,相互修改,有不同的意見通過討論、磋商來解決,相互尊重、謙讓,團結和睦,沒有發生過爭署名之類的事情。”[18]通過邊干邊學、在科學研究基礎上著述的“下水游泳法”和集體合作工作方式的嚴格訓練,這一批青年學者很好地完成了所擔負的研究任務,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功底,迅速成長為侯外廬學派的中堅力量。這種良好學風不僅深刻影響到侯外廬學派的長遠發展,而且為編著《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奠定了堅實基礎。
1956年,侯外廬組織出版《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1957年出版《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增訂本。這樣,《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編著就迫切地提到日程上來。1957年夏,侯外廬以雄偉魄力果斷地啟動了《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編寫工作。他事先征求杜國庠的意見,然后在趙紀彬、邱漢生、白壽彝、楊榮國、楊向奎和張豈之、何兆武、李學勤、楊超、林英等“諸青”出席的編寫工作會議上提出編寫提綱和章節內容,共同討論和補充修改,最后確定編寫分工和完稿時間。作為主編的侯外廬不僅確定全書的指導思想和編寫計劃、親自撰寫第一章,而且既緊張又興奮地指導“諸青”撰述。為了把“諸青”所分擔的各章納入嚴整的體系而保證全卷學術水平,他“將自己對第四卷包括的各種思潮和每一個主要人物思想體系的研究結論,無保留地交給他們……將自己經多年深思而形成的,論述這些人物、思潮的論點乃至基本邏輯,反反復復地用討論方式灌輸給他們”,此外則“任憑他們去發揮自己領悟理論,駕馭材料的能力,去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創見”;在完成通貫全書的審改定稿時,他“費力較多之處,往往是把敘述上升為概念”[7]。經過他的修改勾勒,所有稿件“就像被一條無形的線索所貫串,納入了他所構思的體系”[5]。僅僅兩年,這個新型學術共同體就在1959年夏完成了初稿,“諸青”不僅承擔了全卷編寫的組織事務和協調聯絡工作,而且事實上承擔了執筆編著的“重頭戲”。侯外廬統馭全局的卓越能力和集體合作方式,對張豈之此后的學術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
直接參與并成功編著《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是張豈之等青年學者走向學術成熟的重要階段。第一,“諸青”忠實地實踐了侯外廬“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當以文獻學為基礎”[19]的嚴格要求,他們在文獻方面廣泛搜集包括手抄稿的原始資料,對文獻整理深有體會,如李學勤指出:侯外廬對《東西均》的整理、研究“實開風氣之先”,“在侯外廬指導下,……我們標點了方氏的一些著作出版,還組織編纂方氏的選集、全集”[16]。張豈之剛開始不大適應這種圍繞課題的集體研究方式,但在實踐中體會到其行之有效,“在評價柳宗元思想時,外廬先生指導我作詳細的編年筆記(即按柳宗元的作品寫作年代作出摘要和分析要點),例如關于柳宗元的《天對》,我們就檢閱了有關屈原《天問》的各種注本,從文字到思想內容加以比較,由此對《天對》作出了我們認為是比較恰當的評價”[17];在寫王廷相時,他又下大力氣通讀了《王氏家藏集》。對原著的透徹把握,奠定了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第二,“諸青”貫徹了侯外廬“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古代史料結合起來,作統一的研究”[7]的深切教誨。侯外廬強調馬克思主義對于提高思想覺悟和研究水平的極端重要性,強調“對于自己進行研究所運用的原理的基本概念加以正確而深入的理解和澄清”[20],他不僅自己每天都擠出時間研讀馬克思主義,每有體會即滿懷喜悅地告訴學生們,潛移默化地提高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的自覺性;而且對學生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抓得很緊,如指定他們攻讀《資本論》第三卷的“地租論”等篇章。第三,“諸青”繼續堅持了“層層加碼法”和“下水游泳法”。剛開始侯外廬只讓他們分擔很少章節,指導他們圍繞課題閱讀原始材料、編寫資料長編、嘗試提出觀點,并仔細修改他們的初稿;而當學生如期完成任務后,侯外廬又根據其實際能力而分配新課題。這種緊張而又愉快的研究使張豈之始終處在緊張的工作狀態,腦子里不時思考有關問題。第四,“諸青”發揚了討論磋商、相互改稿的良好作風。針對研究過程中的疑難問題,侯外廬經常與學生們舉行生動活潑、無拘無束的小型討論會,通過討論加深理解、啟發思路。第五,更為重要的是,侯外廬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視為學術研究的靈魂,始終引導學生們把研究工作與社會責任統一起來,堅決反對在研究工作中追逐個人名利。這種以信念培育、道德養成、學術訓練、情感認同為基礎的學術實踐熔鑄了共同體的深厚凝聚力和巨大創造力,張豈之等“諸青”的第一稿成功率相當高,這得到侯外廬的高度贊揚。
1957~1959年,侯外廬學派不僅編著了《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而且密集出版了侯外廬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略》(張豈之、李學勤、楊超、林英編寫)、《陳確哲學選集》及增訂本(李學勤、張豈之、劉厚祜等編輯)、《中國歷代大同理想》(張豈之、楊超、李學勤執筆)、《王廷相哲學選集》(魏明經、張豈之、劉厚祜、牛繼斌等編輯)、《明道編》(張豈之、劉厚祜標點)、《伯牙琴》(張豈之、劉厚祜標點)、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史略》,何兆武譯),及1957年開始整理、1961年出版的方以智《東西均》。此外,李學勤還出版了《殷代地理簡論》。侯外廬學派所顯示的生命活力和工作效率,是令人相當驚嘆的。可以說,侯外廬以其對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憑藉其政治地位、崇高人格和學術威望,為“諸青”撐起了一把遮風擋雨的巨傘,引導著他們走在光明、正確的人生和學術道路上。
從1959年開始,侯外廬的封建土地國有制觀點受到錯誤批判,但他頂著壓力繼續從事學術探索和學派建設,1959年8月選調黃宣民、唐宇元、步近智、陳谷嘉等進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組工作,1963年9月、1964年9月又先后公開招考并錄取盧鐘鋒、孟祥才為研究生。對這些新生力量,侯外廬不僅自己親自施教,而且請何兆武為他們講解西方思想史,請張豈之、林英講邏輯學。1961年夏季,步近智在侯外廬鼓勵下寫成《辛亥革命準備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君權”和封建道德的批判》一文,《新建設》主編張友漁決定刊用并提出修改意見,侯外廬遂請研究室青年學者一起討論,最后由張豈之修改定稿,這是步近智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在侯外廬的領導下,張豈之等“諸青”開始了傳、幫、帶的新使命,這一直持續到1966年。
二、侯外廬學派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的順利傳承
1972年起,侯外廬不顧當時混亂的環境和自身傷痛,以巨大毅力重新著手開展學術活動,不僅編輯《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而且在1973年4月再次組織撰寫《中國近代哲學史》,期間與時在西北大學的張豈之密切通信,1975年還特意要他到北京家中住了約10個月。張豈之一方面照顧侯外廬的生活,一方面協助他修改《中國近代哲學史》,事實上承擔了全書修改的具體組織工作,如他在1974年10月11日致信盧鐘鋒、黃宣民、樊克政:
全稿打印出來,分到每個同志之手,起碼要到十一月初。廿號至月底打印任務甚大。廿號至月底共十天,我意先開始第一步的修改。給我的打印稿,我已陸續看完了。以下五點是我看了打印稿后提出來的,還不是無根據的亂說。
(1)第一章第一節改寫一下,著重說明一個問題: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要添馬、恩關于鴉片戰爭的論斷。具體改寫意見,再面談。由小樊駕輕就熟地改吧!(2)第二章太平天國交林英修改,請他將關于《資政新編》重新寫出。(3)第三章改動較大,包括改寫、調整等。小黃和我擔任。(4)《大同書》再改一改,鐘鋒把整個改良主義都摸了,現在再來修改《大同書》最好。(5)嚴復一章補充介紹歐洲哲學,請老何補。以上工作,廿號至十一月一號以前完成,看有無可能。
第二步修改,大家對全稿提出意見,進行深入討論,對全稿作統一(觀點、文字、體例等)。用一個月左右時間。
我的總的意見是:似乎不必從廿號一直到十一月初全都用在看稿上。如果看半個月,再議半個月,時間拖得很厲害。我們編寫組人不多,可以采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不一定過于拘泥于程式化的程序。稿,大家平時都看了,有些地方要著重改,心里可能是有數的。我們人不多,有些問題隨時可以討論,也不一定過于拘泥于“開會”。事實上,我們在下面商量很多。
以上五點如能盡快完成,那么,全稿的修改問題就不會太大[21]。
1978年2月,《中國近代哲學史》出版。同年,侯外廬招收柯兆利、姜廣輝、崔大華為研究生,這是他正式招收的最后一批學生。隨后,他組織了兩次重大學術活動,這就是編著《中國思想史綱》與《宋明理學史》。因有前期基礎,《中國思想史綱》的編寫極為迅速,1980年5月上冊出版,系根據張豈之、李學勤、楊超、林英、何兆武執筆的《中國哲學簡史》上冊(1963年11月版)修訂增補而成。1981年10月,由《中國近代哲學史》修改而成的《中國思想史綱》下冊也順利出版。
早在1959年《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編寫時,侯外廬就開始醞釀《宋明理學史》編寫計劃,但因種種原因而被迫整整推遲了20年。當1980年邱漢生再次提議時,侯外廬已難以全面、具體地指導這項研究,于是“將編著《宋明理學史》的計劃委托于多年的合作者邱漢生先生和自己的得力助手、大弟子張豈之先生領軍執行”[22]。這一時期,張豈之不僅撰寫張載、羅欽順等章節,而且投入巨大精力和時間組織、協調寫作進度,如他在1982年4月27日、5月14日、5月21日、8月30日、9月24日致信黃宣民、盧鐘鋒:
昨天上午和邱先生就如何修改理學史上卷事交換了意見,決定本星期四(四月廿九日)上午八時半,請你二位,還有冒懷辛、樊克政同志到邱先生家開會。
北宋部分稿,我已統了宋初三先生和邵雍兩章稿,刪改較大,已送邱先生,請他審定。元代部分,再有一天,我即可全部整理完畢;這一部分,我覺得基礎還是比較好的。
元代稿我已“統”畢,交邱先生,請他過目。……南宋部分由邱先生“統”,七月我來京再看。……已經初步“統”的稿,有的有較大的刪和補充,這些都要請原執筆的同志過目。這件事如何做,請與邱先生商量。
關于楊萬里、王蔭麟兩章,我作了一些修改,還曾給老步(近智)一函,請他在個別地方再作斟酌。
我在夏天將全稿看畢,有些稿件我動手作了較大修改,有些我未作修改,提了修改意見,請轉邱先生斟酌,并希望由原執筆先生修改。不知這一步是否已經做到[21]?
1983年3月,《宋明理學史》上卷送交人民出版社,邱漢生高興地致信張豈之:
你兩次來京,完成了《宋明理學史》上卷的定稿工作,這是很重大的貢獻。他日書出版,讀者將從你的辛勤勞動中得到有益的幫助。為此,我個人對你是十分感激的[21]。
《宋明理學史》上卷出版后,張豈之又請林甘泉出面召開質量評議會。1987年6月,《宋明理學史》下卷出版,這部“建國以來以來第一部系統論述宋明理學發展全過程的學術思想史專著,備受海內外學界的關注”[23],圓滿地完成了侯外廬生前交代的最后一項重要任務。《宋明理學史》的編著和出版,客觀上標志著侯外廬學派順利地完成了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傳承與發展。
三、侯外廬學派第二代學術共同體的領軍人物
侯外廬于1987年9月去世后,白壽彝鄭重囑托張豈之:“外廬同志對中國史學研究貢獻很大,你一定要組織幾篇有份量的紀念外廬同志的文章。”他后來又托史念海、瞿林東捎話,希望在西北大學成立侯外廬史學研究室,希望年輕學者特別是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帶頭研究侯外廬的學術思想。經過侯外廬及其學術共同體30年的精心培養和自己的艱苦磨煉,張豈之具備了堅定的思想信念、高尚的道德人格、深厚的學術修養和卓越的學術組織能力,成為侯外廬學派的第二代學術帶頭人。黃宣民曾云:“豈之于我,亦師亦兄。”張豈之在“后侯外廬時代”的學派傳承和發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至少有幾個方面:
(一)深刻總結與大力弘揚侯外廬學派的研究范式
張豈之透辟地指出,侯外廬學派的顯著特點和重要貢獻有兩點:第一,“將社會史的研究和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結合起來”[17]。他認為將社會史與思想史相貫通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創見,“外老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方面創新成果比較多,其原因就在于他追求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思想史的特點相結合”[22],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與創新發展。他自己在指導博士研究生時,就經常強調“對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統一分析……一定要有社會史的基礎”[24]。第二,“注重發掘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的特點,不套用西方的模式”[24],也就是侯外廬倡導的“不茍異亦不茍同”[25]、“求實而不尚空談”[7]的獨立自得治學風格。這兩個特點結合在一起,就是要“既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作為研究的指導,又繼承中國思想學術史的優良傳統”[26],實現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國化、民族化、本土化,這是以侯外廬為代表的“中國思想通史”學派之所以取得巨大學術成就的實質和關鍵。張豈之的這些精辟論斷,為我們準確把握侯外廬學派的思想精髓提供了指針。更為可貴的是,他為后來者樹立了繼承與創新相統一、“照著講”與“接著講”相映照的模范,主張對侯外廬的學術思想要保持一種自覺的反思意識,要“解決其中的一些尚未解決的疑難問題”[27],如社會史分期的法典化標準中的制度變遷與生產力變遷的關系、政治法律制度變遷與經濟制度變遷的關系等問題,這開辟了思想史研究日新不息的廣闊空間。
(二)高度重視侯外廬學術思想研究和著作整理出版
1987年以來,張豈之發表了大量文章闡釋侯外廬的治學精神、學術路徑、思想精義和歷史貢獻;他參與編著《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1987)、《紀念侯外廬文集》(1991),主編《中國思想史論集》第2輯(紀念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專集,2003);支持《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開辟“紀念侯外廬先生逝世一周年”專欄和西北大學設立“侯外廬學術講座”(2012)。此外,還組織召開了“侯外廬學術思想討論會”(1988)、“紀念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2002)、“侯外廬學術思想研討會”(2016),這些會議與“紀念侯外廬同志學術討論會”(1988)、“紀念侯外廬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1993)、“紀念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暨中國思想史學術研討會”(2003)、“侯外廬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2013)等,有力地推動了侯外廬學術思想的研究和宣傳。張豈之2012年開始主編《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33卷),2016年由長春出版社正式出版,為21世紀的侯外廬學術思想研究提供了最完整而權威的文獻支撐。《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與方光華等著《侯外廬學術思想研究》(2015),代表著當代侯外廬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
(三)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梯隊建設
侯外廬學派生生不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僅善于團結志同道合的不同地域、不同學緣、不同學科的學者,而且善于發現、選拔和在學術共同體中培養青年學者。張豈之高度重視侯外廬學派的當代建設,如他在《宋明理學史》編著期間的1982年5月21日就致信黃宣民、盧鐘鋒:
我覺得既要有人統稿(否則不成其為一部書,而成為論文集),又要使同志們在具體研究工作中加深學術感情,不致發生其他的事[21]。
1983年2月8日,他又致信黃宣民:
外老培育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隊伍如何加強?……任(任繼愈——筆者注)先生那里隊伍建設得很好,我們如何迎頭趕上?請考慮[21]。
張豈之指導研究生們盡可能完整地、系統地閱讀研究課題的原始資料,編出資料長編,在此基礎上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他發揚侯外廬學派集體合作的研究方式,引導博士生參加研究所的集體攻關項目,培養其科研集體精神;發揚侯外廬學派互相磋商、互相改稿的優良作風,主張研究生之間“互挑毛病”(相互討論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見);發揚侯外廬學派傳、幫、帶的培養方式,如請方光華、謝揚舉、張茂澤等幫助指導年輕博士生。他在主編《中國思想史》(1989)、《中國傳統文化》(1994、2005)、《中國歷史十五講》(2003)、《中國學術思想編年》(2005~2006)、《中國思想文化史》(2006)、《中國思想學說史》(2007)等著作時,就引進了李曉東、張茂澤、方光華、程鋼、范立舟、肖永明等諸多青年學者,使侯外廬學派呈現出勃勃生機。
(四)繼承和光大侯外廬學派“善于決疑”的學派作風
張豈之指出,侯外廬學派“特別注意解決前人未解決的歷史疑難問題,具有打‘攻堅戰’的勇氣和魄力”[17]。能夠不斷地發現新問題、提出新問題和解決新問題,是侯外廬學派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針對社會史上封建制的法典化與歷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豪族地主與庶族地主、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的特點等疑難問題,思想史上的氏族制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影響、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興起的社會原因、儒學的形成及其演進階段、對諸子之評價、秦漢時期社會與中國思想的特征、中國思想史的經學形式及其內容實質的相異性、豪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分野與中國思想史演進的關系、中國哲學范疇之形態與實質、明清之際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重疑難問題,侯外廬學派都敢于直接面對并提出創造性見解,從而在一系列重大的基本理論問題上把中國思想史研究推進到新境界。張豈之認為:“學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數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創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27]他探索將思想史與文化史相結合、思想史與學術史相結合、提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精髓、弘揚中華人文精神等等,從新的維度發揚了善于決疑、善于創新的學派作風。
從侯外廬開始,侯外廬學派就致力于創造性地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與足以信征的中國史料之緊密結合,創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這得到學界的廣泛共識,如1975年冬白壽彝在拜訪侯外廬時就指出:“外廬同志在中國思想史的精深研究中,設立學術梯隊,這不是宗派,不是什么集團,而是學派,在學術體系上和研究方法上具有個性特色的學派,是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學術研究指導的學派。”[28]在自己的治學實踐和學術活動中,張豈之一直高度強調馬克思主義對思想史研究的指導意義,如他教導方光華:“博士論文需突出寫好一章,即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近代史學的聯系與創新”,“反對吸取中國傳統史學和外國史學中的優秀的東西”是“和唯物史觀不合”[24];他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明確堅持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的研究路徑。我們可以說,侯外廬學派的學術宗旨和根本標志,就是在中、西、馬思想文化資源的融合會通中建構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這是今天衡量一位學者是否歸屬于侯外廬學派的試金石。
四、結語
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潮的諸流派,既有基本立場、核心理念、理論目標的根本一致,也有著理論任務、個人素養、學術興趣、思想風格等多方面的顯著差異,呈現出“理一”與“分殊”相輝映的基本格局,使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整體上避免了偏滯僵化而永葆其生機活力。比如張申府、張岱年與侯外廬都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方向、中國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和對西方文化的開放態度。張岱年始終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但主要以概念、范疇、命題、體系的解析與詮釋的理論分析見長,而比較缺乏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具體探討;侯外廬則擅長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辯證統一中揭示中國思想文化的經濟根源性、社會階級性、意識形態性和繼承改造性。
張豈之有著高度的學派自覺,他強調“人文學派的形成,絕不是靠一些行政措施,也不是用一個模式制作出來的,而是在民主的學術環境中,研究者們認真地進行研究,逐漸形成不同風格、不同研究重點、不同研究隊伍的學派”[24]。他兼備深厚而廣博的史學和哲學素養,一方面強調“唯物史觀的精髓,就是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認識歷史”[27],這體現著學術研究方法論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認為張岱年“在中西對比中研究過中哲史許多重要問題,分析中國哲學概念和命題的獨特意義,提煉中國哲學思想系統,描述其歷史進程,同時還提出中哲史學科的宏觀理論,開拓了新的研究模式,形成了有特色的一家之言”,贊揚張申府、張岱年首倡的“文化綜合創新說”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方法論原則之一”[29]。他創造性地把“文化綜合創新說”的哲學基礎——“兼和”界定為“兼容并包”與“和諧統一”之兩極相通,主張既要重視事物的多樣性統一,更要“經過獨立的研究和努力,熔鑄成自成體系的學術研究成果”[27]。我們可以說,張豈之的治學路徑,體現著面向社會現實問題而會通侯外廬學派與張申府張岱年學派的研究范式和鮮明特色,這是當代中國思想史、哲學史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導向和現實道路。
[1] 方克立,陸信禮.“侯外廬學派”的最新代表作——讀《中國儒學發展史》[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2):33-37.
[2] 劉澤華.《中國儒學發展史》序[C]//黃宣民,陳寒鳴.中國儒學發展史.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1-2.
[3] 蕭萐父,李錦全.《中國哲學史》“導言”[C]//蕭萐父,李錦全.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
[4] 蕭萐父,許蘇民.“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紀念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J].江海學刊,2003(1):134-141.
[5]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紀念侯外廬文集[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6] 方光華,陳戰峰.人文學人——張豈之教授紀事[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
[7] 侯外廬.韌的追求[M].北京:三聯書店,1985.
[8] 何兆武.歷史理性批判散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9] 張越.關于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張豈之教授訪問記[J].史學史研究,1995(3):40-46.
[10] 湛風,鄭雄.在人文學術園地不懈耕耘——張豈之先生訪談錄[J].中國文化研究,2009(2):1-17.
[11] 張豈之.春鳥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2] 閻愈新.侯外廬出長西北大學[J].百年潮,2004(2):35-38.
[13] 黎澍.反對故作高深[J].學習:半月刊,1951(8):26.
[14] 張洲.侯外廬在西北大學[J].文博,1996(4):61-65.
[15]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6] 李學勤.深刻的啟迪——回憶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N].光明日報,1988-08-10(3).
[17] 張豈之.遠見卓識的引路者——略論侯外廬先生對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的卓越貢獻[J].哲學研究,1987(11):34-37.
[18] 張豈之.儒學·理學·實學·新學[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
[19]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M].重慶:文風書局,1946.
[20] 何兆武.歷史理性批判散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21] 杜運輝.侯外廬先生學譜[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22]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論集:第2輯[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23] 盧鐘鋒.理學研究的創新之作:《宋明理學史》[N].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09-28(4).
[24]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張豈之教授與研究生論學書信選[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7.
[25] 紀玄冰.思想史研究的新果實——評侯外廬著《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J].讀書與出版,1947,2(5):35.
[26] 張豈之.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M].長春:長春出版社,2016.
[27] 張豈之.張豈之自選集[M].北京:學習出版社,2009.
[28] 張豈之.憶壽彝先生和外廬先生的一次談話[J].史學史研究,2000(3):5-6.
[29] 張豈之.《張岱年哲學研究叢書》總序[C]//劉鄂培,杜運輝.張岱年先生學譜.北京:昆侖出版社,20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