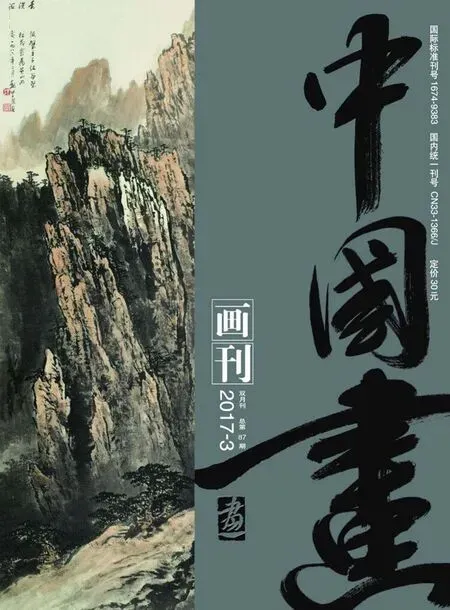玄秘與幽深—龐飛山水畫追求的境界
文/尚輝
龐飛山水畫的與眾不同,在于他從山石的曲折與水墨的漫漶中呈現的境界。

松江 45cm×48cm 2012年 龐飛

洪谷 200cm×98cm 2007年 龐飛
當下山水畫創作以兩種形態為主,一是過度強調寫生的作用,而這種寫生又流于蜻蜓點水式的采風,因而這種形態的山水畫往往也就淪為水墨風景寫生,而不是具有豐厚文化意蘊的中國山水畫。二是過度強調筆墨的獨立性與恒久性,認為筆墨是由中國文化的審美理念和水墨宣紙媒材所決定的一種文化性語言。這種形態的作品試圖擺脫現實的情境感,一意在傳統筆墨的再度整合中生發新變。這兩種當下山水畫的創作狀態,在某種意義上,都揭示了藝術家所成長的年代對于文化認知的不同角度。前者立足于中國畫的變革,其思想基礎始自現實主義的思想影響,把山水畫的變革完全依托于對審美對象感受與感知的尊重和表達,而在實踐上忽略了中國畫意象性表現審美對象的獨特方式,以及筆墨語言作為這種意象傳遞的個性化創造的可能性。后者以“好”為準則,認為“新”與“舊”不是衡量中國畫的價值方法。這種反對藝術進化論的思潮,無疑出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思潮對于傳統中國畫的沖擊。這種藝術觀念的持有者試圖從恢復傳統山水畫的精神中,重新確立已被變革與斷裂的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

巴山途中 80cm×190cm 2008年 龐飛
顯然,當下山水畫的這兩種狀態,都反映了上世紀后半葉中國社會在推進現代性的過程中處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關系而呈現出的一種思想變遷。對于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中國畫家而言,他們既承接了這兩種思想的影響,也試圖從他們自身的文化成長經歷中探尋自己的道路。
龐飛的山水畫就是試圖從這兩者的缺陷中重新建立傳統與現代關系的一種藝術嘗試。他的山水畫,既不是用水墨直接呈現視覺所見的寫生性山水,也不是完全脫離對象純以傳統筆墨表現審美經驗的筆墨性山水,而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切入點。即,在表現現實性的山水上,不是照抄自然,甚至于也不是從寫生畫稿轉變而來,而是注重感受真實性的表達,這促使他把自己成長經歷中最為深刻的陜南自然山川的地貌特征,更多地通過綜合印象去提煉和概括。而這種提煉與概括的方法,則是和他對于傳統筆墨與現代水墨的綜合運用結合在一起的。在汲取傳統的養分上,他并不止于筆墨語言的研習,而是擴展至氣象、境界和品格等精神層面。比如,他的筆墨得益于五代北宋的巨然、范寬的較多,但他也更獲得了他們在氣象、境界方面的啟示。他以宋代山水畫工寫結合的方法,注重闊遠寧謐的意境營造,這就和當下許多僅僅從寫意性筆墨的角度表現山水的作品拉開了距離。顯然,宋人的法度與氣象開闊了他表現山水的空間。但在空間置景上,他又有自己些許獨特的偏好。比如,他的畫面視角調度仿佛一直處于半俯視的狀態,畫面上端鮮露天空與山峰,畫面下端也大多略去了近景,作品幾乎是山水中景的放大與擴充。他在畫面上,刻意表達的是巨巖深壑中各種巖層豐富的轉折變化,畫面也是通過這些豐富的轉折而造成曲幽的深度感。再比如,他畫面這種巨巖深壑的奇幻變奏,并非完全出于了然胸中的理性構思,許多奇幻的轉折,在筆者看來,都是來自他在皮紙上折褶滲化而出的水墨自然之趣。也即,他畫面大面積、整體性的虛實、濃淡、輕重變化,都來自于現代水墨的潛意識性。
龐飛的山水畫往往在眾多的山水畫作品中脫穎而出,這主要得益于他作品在視覺圖式上彌散出濃厚的古雅而清逸的氣息與境界。但這種境界又不完全同于北宋山水畫,那種視覺上的吸引還更多地來自于畫面整體墨色的影像感,忽重忽輕的墨色變化猶如舊照片經過歲月的漂染。應該說,是這種歲月漫漶的影像痕跡賦予了他的作品以神奇的魅力。富有意味的是,龐飛正是通過現代水墨的自然拓印與滲化、皮紙折褶的水痕與肌理以及筆墨鉤皴的毛松與澀滯,巧妙地呈現了這種歲月漫漶的影像效果,從而將傳統與現代、感受與筆墨、實景與虛境結合在一起。當然,在這種結合之中,他還注重巖石體塊和筆墨鉤皴的節奏感的平衡,使之呈現出某種音樂感的形式分割意趣,從而更顯得與當代視覺審美經驗的某種暗合。

仙居 45cm×48cm 2015年 龐飛

溪山清遠 200cm×100cm 2011年 龐飛

太行山居 200cm×80cm 2008年 龐飛

朱家角 120cm×120cm 2010年 龐飛
良好的家學淵源,使龐飛比他的同齡人有了更深的對于傳統筆墨的體悟。在形成他的這種水墨折褶山水畫的圖式之前,他曾畫過大量的意筆山水。尤其是受林曦明的影響,他在意筆水墨山水畫上用功最多。他的畫路也相對寬廣,除了山水畫,他喜愛畫大寫意荷花,并由此涉筆更加寬泛的寫意花鳥與工筆草蟲。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對傳統中國畫的廣博研習,這些對于筆墨的歷煉也都反饋到他山水畫上面的筆墨學養與筆墨格調。那種疏淡而毛澀的筆墨,既是他連接皮紙折褶與水墨滲化的筋骨,也是他營造玄秘與幽深山水畫境界的重要方式。當然,在筆墨的疏淡與蕭散的心性表達上,龐飛還要走許多的路,才能真正心手相應、吐納自然。但他畫面對于整體幽深氣象與玄秘意味的境界追求,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們這一代人對于意象觀照自然與表現主觀心性這一中國畫文化精神的理解與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