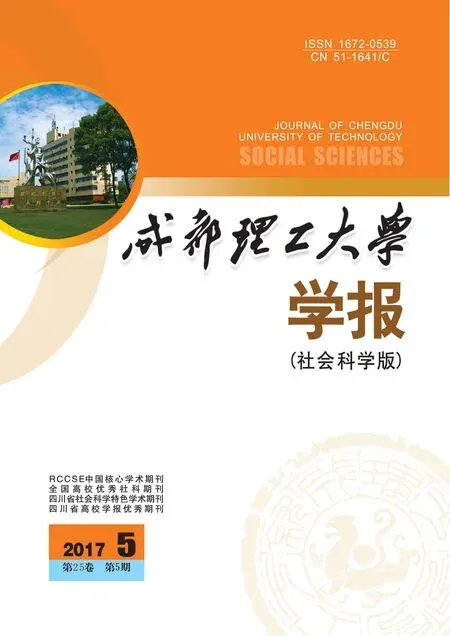論哈代小說《卡斯特橋市長》中的狂歡藝術
陳 珍
(青海民族大學 外國語學院, 西寧 810007)
論哈代小說《卡斯特橋市長》中的狂歡藝術
陳 珍
(青海民族大學 外國語學院, 西寧 810007)
《卡斯特橋市長》是哈代富有狂歡色彩的小說之一,作者主要以賣妻、酒宴、庭審和訐奸四次狂歡廣場為基礎,借助三類人物的特殊文學功能,通過對主要人物進行反復脫冕與加冕的狂歡化藝術手法,展示了主人公邁克·亨察德起伏跌宕的悲劇人生,深刻揭示了人生多變和命運無常的人生哲理。狂歡化不僅是反映作者人生觀的途徑,更是詮釋主人公人生沉浮的敘事手段,亨察德在屢次狂歡中走向沒落。
狂歡藝術;廣場狂歡;脫冕加冕;物品反用;三類人物
縱觀《卡斯特橋市長》的研究史,國內外學者主要從倫理學、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分析、原型學說、社會變革等視角對小說進行了多層面的研究,也有人從性格與環境的角度或從希臘悲劇的角度分析和探討了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筆者看來該小說的狂歡化藝術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哈代繼承了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怪誕現實主義藝術手法,在《卡斯特橋市長》中從人本主義出發描述了羊市賣妻、酒家歡宴、法庭鬧劇、訐奸游行等廣場狂歡景象,并借助騙子、小丑、傻瓜三類人物特殊的面具功能以及吹噓謾罵、詛咒發誓等非主流語言形式營造了激情的廣場狂歡氛圍,在狂歡語境中通過對主要人物升格加冕和降格脫冕的反復交替,展現了主人公亨察德起伏跌宕的悲劇人生,深刻揭示了世事多變命運無常的人生哲理。卡斯特橋狂歡看似熱鬧怪誕的表象下潛伏著悲苦心酸,繁榮與凋敝接踵而至,悲與喜、沉與浮、莊與諧形成了鮮明的二重性和不確定性。亨察德的人生歷程中的每一次大的波折都伴隨著一次色彩鮮明的廣場狂歡,也就是說,亨察德是在作者歷次狂歡化書寫中走過了他的悲劇人生。小說中的狂歡化書寫既是反映作者人生觀的途徑,更是詮釋主人公人生沉浮的敘事手段。
一、廣場狂歡與加冕脫冕
狂歡化詩學理論的文化源泉是古希臘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帶有原始宗教性質的狂歡節。酒神既是死亡之神又是再生之神,因此狂歡節具有鮮明的兩重性,酒神精神是狂歡節、狂歡化的精神根源和心理基礎。狂歡式沒有舞臺,無演員和觀眾之分,具有全民性、儀式性、等級消失、插科打諢等特征。狂歡式在文學中的文本反映就是文學的狂歡化,巴赫金指出,狂歡節上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象征意義、表現狂歡節世界觀的感性形式的語言,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文學的語言[1]158。狂歡式的文學表現就是狂歡化,狂歡化形式多樣,“他以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烏托邦的理想、廣泛的平等對話精神、快樂的相對性、雙重性等為基礎。”[2]79狂歡化有嚴格的時空特點,以廣場等群眾集結的環境為場地,一般為一個民族的節慶儀典,民間節慶活動是狂歡文化的主要載體,廣場是展示民間狂歡文化的主要舞臺,“廣場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歡化的文學中,廣場作為情節發展的場所,具有了兩重性、兩面性,因為透過現實的廣場,可以看到一個進行隨便親昵的交際和全民性加冕脫冕的狂歡廣場。”[2]166在巴赫金看來,文學作品中情節上一切可能出現的場所,“只要能成為形形色色的人們相聚和交際的地方,諸如大街、小酒館、澡堂、船上甲板、甚至客廳……都會增添一種狂歡廣場的意味。”[2]166狂歡化文學在西方由來已久,在文藝復興時期以法國作家拉伯雷為代表的怪誕現實主義作家掀起了狂歡書寫的高潮,哈代為拉伯雷精神的追隨者和踐行者[3],在《卡斯特橋市長》中哈代將民間廣場的歡鬧氛圍和文化精神根據情節需求巧妙植入文本敘事之中,在一連串有因果關聯的狂歡化書寫中演繹了亨察德的悲劇人生。狂歡化書寫成為故事情節發展和人物命運轉折的重要語境和內在動因,亨察德的傳奇人生與四大狂歡場面息息相關,其中的加冕與脫冕促成了他命運的根本轉折,故事情節也因此得到了相應的拓展。
(一)羊市賣妻
羊市賣妻是《卡斯特橋市長》的開篇狂歡,亨察德在小說中一出場就帶著狂歡人物的色彩,在狡猾的賣粥婦的誘導下狂飲醉酒,失去理智后上演了一出離奇荒誕偏離常規的賣妻鬧劇,在羊市拍賣了妻子蘇珊和女兒伊麗莎白,羊市賣妻反映了怪誕現實主義的根本理念。在本次狂歡中,賣粥婦扮演了女騙子的角色,她一生所悟出的生意經是“正正派派做生意賺不了錢”,必須“耍滑頭,搞欺騙”[6]26,她始終奉行這種荒誕的人生哲學,她的詭秘行為給賣妻鬧劇增添了狂歡色彩,從敘事邏輯上為亨察德醉酒提供了似乎合理的理由。狂歡化書寫與民間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英國民間文學研究專家布里格斯在《英國民間故事和傳奇》中收集了一則“鞋匠賣妻”[4]的故事,內容跟《托馬斯·哈代的事實筆記》中記載的發生在作者家鄉多塞特地區的三則真實故事大致相同[5],從以上民間故事以及真實故事中都能發現亨察德賣妻的影子,格林斯萊德指出哈代筆記記載的希爾羊市就是小說中韋敦——普瑞厄茲村羊市的原型,它是當地最盛大的傳統集市,匯集了三教九流、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有休假的短工,閑逛的士兵,農村小店的老板等逛市的人,還有各類民間藝人和生意人,有拉洋片的、賣玩具的、做蠟像的、有通靈的怪物、游方郎中、賭套圈的、賣小擺設的、還有算命先生,這樣一個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環境從客觀上為狂歡創造了條件,民間集市本身就是一個喧嘩吵鬧、眾聲齊鳴的雜語世界,頗具狂歡色彩。民間文學般的賣妻鬧劇在解構常規倫理的同時蘊含了終與始、生與死的二重性,亨察德和蘇珊婚姻的終止孕育了紐森和蘇珊的開始,一段婚姻的死亡催生了另一段婚姻的新生,表現了狂歡化的未完成性和開放性。賣妻丑聞是與亨察德命運有關的第一次狂歡化書寫,為亨察德進行第一次脫冕,為他的日后悲劇埋下了伏筆,從敘事的角度為情節發展留下了諸多懸念,為蘇珊尋夫和紐森尋妻創造了條件,也為伊麗莎白的身世之謎留下了線索。
(二)酒家歡宴
另一個狂歡化書寫是王徽旅館鎮上政要和富商歡聚的宴會,這里亨察德已從昔日窮苦的打草工變成了聲名顯赫的一鎮之長,眾星捧月,權高位重,這是對亨察德的唯一一次升格加冕。作者沒有按傳統的時間順序細述主人公的發跡過程,而采用跳躍式的敘事手法展現了多年后主人公事業發達,春風得意的另一番景象,彰顯了他人生的戲劇性變化。但是,在看似一片繁榮的表象下卻隱藏著潛在的危機,宴會結束時已怨聲四起,市民們對亨察德卑鄙的經商行為頗有微詞,對亨察德的品行開始產生懷疑,預示了亨察德人生在經歷了短暫的繁華后即將到來的蕭條,其悲劇沒落的結局隱約可見,大起必然孕育著大落,起落有序,榮枯有秩是生命的真實軌跡,頹勢將至,惡兆先行,這次顯形的加冕實際上是一次隱形的降格脫冕。除了彰顯主人公命運的起落波動外,這一狂歡化書寫在文本敘事上起了承前啟下的紐帶作用,就在這此歡宴上作者安排蘇珊和亨察德相遇了,這一環節在小說情節發展上起到了鏈接和推進作用,從此情節更加曲折多變,人物關系更加復雜微妙。在亨察德的情感場域,蘇珊的登場必將導致露塞塔的退場,進與退、新與舊之間形成了狂歡化二重性。為慶祝一個特殊的日子而進行的民間娛樂會是小說另一個具有狂歡意蘊的場面,市長亨察德為市民準備了傳統游樂節目,天不遂人愿,那天大雨滂沱,會場顯得非常狼狽,無人光顧,而法夫瑞那邊卻熱鬧非凡,歌舞音樂,人們趨之若鶩。從故事情節上來說這一片段固然并不重要,但在故事的整體脈絡上來說還是意義非凡的,它預示了民心已向代表新世界、新觀念的法夫瑞那邊傾斜的跡象,而代表舊世界、舊觀念的亨察德開始被人冷落。從狂歡化理論分析,這是對法夫瑞的加冕,對亨察德的脫冕,新舊對比,升與降之間為文本增添了動感張力。
(三)法庭鬧劇
賣粥婦在法庭上揭穿亨察德的賣妻丑聞的事件是《卡斯特橋市長》最關鍵的狂歡情節。亨察德因為是上屆市長,所以擔任治安法官參加輕罪審判,對微小過失進行及時審判和處理。這次庭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賣粥婦當庭揭發了亨察德隱匿了近二十年的賣妻罪行,這一舉動一下子顛倒了亨察德和賣粥婦之間的關系,原來的法官成了罪犯,罪犯成了法官,審與被審瞬間換位,加冕與脫冕共存,高高在上的“國王”瞬間變成了“奴隸”,“奴隸”成了主宰乾坤的“國王”,實現了民間對官方的戲謔解構,體現了狂歡化主張生死榮枯、新老更替、起落交錯的變化的精神內核,旨在呈現一個變化的世界和流動的人生。三類人物的道具功能為本次狂歡增添了狂歡籌碼,小丑治安警察斯塔伯德的猥瑣懦弱和騙子賣粥婦的機智果敢間形成的反差使狂歡變得更加詼諧幽默、滑稽可笑。因賣粥婦詭秘地透露了風聲,引來了異常多的圍觀者,所以引起的轟動“大得無法形容”[6]249,哈代沒有極力渲染這個動人的狂歡場面,但讀者可以感受到令人捧腹的熱鬧氣氛。這個出人意料的法庭鬧劇給了亨察德沉重打擊,他很快就“名譽掃地”,從此他的氣運驟然下降,社會地位“急轉直下”[6]296。這個戲劇性的變化是亨察德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丑聞暴露使他身敗名裂,又因固執偏信商業上慘遭挫敗,從此一蹶不振,開始踏上了悲劇之路。禍不單行,亨察德愛情上也受到重創,因為丑聞使露塞塔看清了他的“真面目”[6]222并決意棄之而去,他們的愛情危機導致露塞塔寫給亨察德的情書落入趙普手中,成為訐奸游行的重要素材,因此庭審狂歡在文本敘事上是訐奸游行的前提鋪墊。
(四)訐奸游行
訐奸游行是《卡斯特橋市長》中起關鍵作用的另一個重要狂歡情節,也為小說掀起了又一個高潮。訐奸游行是英國古老的民間廣場現象,也叫司奇米特(Skimmington Ride)或粗糙音樂(Rough Music),是社區成員組織起來揭露懲治有悖于道德規范行為的一種民俗事象,主要針對傷風敗俗的男女不正當關系或家庭暴力, 這類民間自發的懲罰活動具有相當大的社會約束力,它從輿論的角度維護正常規范的男女關系和家庭倫理。《卡斯特橋市長》中的訐奸游行策劃于被作者稱之為米克森巷的教堂的最低等的彼得手指客店,訐奸游行的發起者小丑似的人物趙普在他的請求遭到斷然拒絕后公然透露了他的意圖——“寒傖寒傖”“本城一個高高在上的人”,“這種穿著綢緞、蠟人兒似的、盛氣凌人的東西”[6]320,訐奸游行的矛頭直指露塞塔,這個“花里胡哨”、“水性楊花”、激起民憤的沒有口碑的上等人。南斯說她丟了她們的臉,賣粥婦恨她沒有感謝她,朗威斯認為她罪有應得,考克松大媽覺著她是訐奸會絕好的主角,“彼得手指”老板娘坦言,拿這樣的風流事搞訐奸會“是世界上最開心的事”[6]323。總而言之,生活在卡斯特橋市最底層的人都不想辜負了露塞塔和亨察德的這段孽海情天,不愿錯過這個絕佳的機會,打算借此機會“好好樂一陣子”[6]324。訐奸游行除了給民眾提供了酣暢發泄、娛樂狂歡的機會外,還為他們搭建了挑戰權貴的最佳平臺,作者指出這不只是一場開心的玩笑,而是“一頓報復”[6]333,是一場酣暢淋漓的報復。搞臭露塞塔也就搞臭了她的丈夫法夫瑞,一個“當了市長又成了有錢人,一心想著男女之事,而且野心勃勃”[6]332的人,一個一當官就變了臉的人,訐奸游行使露塞塔癲癇病發作,流產死亡,為伊麗莎白和法夫瑞的結合創造了似乎合理的條件,而亨察德的命運更是雪上加霜,江河日下。
值得注意的是,訐奸游行恰好定在皇室貴胄前來訪問的當天,旨在趁卡斯特橋的頭面人物們興致正濃的時候,以訐奸狂歡的形式“給皇室的訪問收場”[6]333,讓權力萎縮,斯文掃地。“給那些身居顯位的人開開玩笑,讓他們丟丑,對于輾轉于他們腳下的人來說,是一種至高無上、淋漓痛快的享受”[6]372。這是一場以趙普為代表的底層民眾向以法夫瑞、露塞塔,甚至王室顯貴為代表的上層發起的沒有流血的戰爭,也是最低等的彼得手指向最高級的王徽旅館發起的挑戰,同時也是對亨察德這位昔日權貴的歷史清算,它以下層人物對上層人物的戲謔脫冕為娛樂目的,表達了狂歡式顛覆等級、主張平等的世界感受。卡斯特橋訐奸游行反映了狂歡化的精神內核,它是社會底層民眾向上層社會發起的挑戰,是底層民眾為昭示其存在而發出的強音。另外,從某種意義上透視了以趙普、賣粥婦和“彼得手指”老板娘為代表的社會群體的仇富、仇權、仇美的心理,暴露出卡斯特橋尖銳的階級矛盾和復雜的社會問題。狂歡理論與酒神理論均肇源于酒神精神,但它們屬于兩個概念,酒神理論重在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表露,狂歡化則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它是從官方與民間、主流與邊緣、宗教與世俗相對的角度提出的,是西方二元對立文化的集中反映,表現出鮮明的民間政治訴求。
二、物品反用與逆向原則
物品反用是《卡斯特橋市長》狂歡化書寫的又一個表現形式。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介紹了反用日常物品以顛覆常規、消解成章從而暫時擺脫制約和束縛的一些常見的狂歡形式,例如“反穿衣服,褲子套到頭上,器具當頭飾,家庭炊具當作武器,如此,等等。這是狂歡式反常規反通例的插科打諢范疇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是脫離了自己常規的生活”[1]165。訐奸游行中被懲罰的男女雙方的模型背對驢頭,面對驢尾,游行者通常敲擊破盆舊壺、盤子或鏟子,吹口哨或牛角號,搖撥浪鼓,狂叫怒吼,不時伴有色情言語,在“粗糙音樂”所營造的歡鬧氣氛中,在一片詼諧滿足的笑聲中,參與民眾以半娛樂的形式對目標人物進行戲謔降格。“背對驢頭,面對驢尾”表現了對常規的顛覆,“敲盆擊鍋”等形式符合狂歡式物品反用的原則,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在缺乏正統器具的現實條件下常常會就地取材,用身邊的日常用品來代替高雅正統的器物,常見的有以敲擊鍋盆、碗筷來代替高雅樂器,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濃厚的解構正統、顛覆高雅、消解主流的意識。卡斯特橋的訐奸游行中,被懲罰的亨察德和露塞塔的模型背對驢頭,面對驢尾,“屠刀、鉗子、鈴鼓、小型提琴、臨時拼湊單弦或雙弦琴、粗制濫造的笛子、蛇形管、羊角喇叭以及有史以來各式各樣的樂器的喧嘩鼓噪”[6]348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曲粗野的大型民間交響樂,這種原始粗獷的民間審美顛覆了長期以來在歐洲占統治地位的“高貴的單純與靜穆的偉大”這一高雅審美理想。物品反用反映了狂歡化逆向觀世界、顛倒看人生的思想原則。
三、三類人物與面具功能
騙子、小丑、傻瓜是狂歡化文學營造狂歡氛圍不可或缺的三種特殊藝術形象,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扮演開心國王、王后的角色,三類人物是中世紀社會底層與正統文學相伴而生的諷刺性和諷刺模擬性民間創作和半民間創作中出現的,對后來歐洲小說發展產生了重要意義的三個具有各自標志性形象的人物。三類人物擁有自己“特殊的世界、特殊的時空體”[7]354,在小說中他們憑借特殊的面具功能揭露和戳穿人際關系中的虛偽和謊言,從而幫助小說家表達本不可以表達或難以表達的個人觀點和態度。他們是狂歡化文學的典型人物形象,作為被主流社會所鄙視的邊緣人物,他們以鮮明而獨特的、被官方正統文化所不齒的形象與官方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形象間形成對抗,通過顛覆正統文化所欣賞的理想形象戲謔正統人物達到娛樂和狂歡的目的,以此暫時滿足民眾的精神需求。巴赫金指出,在滑稽劇和諷刺模擬的系列作品里,三類人物擔負著反惡劣常規和揭穿人們關系中的謊言的任務,他們與那些僵化的制度和謊言相抗爭的力量“是騙子清醒、風趣而狡黠的頭腦,是小丑諷刺模擬式的嘲弄,是傻瓜心底忠厚的不解。對付彌天大謊的,是騙子風趣的小騙局;對付利己主義的假造和偽善的,是傻瓜并無私心的天真和正常的不理解;對付一切陋習和虛偽的,是小丑進行揭露的綜合形式”[7]351-352。三類人物在小說中“通過特殊的途徑恢復了文學與民眾廣場之間被割斷了的聯系”[7]354。
《卡斯特橋市長》中哈代成功塑造了騙子賣粥婦、小丑古斯塔夫和傻子阿貝·衛特狂歡化三類人物藝術形象,他們在文本中充分發揮了道具功能和情節過渡上的潤滑作用。巴赫金指出,“小丑行為”、“扭扭捏捏”、“裝瘋賣傻”、“怪癖行為”都屬于三類人物典型的行為表現。治安警察斯塔伯德像《還鄉》中的老闞特和蘇珊·南色一樣扮演了小丑角色,他形象猥瑣,性格懦弱,行為古怪,亨察德指責他說話羅嗦像個女人,賣粥婦罵他“老蘿卜頭”、“該死的傻瓜蛋”、“狗娘養的”,在庭審現場他對賣粥婦的指控繼而跟她的公堂對簿使本該嚴肅的庭審顯得滑稽可笑,讓人忍俊不禁,增添了該場面的狂歡色彩,在訐奸游行當天因害怕被人發現他和搭檔把政府警棍塞到了水管內,躲在巷子里,不敢吱聲露面。身為警察的斯塔伯德猥瑣形象、庭審現場的丑態和面對訐奸游行時的萎縮逃避是對官方形象的降格顛覆。阿貝·衛特在小說中雖出場戲份不多,但具備了傻子的一些形象特征,他“溜肩膀”、“眨巴眼”,大凡受到一點點刺激,他的嘴就會“微微張開,好像沒有下巴來支撐似的”[6]117,露出一副十足出神的傻相,大家都叫他可憐的阿貝。他自稱天生的笨腦瓜,一念禱告腦瓜就像死木疙瘩,這種表述無疑是對上帝的褻瀆和對宗教的解構;他行為滑稽怪誕,睡覺總過頭,上班總遲到,為了能按時起床跟上早班,他在腳趾上栓一根繩子,繩頭放在窗戶外,靠伙伴拽繩子來叫醒他,特別是受到亨察德的懲罰,大清早只穿褲頭狼狽跑過街道的情景更是一出典型的滑稽鬧劇,與正統文化形成了對話,以此來消解高雅文化,因此,他也隸屬于三類人物,是類似于《還鄉》中的克銳、《遠離塵囂》中普格拉斯和《綠蔭下》中的里福的“鄉村傻瓜”[8]。三類人物在小說中雖然只是道具人物或福斯特所謂的扁形人物,但他們與主人公的命運存在密切關系,騙子賣粥婦既是亨察德悲劇的始作俑者,又是重要推手,傻瓜阿貝·衛特陪伴亨察德走過了人生的最后歷程。
賣粥婦以女騙子形象出現在卡斯特橋的文本狂歡中,她機智詭異,圓滑狡黠,言語粗俗,喜歡自吹自擂,說她見多識廣閱歷豐富,“懂得怎么跟這地方上最有錢講究吃喝的大肚子打交道”[6]26,知道牧師、花花公子、城里人和鄉下人等各色人物的口味,發誓詛咒、吹噓謾罵、油嘴滑舌是典型的廣場語言形式。她無視官方禁令偷售私酒,不顧宗教戒律公然在教堂邊上撒尿,并以污言穢語辱罵政府警察。她行為不軌,累教不改,哈代說她出庭的次數比審問她的法官還要多得多,在法庭上她當眾指責法官亨察德并暴露了他的賣妻隱私,把他從法官的高位一下拽入了罪犯的深淵,實現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戲劇性逆轉,完成了狂歡式“加冕”與“脫冕”的瞬間變化,使嚴肅的庭審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可笑的狂歡鬧劇,法庭鬧劇使亨察德顏面掃盡,社會地位墜入低谷。在某種意義上,賣粥婦就是亨察德悲劇的制造者和有力推手,亨察德的一生命運都與這個“臉上斑斑點點”、全身像“油水里浸泡過一樣”[6]245-246的、形象滑稽、行為放蕩的女騙子有關。在現實生活中,三類人物被主流文化所不齒,屬于邊緣化的人物,但狂歡文學中他們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行動往往是推動故事情節變化和主人公命運逆轉的關鍵因素,賣粥婦偷售烈酒致使亨察德賣妻以及在法庭上揭發他的丑聞這兩個舉動構成了亨察德悲劇的關鍵環節。因此,賣粥婦這個現實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狂歡文本中卻轉化成了操縱主人公命運的“大人物”,體現了狂歡化的逆向原則。總之,女騙子賣粥婦從以下三個層面實現了對官方、宗教和權威的脫冕,“偷售私酒”顛覆官方制度,“教堂邊撒尿”解構宗教,“戳穿法官隱私”消解權威,充分發揮了三類人物在狂歡文學中的面具功能。她的行為是對維多利亞婦道的挑戰,她的在場是對英格蘭淑女形象的顛覆。
狂歡化是哈代“性格與環境小說”中比較常見的藝術風格,富含狂歡色彩的《卡斯特橋市長》堪稱其中之最。小說中作者書寫了賣妻、酒宴、庭審和訐奸四個狂歡廣場并借助三類人物的特殊文學功能通過對主要人物進行反復脫冕與加冕的狂歡化藝術手法展示了主人公亨察德起伏跌宕的悲劇人生,深刻揭示了人生多變和命運無常的人生哲理。狂歡化不僅是表現作者人生觀的藝術途徑,更是詮釋主人公命運沉浮的敘事手段,亨察德就是在一次次狂歡中走向沒落,因此,《卡斯特橋市長》也是亨察德的命運狂歡曲。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詩學與訪談[M].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2]夏忠憲.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3]Hardy,F. E. Life of Thomas Hardy[M].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7:134-135.
[4]Briggs, Katharine. British Folk-Tales and Legend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289-290.
[5]Hardy, Thomas. Thomas Hardy’s ‘Facts’ Notebook[M], ed. William Greenslade. Aldershot: Ashgate, 2004:175.
[6]哈代.卡斯特橋市長[M].張玲,張揚,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M].白春仁,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8]Sutherland, John. So You Think You Know Thomas Hard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82.
編輯:魯彥琪
On the Carnival Art in Hardy’sTheMayorofCasterbridge
CHEN Zhe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Xining Qinghai 810007,China)
InTheMayorofCasterbridge, Hardy describes four square carnivals, sale of wife, banquet, trial in court and Skimmington, which serve as the big turns in the capricious life of Henchard, the protagonist, and creates a heavy carnival atmosphere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Three Funny Characters in carnival literature. Carnivalesque is both the means to demonstrate the writer’s life view and the narrative way to unfold the hero’s tragic life.
carnival art; square carnival; degrading and upgrading; opposite usage; Three Funny Characters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17
2016-12-30
陳珍(1967-),男,青海湟中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I106.4
A
1672-0539(2017)05-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