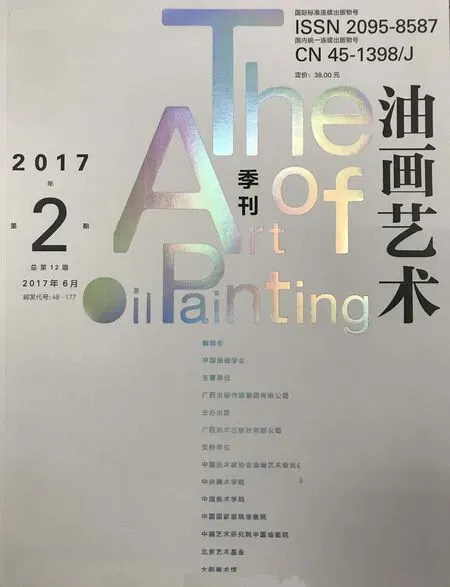西南油畫與當代油畫的源流與現狀
吳永強
【提要】新潮美術興起,西南油畫先后經歷了云南“新具象”與生命之流、川渝“新生代”與“新傷痕”、都市經驗與全球化、“新卡通一代”與圖像轉換等階段,實現了從現代藝術到當代藝術的轉型。如今,在市場支配藝術和藝術家集群化的語境下,西南油畫進入了一個多元而迷茫的時代。
1979一1984年,以四川美術學院學生畫家群為主體的四川畫派 ,以“傷痕美術”和“鄉土繪畫”寫下了西南油畫史上的經典一頁。從知青題材的“傷痕”作品,到羅中立的《父親》,四川畫派又陸續擺下了鄉土繪畫的盛宴,遂令西南內外,跟風者眾。從1979年的“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全國美展”、1981年的“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到1982年和1984年的兩次四川美院師生進京作品展,西南油畫不斷以自然主義的寫實風格和“小、苦、舊”的題材形象收獲贊譽。然而變化總在盛景之后,1984年第六屆全國美展之后,隨著新潮美術的興起,西南油畫隨四川畫派一道走向沉寂。不過正是在沉寂之中,新的種子開始發芽。
一、云南“新具象”與生命之流
西南油畫的新因素最早出現于云南“新具象”群體。1985年,云南畫家張曉剛、毛旭輝、潘德海聯合上海畫家侯文怡、張隆(昆明籍)、徐侃先后在上海、南京兩地舉辦展覽,取名為“新具象”。隨后,他們吸收西南三省成員,發起組織了“西南藝術研究群體”,形成一場“新具象”運動。按照毛旭輝的解釋,所謂“新具象”,就是“心靈的具象,靈魂的具象” ,他們借此表達對自然主義、矯飾主義的反對和對生命直覺的推崇。“新具象”成員也曾追隨過鄉土題材,如張曉剛的《天上的云》《暴雨將至》,葉永青的《牧羊村的撒尼姐妹》,毛旭輝的《圭山組畫》等,均取材于西南邊遠山村,不過這些作品并未屈從于鄉土自然主義,而是借鑒了早期現代派的語言風格,因為作者的關注點并不在鄉土題材本身,而在于傳達內心情緒和追求形式上的現代感。在這方面,周春芽也可算一個例子,其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藏族新一代》《剪羊毛》,同樣用鄉土題材承載了一種表現性意趣和有現代感的形式構成。他們與1980年出現的重慶“野草畫會”異曲同工,在西南油畫界埋下了現代性的種子。
“新具象”的出現,使這顆種子始得發芽。“新具象”成員的作品不僅告別了鄉土寫實模式,也與當時北方的理性繪畫相對應,成為“85美術新潮”生命之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稍后出現的昆明“南蠻子”群體、貴陽“原始風”、成都“紅黃藍畫會”以及四川美院新一代學生畫家的創作中,我們都能觀察到這種流向,那就是借鑒現代形式來表達直覺感悟并強調原始生命體驗。當時,高名潞曾撰文討論四川美院81級畢業生的油畫作品,通過將其與該校77級作品和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同年級作品比較,文章指出,再現距離和理性,重視形式風格和表現 ,是新一代四川美院油畫創作的特點。其后,牟群在一篇評價1986年四川美院第二屆“學生自選作品展”的文章中,將這一批學生稱為“第二代四川群體”,認為他們“以形式崇拜和自由追求為己任”。 兩篇文章都道出了一個事實,即年輕一代的西南油畫家正在與過去作別。其實,這種情況也發生在上一代畫家身上。例如,毛旭輝、張曉剛、葉永青、周春芽等,也從過去借鑒印象派、后印象派轉向了對表現主義、原始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吸收。
雖然提倡主觀表現,可是在“85美術新潮”時期,許多西南油畫家仍然保持了鄉土溫情,他們的作品明顯地帶有地域色彩。“南蠻子”宣稱“以西南的文化的蠻風來復蘇沉睡的邊疆冷土” ,貴州畫家以現代派形式來釋放山地文化的野性,四川美院青年畫家如龐茂琨、朱小禾、張杰、陳衛閩、翁凱旋、魯邦林、任小林、李強、閻彥、羅發輝、楊述等,也常在筆端流露出對鄉土的纏綿。這或許可證明西南油畫仍未斬斷鄉土繪畫的文脈。不過,恰好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它們與矯飾主義鄉土繪畫的區別,后者是跟風和模仿,前者來自心靈的實誠。在他們的畫面中,再也見不到矯飾化的鄉土自然主義和“小、苦、舊”形象模式,而是形式多樣,充滿個性,富有現代感。即使采取寫實手法,也有作者獨特的現代性追求。
但是,在提倡觀念更新的歷史氛圍中,鄉土意識卻受到重新審視。德國藝術史學家貝爾廷曾從當代藝術與全球文化身份的角度區分了“世界藝術”和“全球藝術”的概念,照此區分,“世界藝術”屬于地域性藝術,“全球藝術”才是表征多元文化平等的當代藝術 。1986年11月,“云南油畫新作展”開展期間舉辦了云南油畫討論會,會上,毛旭輝提出要“更新繪畫的區域性概念” ,主張把區域性放到大時代的復雜體系中,自然而非硬性地呈現區域性特征。聯想到貝爾廷的觀點,我們覺得,他似乎已經本能地趨近了“全球藝術”觀念。
二、川渝“新生代”與“新傷痕”
川渝“新生代”油畫以對都市經驗的傳達,與生命流繪畫拉開了距離。但同時,又以對藝術家個體生存經驗的專注而與北方“新生代”油畫發生了呼應,因此與后者一道,共同反映出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油畫由集體主義向個體經驗轉化的趨勢。
北方“新生代”油畫以方力鈞、岳敏君等的“潑皮藝術”(或稱“玩世現實主義”)為內容,它將起源于歷史轉折的宏大敘事隱藏于個體生存圖像,而川渝“新生代”油畫只是對純個體經驗的傳達。后者以心理敘事的方式展開,具有個人化、私密化和自戀性特征,并著意于暴露“青春殘酷”“肉身焦慮”和對傷害的迷戀,而不論它們采取卡通、艷俗、表現還是模糊化的圖像形式。正是在這個理由上,王林將其稱為“新傷痕”。其焦慮感,來源于面對都市異化的無所適從;其對傷害的迷戀,表征了個人在物化現實中的沉淪與掙扎。
這樣,川渝“新生代”油畫就不僅在共時性層面上與北方“新生代”油畫拉開了距離,也在歷時性層面上與“85美術新潮”的集體主義、英雄情結和宏大敘事漸行漸遠。后者在“北方藝術群體”所追求的崇高和“理性”、浙江“85新空間”所表現的冷漠感中得到了具體呈現。在川渝“新生代”油畫中,我們再也見不到理性繪畫所追求的“靜力學效果”和“靜呆美”,而只見到異質的圖像、陌生的情境,傷感的氣質和莫名的哀傷,從這個質調上看,它倒似乎顯得與本土生命流繪畫存在血緣關系。
三、都市經驗與全球化
川渝“新生代”藝術足以成為一個標志,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西南油畫的關注點從鄉土題材轉向了城市題材。盡管仍然有以羅中立、陳衛閩、陳安健、陳樹中等為代表的西南畫家以鄉土題材作畫,但他們也不再遵循過去鄉土繪畫的邏輯,而是基于對都市生存和現代化的反思,致力于建構一種“新鄉土”風格。而那些直接針對城市經驗和都市人格進行創作的畫家,更是以其作品為90年代中期中國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留下了視覺證據。必須提到,西南畫家所表現的城市經驗,并不僅僅以“新傷痕”形式出現,而是采取了多元的角度,形成了多樣的圖式,在四川美院畫家中,鐘飆、龍全、俸正杰、何森、張小濤、翁凱旋、王大軍、楊勁松、劉芯濤等人的作品如此,在貴陽畫家中,董重、蒲菱、李革等人的作品也是如此。這在1997年由王林策劃,輾轉重慶、成都、昆明三地的“都市人格”系列展,以及同年由管郁達在貴陽策劃的“都市人格1997——重返烏托邦”展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
這種轉型同樣發生在成名更早的藝術家中間。例如,20世紀90年代,張曉剛創作了《手記》系列、《天安門》系列、《大家庭》系列,葉永青創作了《大招貼》系列,毛旭輝創作了《家長》系列、《剪刀》系列,周春芽創作了《太湖石》、《綠狗》系列,這些作品不但以各自的方式反照了作者的都市經驗,而且無不以鮮明的本土化和個體化特征,宣告了對現代主義的放棄。但就其本土性文化特質而言,它們卻不是依靠執著于地域性文化經驗取得的,而是在更高的文化層面上,圍繞中國現實經驗或歷史文化,依靠個體性觀照而取得的。即便是圍繞大巴山題材進行創作的羅中立,也不再以俯瞰的姿態發表對農民的同情,而是以平視的角度,呈現農村生活狀態,創造了關于中國農村的人文圖像。在文化上,它們反映的是中國經驗而不是地域性經驗。這種對本土性立場的關注,凸顯出中國文化的身份問題,有利于使當代藝術成為一種手段,以幫助中國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中展開與世界的平等對話。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地區,同樣生活著一些候鳥型藝術家,由于經常穿梭于國內外,對他們而言,文化身份的問題更顯得迫切而緊要。在這些畫家中,重慶的何工可謂一個典型。何工在創作中將本土立場融于對個體立場的捍衛,表達了對后殖民文化和一切固有偏見的批判。他以與新表現主義精神共鳴的作品,披露了其在國際上行走的歷程,為西南油畫與國際當代藝術的近距離“接軌”,留下了一份生動的檔案。
四、“新卡通一代”與圖像轉換
21世紀以來,與市場化同步,中國當代藝術越來越陷入消費文化語境,藝術家需要面對流行文化、網絡傳媒、動漫游戲等信息時代和消費社會的景觀。在這種情況下,“新卡通一代”應運而生。我們知道,“卡通一代”是一種新生代藝術樣式,盡管發端于廣州,卻繁榮于北京和川渝,所以早就與西南油畫結下了緣分。忻海洲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陸續創作的《城市卡通人》系列,一度成為西南新生代油畫的身份圖式。而“新卡通一代”的代表人物,也以熊宇、高瑀、陳可、沈娜、熊莉鈞、李繼開、楊納等占據多數。忻海洲曾寫道:“人們在文明的游戲中被雕塑得卡通化了,我發現,我們都是城市卡通人。” 到了21世紀,當游戲、動漫、網絡、虛擬、“新新人類”不再僅僅是一些詞語,而成為人們尤其是青年人日常經驗中的現實時,“城市卡通人”以新的面貌還魂,成為西南油畫進入21世紀的一道絢麗景觀。
“新卡通一代”包含了“70后”和“80”后兩代人,而以“80后”為主。如果說作為“60后”新生代的“卡通一代”還在努力用卡通圖像來隱喻其個人對時代遭遇的總體感知,試圖為自己成年后才陸續趕上的消費文化和網絡文化發明易于識別的符號,那么,“新卡通一代”則更傾向于用游戲、動漫圖像來指向自我,指向他們在消費社會和網絡文化中早已習慣成自然的生活。相比于上幾代人而言,這種生活波瀾不驚,就好像隔絕了歷史,處于時間的空白地帶。不過,作為藝術從業者,藝術界的走向對他們而言并不是一片空白,這些年輕的西南藝術家覺察到,背襯都市經驗的“艷俗藝術”“卡通一代”“青春殘酷”余緒未散,而新生代自傳體仍然是一種能夠生效的藝術生存途徑;而在一個碎片化的生活圖景中,也的確只有回到自我,心靈才能得到安放。所以,西南“新卡通一代”表面上附著于網絡時代的卡通藝術、果凍藝術等潮流樣式立身,內中卻縈繞著早前“新生代”式的自戀和多愁善感,這讓他們圍繞游戲、動漫形象和虛擬世界,為21世紀的西南油畫注入了新的具體性。
高瑀和陳可這兩位不同性別的畫家,也許能夠作為恰當的例子,幫助我們認識川渝“新卡通一代”油畫創作的特色。高瑀吸收日本動漫和村上隆、奈良美智等藝術家的影響,把在中國有“國寶”之稱的大熊貓打造成了一個符號化、內含傲慢、充滿顛覆性的卡通形象GG。有評論者猜想,GG的狀態和情感出自高瑀本人,帶有畫家自傳意味 。如果此說成立,那么就意味著卡通創作成了藝術家協調自我沖突、舒緩情感的一種手段。陳可把得自奈良美智的啟示,連同日韓卡通藝術的整體影響,悄悄置換為一種頗具女性細膩感的情境性敘事。其形象滌除了奈良美智筆下小女孩的那股邪氣,其畫面帶著淡淡的憂傷,私密、敏感,幽遠,充滿孩子氣,但又激起了人們窺視的欲望。如果我們可以把新卡通一代叫作“后新生代”,那么這兩個例子就寓言了“后新生代”西南畫家的一種創作取向,即既追求圖像轉換,又試圖顧影自憐,玩味私情。這種取向有川渝“新生代”的遺傳因子,又在傳遞過程中因與快速遭遇的消費社會和網絡時代發生碰撞,隨之散播開來,成為一種特質,不斷在“新卡通”、“小清新”藝術以及“手感秀”的西南“新新人類”繪畫中滲漏出來。
五、多元而迷茫的今天
如同國內普遍存在的情況一樣,除了集中于院校,跨越體制內外、久留或暫住北京、部落化生存和接受“文化產業”的介入,是西南地區畫家的基本生態。而部落化生存,是一個常在的現象,這說明,就大多數人而言,如今藝術是一個職業而不是愛好。成都的“藍頂”“濃園”“高地”,貴陽的“城市零件”,云南的“麗江工作室”以及一度火爆的昆明的“上河會館”“創庫”等,還有散布在這些城市和其他地方大大小小的藝術家村落或藝術聚集區,集中了大量創作油畫的藝術家。而且,伴著最近幾年藝術市場的低迷,客京滯留798、宋莊等地的西南畫家有逐漸回流的趨勢,目的地一般以成都為多,因此成都畫家的數量在西南三省城市中居于首位,也相對更為集中。
面對一種藝術進行式,我們實在無法一一點出畫家的名字,也無法對今日西南地區或其中任何一個城市的油畫創作狀態做出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例如,如果我們說貴州是野性的,那么一個溫和的畫家的作品就將給出反例;如果我們說云南是簡約的,那么一個云南畫家的復雜的構圖就將證明我們的說法;如果我們說成都是重手感的,那么僅靠挪用圖像就能得到一件作品的畫家就將令我們住嘴。在這個藝術都難以被定義的時代,還指望依靠一個籠統的敘事來指認一地藝術創作的真相,已經變得十分可疑,所以我們寧愿相信,藝術家創作的真正差異性只存在于個體之間。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回到一種現象學起點上,對西南油畫的今日狀況形容它是“多元化”的,雖然這個詞在許多時候幾乎等于無話可說。
不過,一些碎片化的觀感依然是可以說出來的。就拿我們最為熟悉的川渝兩地來說,有的畫家注重文化觀念的傳達,有的畫家注重個人情感的表現,有的畫家關注圖像轉向,有的畫家注重傳統體驗,有的畫家趨于外向的介入,有的畫家希望保持內向的純粹……但在這多聲部的合唱中,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一個旋律,似乎就是“溪山清遠”,猶記得這是2011年成都雙年展的主題詞之一。在創作上表現為用油畫、水墨或跨媒介手段來處理風景、靜物題材,或解構和轉換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山水、花鳥圖像。盡管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文化上的或觀念上的說辭來替這些做法辯護,但往往辯護的意義只存在于我們自己的文字之中。而且最近幾年,國內畫界興起的一股旅行作畫風潮也深深地影響了西南畫壇。油畫家們近到郊外,遠到異國他鄉,在原野間豎起畫架揮運畫筆。這當然能夠促進油畫這門藝術再次面對自然。我們或可說,在這種情況下,油畫便得以重返其活力始發的現場,并向圖像統治繪畫的權勢發出挑戰。不過,這股風潮也慢慢滋生出以寫生同化創作的現象,好像畫家只要帶上眼睛,具備一副手藝,便可接二連三地制造出作品,再也不必受思想、觀念、情感和想象力的折磨了。與此同時,寫生畫展被大量舉辦,寫生——的確只是寫生——之作填滿了大小展覽,它們編織出一道景觀,讓人誤以為,除了寫生,油畫家已經無事可做了。其結果是,油畫更深地放縱了對物性的沉湎和對社會現實的疏離,而與此同時,明明只是寫生,畫面上只要淌著顏料,留下屋漏痕,就會被指認成“當代藝術”……對比之下,我們就未免懷念起何工一類的藝術家了,因為我們在他通常是結合跨媒介材料的油畫作品中,感受到一種流放者的氣質,一種即使被邊緣化也不放棄“異爭”的姿態,這也許才是西南當代油畫值得追求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