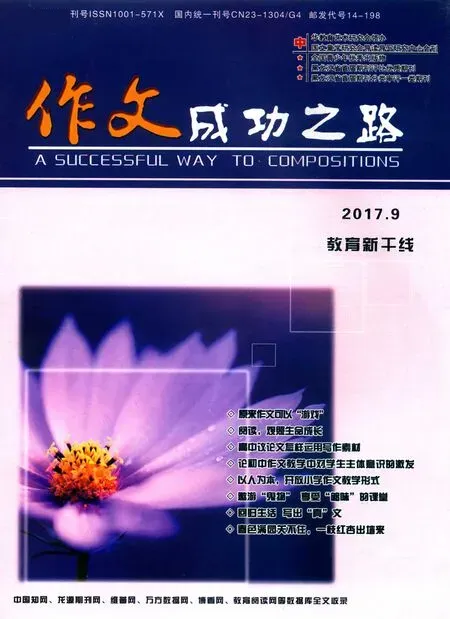總有那么一個地方
山東省青島市五十八中 馬澄瑤
總有那么一個地方
山東省青島市五十八中 馬澄瑤
陳方醒來,勉強支起身子,半倚在枕頭上,仿佛還沉浸在夢里。世界仍是入睡前的樣子,桌上還有半聽未喝完的葡萄汁,玻璃杯壁的缺口仍然顯眼,自己也還是一個即將大四畢業卻前路迷茫的男青年。可似乎又有什么不一樣了,夢里不可置信的真實感讓他難以思考。
在夢里,他去了加德滿都,一個他自小就心心念念的地方。走走停停,無意間拐進了一座寺廟,他虔誠地撫過一個個轉經筒,指尖的冰涼觸感是那樣真實。抬起頭,空中升起了一支支風馬,被風吹動著。他忽然想起了《壇經》記載的一個有趣的哲學對話:
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慧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雖然不免有唯心主義傾向,但他還是癡癡地望著迎風飄動的風馬,直到醒過來。
陳方揉揉頭發,強迫自己清醒,然后帶著書繼續去圖書館準備托福考試和工作簡歷。
一連幾夜,卻是相似的夢。終于,第五天又一次夢醒后,陳方下定了決心。
北緯二十七度,東經八十五度,加德滿都。
“還是來了。”陳方走出機場,無奈地自言自語,“希望不會辜負我從輔導員手指縫里擠出的假期。”
北部高大的喜馬拉雅山脈阻擋了南下的冬季風,溫柔地擁住了從印度洋吹來的海風,帶給加德滿都清新濕潤的每一天。天空是仿佛被冰凍過的藍,空氣里可以看到閃閃發光的塵埃,集市上充盈著水果和香料的氣息,還有成群結隊的僧侶。陳芳被裹挾在人群中,踉踉蹌蹌地向前走去,進了一座寺廟也不自知,意識到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正殿的后院。大片熱帶樹種安靜地生長著,使人呼吸的力度也漸漸輕了起來。不知過了多久,陳方回身,瞥見一個喇嘛摸樣的人站在身后,忙合十作揖。那人回禮,說了一句話,似乎是藏語。
“不好意思,我只會講漢語和英語。”陳方有些窘迫。
喇嘛雖聽不懂,但也溫和地笑笑,做了一個隨他走的手勢,便轉身走開了。
陳方躊躇了一會兒,追了上去。
很干凈的一間耳房,喇嘛給陳方倒了一杯茶,傳統的酥油茶。
經過熱心導游的翻譯,陳方才知道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覺得他有眼緣,便請他來房里小坐。大師還說自己有事先失陪了,請陳方飲完茶自便。
陳方小口抿了一點茶,打量起這個屋子。一張木桌子,用磚土搭起來的床,床邊有一個架子,架子上有本書。陳方走上前,小心地拿起它,看不懂的圖形和文字,應該是用藏語記錄的什么事。陳方舉著書,突然一陣困倦卷席全身。迅猛也來勢洶洶。
陳方做了一個夢。
晨曦照耀下的經殿煜煜生輝,繚繞而出的香霧更添幾分脫塵之氣。熙熙攘攘的教徒走進經殿誦經,經殿中央坐著一個年輕男人,著紅色的袍子袈裟,被眾人眾星捧月般環繞著閉幕誦經。隔著兩個軟墊跪坐著一個少女,有些圓潤的的臉龐上紅紅的,烏黑的發散在肩后,口中念念有詞。,驀然,中央位置的男人睫毛顫了顫,卻又很快歸于平靜。
那一天,驀然聽見你誦經中的真言。
畫面很快模糊,轉為經殿后院。
五顏六色的風馬在空中飄蕩,影子落在地上像活潑的水草。又是那個年輕的男人。他抖一抖紅袍,露出骨節分明的手,一點點轉動著經筒,慢慢地走到山路邊。然后跪下,匍匐在石路上,一步又一步,頭磕了一次又一次,滿面塵埃,又虔誠至極。
那一月,只為觸摸你的指尖。那一年,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畫面黑了下來,突然又燈火通明,是拉薩的街市。
這次年輕男人脫下了彰顯身份的紅袍袈裟,一襲粗麻布衣,游走在張燈結彩的街頭。手邊有一家酒館,不曾猶豫地撩起布簾,跨入酒家。木紋繁瑣的床邊,有他半明半暗的臉龐,有手里細細摩挲的酒杯,有望向布達拉宮迷惑的眼神。如果你走近,或許可以聽到他的低語:
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那一夜,我不是雪域最大的王,我是拉薩最美的情郎。
陳方醒了過來,腦袋浮浮沉沉,只依稀判斷出自己伏在那間耳房里的桌子上睡著了。他知道夢里的男人大概是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不可名狀的憐惜和無奈涌上心頭。他出神得想著,再抬眼喇嘛已經回來了。陳方忙作揖告辭,匆匆出了寺廟。
“人總要有信仰,無關宗教。我知道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夢了,但我卻真切的懷戀著它們。既然不可能在加德滿都或者西藏度過我的余生了,那么至少現在的生活要像點樣子。”回程的飛機上,陳方在擁擠的小桌板上寫下這段話,舒了舒眉頭。
高空的云有點薄有些卷,好像一條條風馬在自由地擺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