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一葉總關情
蔣儉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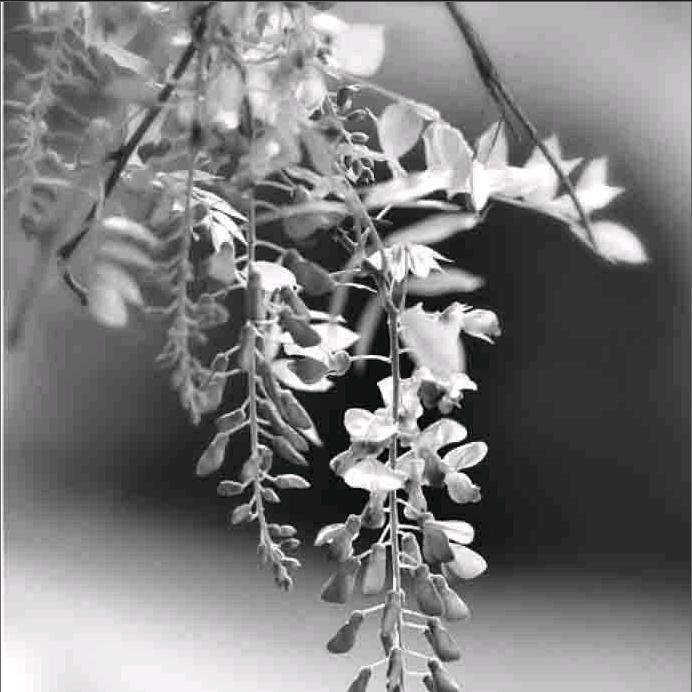
助學寄語
又是一年春來到,在明媚的陽光里,初初又和你相遇在《初中生世界》。
現在,初初想和你說一說本學期語文課第一單元的關鍵詞——詠物抒懷。它是文學創作中一種重要的表現手法,托意于物,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來表現抽象事物或思想感情。“一枝一葉總關情”,自然界的風花雪月都有其獨特的景致,這些景致流過心田,也就有了詩情與畫意。在作者筆下,這些被描摹、詠嘆的事物里,表達著他們的情思,寄寓著他們的愿望,流露著他們的人生態度,蘊含著生活的哲理。
本單元所選的四篇詠物抒懷散文均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經典之作,各有特色。它們有的直抒胸臆,淺顯易懂,如茅盾的《白楊禮贊》;有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甚至通篇使用象征,讀者也許不易把握文章的主旨,如郭沫若的《石榴》、宗璞的《紫藤蘿瀑布》、高爾基的《海燕》。
初初覺得,要讀好詠物抒懷的文章需抓住兩個點:一是關鍵點;一是相似點。
抓住關鍵點,即要把握好文章的重點,作者重點描摹的,也是讀者應該認真關注的。因此,我們要仔細揣摩和分析吟詠對象的形象特點。
抓住相似點,即要善于聯想與想象,分析寫作對象與所要表達的真實情感間的關聯處,體會作者所抒之情、所言之志。
當然,有時我們還要適當聯系寫作的背景。這里所說的背景,可以是社會背景,也可以是作者的生活背景(人生經歷),從而了解作者寫作的緣起。
最后,初初想說,經典的散文作品,是作者用自己的人生閱歷釀制的美酒,細細品,回味無窮。
延伸文本
《海燕》拓展閱讀——
黑蜜蜂
鮑爾吉·原野
黑蜜蜂無牽無掛,孤獨地飛在山野的灌木上方。一只肚子細長的黑蜜蜂在巖石的壁畫前飛旋,白音烏拉山上有許多壁畫——古代人用手指頭在石上畫的圖形符號。我覺得像是古埃及人來蒙古高原旅游時畫的。黑蜜蜂盯著壁畫看,壁畫上有一人牽著駱駝走的側影,白顏料畫在堅果色的黑石上。黑蜜蜂上下鑒賞,垂下肚子欲蜇白駱駝。“古代駱駝你也蜇啊?”我說它。黑蜜蜂抻直四片翅膀,像飛機那樣飛走了。
草原上有許多黑蜜蜂,長翅膀那種大黑螞蟻不算在內。盛夏時節,草地散發嗆人的香味,仿佛每一株草與野花都發情了。它們呼喊,氣味是它們的雙腳,跑遍天涯找對象。花開到泛濫時節,人在草原上行走沒法下腳,都是花,踩到哪朵也不好。花開成堆,分不清花瓣生在哪株花上。黑蜜蜂比黃蜜蜂手腳笨,在花朵上盤桓的時間長。我俯身看,把頭低到花的高度朝遠方看——花海有多么遼闊,簡直望不到邊啊,這就是蜜蜂的視域。蒙古人不吃蜜,像他們不吃魚、不吃馬肉狗肉、不吃植物的根一樣。沒有禁忌,他們只吃自己那一份,不泛吃。野蜜蜂的蜜夠自己吃了,還可以給花吃一些。蜜蜂是花的使者,它們穿著大馬褲的腿在花蕊里橫蹚,像赤腳踩葡萄的波爾多釀酒工人。晚上睡覺,蜜蜂的六足很香,它聞來聞去,沉醉睡去。蜜蜂是用腳吃飯的人,跟田徑運動員和拉黃包車的人一樣。
草原的晨風讓女人的頭巾向后飄揚,像漂在流水里。軋過青草的勒勒車,木輪子變為綠色。勒勒車高高的輪子兜著窄小的車廂,趕車的人躺在里面睡覺,憑駕車的老牛隨便走,隨便拉屎撒尿。黑蜜蜂落在趕車人的衣服上,用爪子搓他的衣領,隨勒勒車去遠行夏營地。月亮照白了夏營地的大河,河水反射顫顫的白光。半夜解手,河水白得更加耀眼,月亮像洋鐵皮一樣焊在水面。那時候,分不清星星和螢火蟲有什么區別,除非螢火蟲撲到臉上。星星在遠處,到了遠處,它躲到更遠處。蟲鳴在后半夜止歇,大地傳來一縷籟音,仿佛是什么聲的回聲,卻無源頭。這也許是星星和星星對話的余音,傳到地面已是多少光年前的事啦,語言變化,根本聽不懂。等咱們搞明白星星或外星人的話,他們傳過來的聲音又變了。
黑蜜蜂是昆蟲界的高加索人,它們身手矯健,在山地謀生。高加索人的黑胡子、黑鬈發活脫是山鷹的變種,黑眼睛里藏著另外一個世界的事情。他們剽悍地做一切事情,從擦皮靴到騎馬,都像一只鷹。黑蜜蜂并非被人涂了墨汁,也不是蜜蜂界的非裔人,它們是黑蝴蝶的姻親,蜜蜂里的山鷹。蜂子們,不必有黑黃相間的華麗肚子,不必以金色的絨毛裝飾手足。孤單的黑蜜蜂不需要這些,它在山野里閑逛,釀的蜜是蜜里的黑鉆石。
一位哈薩克阿肯唱道:
黑蜜蜂落在我的袖子上,袖子繡了一朵花。
黑蜜蜂落在我的領子上,領子繡了一朵花。
黑蜜蜂落在我的手指上,手指留下一滴蜜。
我吮吸這一滴黑蜜,娶來了白白的姑娘。
晨光在草原的石頭縫里尋找黑蜜蜂,人們在它睡覺的地方往往能找到白玉或墨玉。黑蜜蜂站在矢車菊上與風對峙,它金屬般的鳴聲來自銀子似的翅膀。圖瓦人說,黑蜜蜂的翅膀紋絡里寫著梵文詩篇,和《江格爾》里唱的一樣。
(選自2016年第2期《文學教育》,本刊有刪改)
鑒賞空間
《黑蜜蜂》的作者鮑爾吉·原野與歌手騰格爾、畫家朝戈被稱為當今中國文藝界的“草原三劍客”。鮑爾吉·原野來自草原,因此他的很多作品散發著濃濃的草原氣息,就如散文《黑蜜蜂》。
《黑蜜蜂》是一部充滿想象力的作品,它為讀者描繪了一個黑蜜蜂的生活世界,神奇而獨特。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這篇散文不僅是對黑蜜蜂的贊美,還是作者為蒙古人而作的贊歌。仔細讀一讀、找一找,你會發現開啟文本的密碼。
讀有所思
1. 作者筆下的黑蜜蜂有哪些特點?
2. “花開到泛濫時節,人在草原上行走沒法下腳,都是花,踩到哪朵也不好。”說說句中“泛濫”二字的表達效果。
《白楊禮贊》拓展閱讀——
山谷里的花
于振坤
早晨醒來,鳥啼樹間。我洗漱完,走出山村,直奔山谷。
山谷距山村五里路,但要翻過一個山頭,再走上一段彎彎的小路。
正是春末,晴朗的天。從山里吹過來的風,帶著青草和野花的氣味,輕輕地吹拂著我的面頰和胸襟,我心生愜意,腳底生風,一會兒工夫就到了山谷。
站在山谷的邊緣,看到山谷不深,雖有裸露的巖石,但沒有懸崖峭壁奇石異峰,也沒有雪浪翻卷飛瀑轟鳴。從谷底到谷頂,從眼前向縱深,綠茵茵是山谷的主旋律。那濃濃的綠、淡淡的綠,是樹,是草,是野花的莖和葉。它們高低起伏,隨著山谷而綿延。綠色的中間開著許多異樣的花,有白色的老鴉瓣、照山白,黃色的龍牙草、刺五加,紅或紫色的馬蘭花、益母草、錦地羅……
這些花,五顏六色,千姿百態,散落在山谷里,陽光一照,仿佛千萬顆星星在眼前灼灼閃耀。微風一吹,它們像在跳舞,又像千萬張稚嫩的小臉兒在向我微笑……
我陶醉于山谷里,欣賞著這里的每一朵花。
當走到山谷的底部,谷底的涓涓細流淙淙作響,浸濕了我的鞋子,我竟全然不知——我被小溪邊上的一棵蒲公英吸引住了。它開了許多朵金黃色的花,綠油油的葉子,直挺挺的花莖,堅韌而蒼勁。它的根像藤蔓深埋在小溪邊的巖縫里。
這是一朵最為普通、最為常見的花。但是,這朵花和我以前見過的有所不同,以前見過的是趴在地上的,可這朵花是向上的。也許,是因為它長在小溪邊能吸取足夠的營養又沒有人來踐踏。它那張開的小花瓣微微顫動,好像在和我說話:歡迎你老朋友!是啊,相信我們這些“50后”的人,幾乎所有人的童年都曾與它邂逅過。它生長在路邊、荒野、房前、屋后。那白白的小絨球,是它的種子。記得小時候,我常將那小絨球放在嘴邊使勁地吹,每次吹,那小絨球都會四處分散,像天空中的降落傘。
如今,在城里已經很難再見到它了——到處是柏油馬路、水泥地面、高樓大廈……一想到這些,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我更愛這山谷里的花了。
也許,你會覺得這山谷里的花,沒有河南洛陽的牡丹花花大色艷雍容華貴,也沒有福建漳州的水仙花葉姿秀美花香濃郁,更沒有浙江金華的山茶花花姿綽約端莊高雅。
是的,我不否認你的感覺。它們是名花,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
但是,這山谷里的花卻是純天然、純野生的啊!它們不羨慕名花,不卑賤自己,按照自己的天性活得非常自然;它們遠離城區,遠離人群,習慣于無人欣賞,活得自在且清閑。
我贊賞它們。
人,有許多種活法。
如何選擇?
也許,你選擇像這山谷里的“花”一樣,會生活得不累,且富有情趣。
“智慧的人,永遠不會活在別人的嘴里,或者眼里。”
我站在山谷里,久久不愿離去。忽然覺得這山谷之大、野花之多,而我之渺小。我被花包圍,仿佛是花中的一員,融入了大自然……
(選自2016年第7期《散文百家》)
鑒賞空間
讀完文章后,你有沒有發現本文與《白楊禮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通過交代花生長的環境來突顯花的美麗自然的天性;又如通過寫雍容華貴的牡丹、葉姿秀美花香濃郁的水仙、花姿綽約端莊高雅的山茶,來襯托山谷野花的清閑自在。作者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直抒胸臆地表達對“山谷里的花”的贊賞,亦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生活態度。
讀有所思
1. 請從修辭的角度賞析下面這句話。
微風一吹,它們像在跳舞,又像千萬張稚嫩的小臉兒在向我微笑……
2. “智慧的人,永遠不會活在別人的嘴里,或者眼里。”你怎么理解這句話?
《石榴》拓展閱讀——
溫暖的葦花
丁立梅
蘆葦的花,最不像花,像是用輕軟的絲絮絮出來的。
出城,逢到有河的地方、有溝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不是一棵一棵單獨生長,要長,就是一片,一群。擠擠挨挨,摩肩接踵,親親密密。它們是最講團結精神的,這一點,比人強。人有時喜歡離群索居,喜歡獨立特行。所以,人容易孤獨,而蘆葦不。
風吹,滿天地的葦花,齊齊的,朝著一個方向致意。它讓我想起“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那樣的詩句來,那是極具蒼茫寥廓、極具凄冷迷離的景象。可是,我眼前的葦花不,一點也不,我看到的,是一團一團的溫暖。冬陽下,它像極慈眉善目的老婦人的臉,人世迢迢,歷盡滄桑,終歸平淡與平靜。
我一步一步下到河沿,攀了兩枝最茂盛的葦花。一旁的農人經過,看我一眼,笑笑。走不遠,復又回過頭來看我一眼,笑笑。他一定好笑我的行為,采這個做什么呢!
我是要把它帶回家的。家里有花瓶,靛青色的,上面拓印著一片一片肥碩的葉。這是我的一個學生,在江西讀書,不遠千里給我捎回來的。花瓶太大,沒有花能配它。插兩枝葦花進去,卻剛剛好。葦花伸出長長的脖頸,在我的花瓶上方笑,綿軟、溫柔,一團和氣。
來我家的人看到,驚奇一聲,這不是蘆葦嗎!
當然是。尋常的物,換了一個環境,就顯出不尋常來。有一句話講,環境造就人。其實,環境也造就物的。
我的老父親看到,卻吃吃笑出聲來。他說,丫頭,虧你想得出。我知道父親笑什么,老家遍地蘆葦,沒人拿它當寶貝的。
冬天,農閑。家家要做的事,就是去溝邊河邊割蘆葦,運回家當柴火。一叢一叢的蘆葦倒下,葦花受了驚嚇,撲撲撲,四下飛散,飛絮滿天。農人的頭上身上,都沾滿葦花。他們把它當塵一樣的,隨便拍拍,輕描淡寫。彎腰,卻在小鳥用葦花壘成的窩里,撿到幾只還溫熱著的鳥蛋。他們很高興地把鳥蛋揣進懷里,哪里顧得上半空中,鳥的凄凄鳴叫呢。他們的眼前,晃過家里幾個孩子的小臉。請原諒,貧窮年代,那是孩子的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