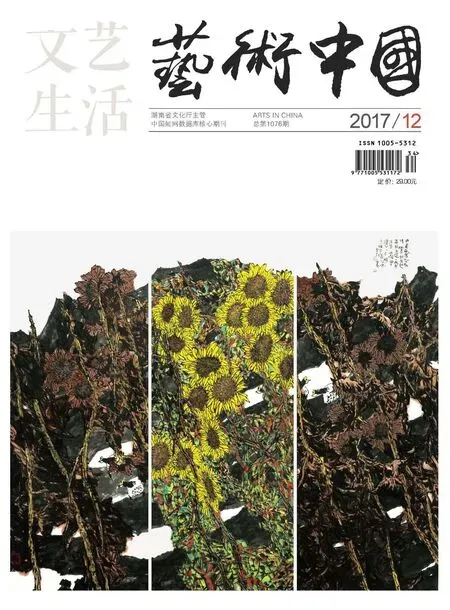意象油畫中的表現主義
◆余尚紅(江蘇宜興廣播電視臺)
油畫藝術作為“舶來品”來到中國已經一個多世紀。上個世紀初,一批留學生抱著藝術救國的思想,踏上了去歐洲、日本的“取經”之路。學成歸國后,這批精英在新建立的美術院校內傳授油畫藝術。從這一刻起,中國的油畫藝術就一直在東西方的雙重語境下生存。近十年來,中國油畫家經過了長達半個世紀探索油畫本土化和民族化之路,提出了“意象油畫”的說法。
這一說法的潛在對象是“寫實油畫”,現在許多文本在使用“意象油畫”一詞時主要有以下三個層面的意思:第一,意象油畫是油畫藝術在中國民族化、本土化的結果,是油畫在中國生根的象征;第二,意象油畫是油畫藝術本體語言在中國延展的體現,超越了寫實繪畫“乃工”“乃匠”的評價,接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內核和審美趣味,這種看法顯然借鑒了傳統文人畫的說法;第三,“意象油畫”主要是指中國江浙滬地區提倡“中西結合”的地域性畫派,其代表人物有劉海粟、林風眠、吳冠中、蘇天賜等等。
“意象”用來表達油畫本土化特征的時候,會碰到很多想當然的解釋。因為這是一個中國文藝批評中的老詞,其概念史可以追述到《老子》這個中國最古老的思想文獻:“圣人立象以盡意”。這個“象”基本上可以理解為圖形、文字。而“意象”二字合用并且廣泛通行是在唐以后,主要出現在“詩話”中,如“意象欲生,造化亦奇”;在宋人筆記中,意象的意思又衍生為表情儀態之意。基本上,用現在的話說,在文學批評中的意象,是指主觀意識對客觀世界的觀照后形成的“心像”。意向的模糊性的詩意被用來對抗寫實繪畫中許多嚴格的戒律。在畫家這里,意象油畫其實更加側重的是一種區別于古典油畫技法的寫意手法,以及中國式的審美、文化傾向、心理表現等等。但從實際看,這種寫意手法和中國畫的寫意有本質的區別,它仍然受油畫語言的語法約束。中國寫意畫,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畫的材料和創作模式共同決定的。中國畫的發展和西方現代藝術不同,前者講的是繼承,后者講的是創新。
意象油畫的技法,一面是從蘇派繪畫語言中發展而來,一面吸取了歐洲的現代繪畫中的表現性因素。這里經常容易被混淆的兩個概念,就是“表現性繪畫”和“表現主義繪畫”。后者是現代繪畫史上的一個流派。當然,對中國的當代藝術,尤其是架上繪畫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表現主義”一詞首先是由一些德國畫家提出來的,他們盡管分屬于不同的繪畫團體,為了共同探索不同于過去遵從自然的繪畫可能性形成的一個繪畫流派;而“表現性繪畫”則是一個更加寬泛的概念,包括了法國的野獸派和直到后來的抽象表現主義,梵高、蒙克、康定斯基都在其列,他們著重表現的是心理因素而不是自然,用新的技巧和新的象征、不協調的色彩和扭曲的形式表現無形的世界。
藝術史家沃林格爾,以“移情論”研究了原始藝術和哥特藝術中的表現。這兩個時期的藝術的最大特征就是“表現主義”,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表現”。它不同于“再現”傳統,不以模仿自然為目的,而是通過形式表達直接指向精神性。沃林格爾的研究影響了現代繪畫的創作。當時的留學歐洲的畫家多少直接或者間接地受此觀念的影響。因此,有人將表現主義繪畫稱作西方的寫意繪畫,以此來比附論證中國油畫繪畫從寫實走向寫意的必然性,顯然是對“表現主義”的一種誤讀。除此之外,如果從單純的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意象油畫和表現主義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發現二者之間并沒有任何歷史性的事實關聯。換句話說,對中國油畫的意象表現風格并非直接來自表現主義的影響,更多的是從蘇派繪畫的教育體系中生長出來的。
后來的繪畫理論研究更加明確了現代繪畫中的表現性。在描述西方藝術的發展史從古典轉向現代的特征時,貢布里希引入了兩個重要的概念:“再現”與“表現”。在《藝術與錯覺》中貢布里希寫到:“藝術不僅是打開外部世界的鑰匙,也提供打開心靈的鑰匙,正是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使得藝術家的興趣發生了根本變化。”沿著貢布里希畫家將從外部世界轉向心靈的思路,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印象派畫家關注的是光線、色彩如何以“客觀”的方式呈現在畫面上——畫家是自然的“記錄者”,畫面是自然的“鏡像”;表現主義畫家們關注的是,色彩和筆觸如何以符合藝術家心靈情感的方式組合,繪畫的行為本身比再現繪畫的對象更有意義。兩者都打破了寫實繪畫以再現對象為手段,而將繪畫語言直接作為表現的對象。這和中國的傳統繪畫中的寫意的確不謀而合。中國畫的題材和畫法大多比較固定,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圖式,藝術家在圖式的基礎之上發揮。筆墨材質和情感的表現成為藝術家創作時的關注點。而中國老一輩的油畫家像吳冠中、蘇天賜先生,用油畫來表現煙雨江南,在氣質上和中國傳統水墨有所繼承。
“意象”一詞比較貼合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而且比較集中地表達了中國詩性文化特質,意象和表現就如共生的兩姐妹。“意象”作為一個模糊的介質,溝通著藝術家的內心情感和畫面上的色彩和造型。中國油畫走向意象表現,某種程度上也是向中國寫意的視覺藝術傳統的回歸,是一次“本土化”進程。表現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寫意繪畫之間具有某種共性,至少在視覺習慣上如此。劉海粟先生曾將梵高和石濤的藝術作比較,這種生硬的比較盡管不是在嚴格藝術史的框架下進行的,但仍然解釋了表現主義繪畫和中國傳統繪畫在畫面上的某種關聯。佛教傳入中國的情況與此相似,從兩漢之際開始,歷經一次次的傳法與漢文化碰撞、融合,至唐代逐漸本土化并且發展出中國特有的禪宗。油畫加上意象二字就帶有了濃厚中國印記。如果把中國的油畫藝術放在全球視野來看,中國的油畫家們只有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探索出一條路子來,才能獲得某種文化的認同感。
當然,這里面還有個評價標準的問題,就是油畫或者當代架上繪畫本身總能從西方藝術家的作品看到影子,而且其評價標準還在蘇派美術教育的框架和歐洲古典繪畫建立的標準上徘徊。而在西方現代藝術的話語邏輯中,這意味著藝術失去了創造性,而且對于中國的藝術家來說還有文化自尊的問題。因此,過多的思考如何擺脫西方標準而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油畫審美才是關鍵。而這個問題的解決絕不是理論家能完成的,它要求中國的油畫家通過藝術實踐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