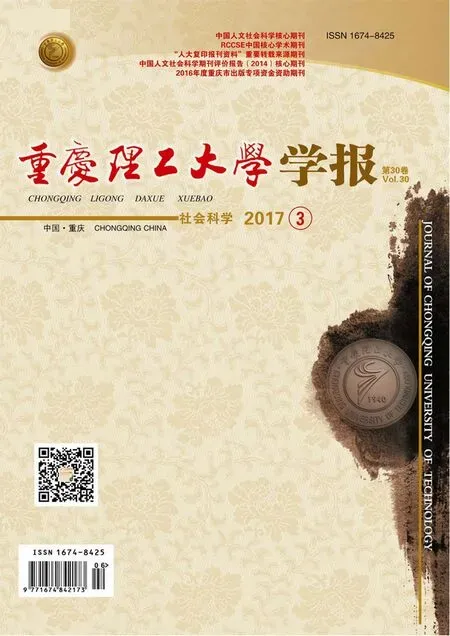德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啟示
戴 哲,張蕓芝
(1.華東政法大學 知識產權學院, 上海 200042; 2.埃克斯-馬賽大學 法學院, 法國 馬賽 13100;3.奧爾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法國 奧爾良 45100)
?
德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啟示
戴 哲1,2,張蕓芝3
(1.華東政法大學 知識產權學院, 上海 200042; 2.埃克斯-馬賽大學 法學院, 法國 馬賽 13100;3.奧爾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法國 奧爾良 45100)
德國專利法規定了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以及類推的合理許可費三種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的方法。實際損失計算方法最為直接,能夠直接確定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但在操作上較為困難,很少在實踐中使用。侵權人所獲利益計算方法并非是為了直接補償實際發生的損失,而是尋求一種公平的解決方法,德國法院會先確定侵權人的銷售收入、應扣除的成本,以及因專利侵權所獲收益占總收益的比重,后計算得出侵權人所獲利益。合理許可費的計量方法是德國司法實踐中運用頻率最高的方法,德國法院在確定許可費的計量基礎以及許可費率之后,即可計算出合理許可費。德國對這三種方法的具體適用對我國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國應減少法定賠償計算方法的使用,并應以上述三種方法為核心,科學、準確地確定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
德國;專利法;侵權損害;賠償額
根據德國《專利法》第139條的規定,當發生專利侵權時,專利權人有權要求侵權人進行賠償。在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上,專利權人可以依據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以及類推的合理許可費*Der Schutzbereich des Patents und der Patentanmeldung wird durch die Patentansprüche bestimmt.Die Beschreibung und die Zeich-nungen sind jedoch zur Auslegung der Patentansprüche heranzuziehen.三種方法進行計量。專利權人可以在這三種方式中自由選擇,當侵權人做出賠償或者判決結束后,專利權人的此種選擇權才失效。這三種方法不能混合使用,更不能累加使用*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March 6, 1980 (Tolbutamid), 1980 GRUR 841, 844.。但是,在一個案件中,一個特定的專利侵權可以采用一種方法衡量賠償數額,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專利侵權可以采用另一種方法計算*參見THOMAS KüHNEN & EVA 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in der Praxis (Th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in Practice)”, No. 1398 (4th ed., 2010).。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所賦予的“自由裁量權”,德國法院可以估算專利損失。德國法院認識到,準確地計算專利損失是幾乎不可能的,因此法院亦接受并非完全符合現實的估算結果*參見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Oberlandesgericht), No. 2 U 39/03, June 2, 2005 (Lifter), http://www.duesseldorfer-archiv.de/?q=node/162, at II.4.a.。當然,這種估算須由富有專業審判經驗的法官做出。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六十五條也規定了上述三種計量方法,但除此之外,還規定了法定賠償計算方法,即“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賠償”。在計量方法的確定上,我國并未賦予專利權人以選擇權,《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了計量方法的適用順序,首先是實際損失,其次是侵權人所獲利益,再次可參照專利許可使用費,最后是法定賠償計量方法。實踐中,我國法院大量使用的是最后一種方法,即法定賠償計算方法。根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統計,我國2008年至2013年的專利侵權案件中,法院采用法定賠償結案的比例高達97.25%,平均賠償額度不到8萬元人民幣[1]。這種計算方法缺乏科學性,得出的賠償數額缺乏準確性,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與我國不同的是,在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上,德國賦予專利權人以選擇計量方法的權利,并且,德國法院以事實為導向,通過當事人舉證、法院調查、聽證等多種方法,準確地確定賠償額,這對我國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一、以專利權人的實際損失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
德國傳統民事賠償制度即以填補損害為主要功能,在制度設計上體現為侵權人有義務因其侵犯專利權而補償專利權人的實際損失。以實際損失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是最能體現專利救濟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在操作上較為困難,實踐中很少使用。
(一)利潤損失的確定
專利侵權可能造成專利權人的利潤損失。專利權人的專利產品銷售可能因為侵權人銷售侵權產品而減少,專利權人銷售的專利產品價格可能因為侵權人降低侵權產品的價格而降低[2]。根據德國法,專利權人有兩種展示利益損失的方法,一種是具體方法,另一種是抽象方法*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Oct. 19, 2005 (Abstrakte Berechnung entgangenen Gewinns), 2006 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Rechtsprechungs-Report Zivilrecht (NJW-RR) 243, 244;。
具體方法要求專利權人證明其特定交易的失敗是基于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同時該特定交易能給專利權人帶來特定的利益,此時專利權人承擔完整的證明責任。抽象方法所涉及的利益指的是專利權人基于其正常的商事活動可預期的利益,這種方法背后的理論在于,一個商人可以從其正常的商事活動中獲取利益。抽象的方法不要求對該利益絕對能夠實現,只要該利益的實現存在足夠的可能性。專利權人需要證明其在商事活動中享有一種可預期的利益,而侵權人可以舉反證,證明專利權人在現實情況下難以獲取該利益*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Abstrakte Berechnung entgangenen Gewinns), 2006 NJW-RR 243, 244.。這種反證是能夠實現的,比如,侵權人可以證明只有自己可以開發和滿足新興市場的需求,或者專利權人沒有能力增加產出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當專利權人所處的市場很小,特別是當該市場只有專利權人和侵權人時,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很可能導致專利權人的利益損失*參見THOMAS KüHNEN & EVA 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in der Praxis (Th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in Practice)”, No. 1437(4th ed., 2010).。比如,隨著侵權人進入市場,專利權人的專利產品銷售馬上下降,那么可以認為專利權人的利益損失是由侵權人銷售侵權產品造成的。然而,大多數案例并非如此簡單,除去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外,有大量其他因素會影響消費者購買其他競爭者產品。這些因素涉及各個方面,比如,競爭對手更低的價格或競爭對手良好的產品品質和服務,更多的競爭者存在,更多復雜的因素介入,意味著更難以識別影響消費者決定的因素。如果專利權人無法充分證明其利潤損失是由侵權行為造成的,那么法院更有可能認定專利權人的損失并不是由侵權行為造成的。專利權人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以證明該因果關系,但德國最高法院明確指出不應設立過高的證明標準*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Schmiermittel), 2008 GRUR 933, 935.。
為了證明利益損失的數額,專利權人必須公開和證明其計算損失的過程,通常計算類似商品的收益是不充分的。為了計算利潤損失,銷售價格的計算必須考慮專利權人在實際生產和銷售產品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支出。
(二)其他實際損失的確定
專利權人的實際損失并不局限于利潤損失,同時還包含了專利權人現存資金的減少,專利權人因此可以要求賠償訴訟費,糾正市場混淆和挽回商譽的開銷*參見GEORG BENKARD, “Patentgesetz (Patent Act),” Sec. 139, No. 62 (10th ed., 2006).。曾有人建議專利權人可以要求 “跳板損害賠償”,但法院至今沒有決定是否采納。“跳板損害賠償”指的是在專利權失效后造成的損失賠償。其背后的理論基礎在于,一個競爭對手若計劃在專利失效后進入相關市場,那么其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建立和擴大市場地位。若侵權人在專利存續期間進入市場,那么就會損害專利權人實際享有的優勢地位*參見THOMAS KüHNEN & EVA 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in der Praxis (Th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in Practice)”, No. 1478(4th ed., 2010).。
(三)實際運用中的問題
從學說角度分析,實際損失的方法是專利損失三種計算方法中最直接的一種,它給予了專利權人因侵權行為而受到損失的計算方法。這種方法只考慮受害的專利權人,不考慮侵權人是否因侵權而獲得了利益。然而,這種方法的適用有很多現實的困難。在復雜商業和技術性強的專利侵權案例中,往往很難證明侵權行為會對專利權人造成何種損害。因此,專利權人通常較難證明專利侵權和專利權人損失理論間的因果聯系*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Nov. 2, 2000 (Gemeinkostenanteil), 2001 GRUR 329, 330.。此外,德國的專利權人通常不愿意為證明其利潤損失而公開內部信息,比如其價格計算過程*參見PETER MES, “Patentgesetz.Gebrauchsmustergesetz (Patent Act.Utility Models Act),” Sec. 139, No. 76 (2nd ed., 2005).。因此,實際損失的方法往往很少在實踐中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專利權人可以根據德國《專利法》139條的另外兩種方法,類似于計算實際損失的方法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
(四)典型案件——“旋轉鎖系統”案*參見Mannheim District Court (Landgericht), Oct. 19, 2007 (Fahrradhelm-Drehverschluss), 2008 NJOZ 2391.
“旋轉鎖系統”案是德國法院使用實際損失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典型案例,涉案的旋轉鎖系統專利可以用于關閉和調整自行車頭盔內的用于保護下顎的防護帶*German Patent No.DE 43 26 049 C2.。原告2(專利權人)給予了原告1一個排他的專利獨占許可,許可費為每個旋轉鎖0.05瑞士法郎,原告1基于此將專利用于其旋轉鎖上。被告生產自行車的頭盔,從1999年到2003年,被告以3.6歐元的單價向原告1購買了945 000個旋轉鎖,并將這些旋轉鎖用于其生產的頭盔,2003年被告停止從原告處進貨。隨后,被告以不到0.6歐元的單價向一家中國生產商購買了303 400個旋轉鎖,由此原告1和原告2起訴被告,要求專利侵權損害賠償,特別要求彌補他們損失的利潤。
原告向法院證明了侵權行為和原告利益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審理該案的曼海姆地區法院認為,如果被告沒有購買侵權產品,那么被告就可能按之前購買的習慣繼續向原告1購買旋轉鎖。被告也向法院證實了市場上不存在其他可以獲取的不侵權旋轉鎖。法院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傳統典型的侵權案件,本案的原告與被告并不是傳統的商業競爭對手,兩者生產的產品并不具有相同的客戶群體。以往的案件中,原告與被告之間往往具有競爭關系,力圖將產品賣給相同的第三人。在這些案例中,法院一般需要分析的是,若市場上不存在侵權產品,那么特定的客戶群體是否會購買更多的專利產品,或者購買其他合法的替代性產品。在本案中,被告已經持續多年從原告1處購買具有專利的旋轉鎖,而被告向中國生產商購買完全一樣的旋轉鎖,這可客觀證明了被告會在未來持續使用同樣的旋轉鎖。根據德國《民法典》第252條,權利人利益損失的舉證責任可以適當降低。法院認為,在普通的商業活動中,被告會像過去幾年一樣,向原告1購買旋轉鎖。因此,有足夠的可能性可以證明原告1會通過被告購買其旋轉鎖而獲利。
依據侵權產品數量(303 400)和原告1、2雙方間的專利許可費(每個0.05瑞士法郎,相當于0.033歐元),法院最終判決被告向原告2(專利權人)支付總額為10 012.20歐元的賠償。對于原告1,法院根據其提供的旋轉鎖產品價格計算流程得出了原告1的利益損失,為了使利益損失計算更加準確,法院假設原告1實際生產了303 400件產品,根據供需理論(即某種產品供給上升,該產品的價格會下降),原告1會降低旋轉鎖的銷售價格(原售價每件3.6歐元)。與侵權者獲得利益的計算方法相類似,利益損失計算中只有那些可以直接被記到侵權產品的成本支出才能被扣除,管理費用無法扣除。在扣除了原材料成本、運輸費用、支付給專利權人的許可費、勞動力支出、生產設備的維護費、包裝費等等成本后,法院認定原告1的利益損失為每個旋轉鎖2.425歐元,結合侵權產品的數量303 400件,最后原告1的利益損失為735 745歐元。
在法院判決書的結尾,法院總結認為,利潤損失的計算不能過于極端,不應超額計算。法院的理由是,如果原告1放棄生產旋轉鎖,而是以每件低于0.6歐元的低價向中國生產商購買專利產品,同時原告1仍以每件3.60歐元的價格出售,那么原告1將獲得更高的回報。
二、以專利侵權人獲得的利益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
計算專利侵權人獲得的利益是德國專利法上第二種計算專利損失的方法,這種方法背后的目的不是為了補償實際發生的損失,而是尋求一種公平的解決方法,該公平的背后是專利權人因侵權行為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它并不是一個不當得利的訴求,而是一種專利侵害救濟的訴求*參見GEORG BENKARD, “Patentgesetz (Patent Act),”Sec. 139, No. 72 (10th ed., 2006).。為了簡化計算,德國法允許最后決定的專利損失數額與專利權人實際損失存在差異。這種方法也避免了上述現實問題的產生。特別是專利權人可以依據侵權人提供的信息計算數額,這樣專利權人就不需要向其競爭對手公開其商業的內部信息。
這種方法的理論基礎在于,如果侵權人使用專利獲得了利益,那么專利權人就損失了對應的利益*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Objektive Schadensberechnung), 1995 GRUR 349, 351.。顯然,這種理論是建立在一種假設的基礎上的,并非絕對的真理,但是德國專利法為此創設了法律擬制,包含專利權人會跟侵權人一樣生產同樣數量和品質的專利產品。在法律承認了這種法律擬制之后,它便成為專利損害賠償的規則之一,不容當事人辯駁,與專利權人是否實際意識到同樣數額的利益無關*參見RAINER SCHULTE ET AL., “Patentgesetz mit Europ?ischem Patentübereinkommen (Patent Act with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Sec. 139, No. 120 (8th ed., 2008).,同時它與專利權人是否實際生產了專利產品或者專利權人通過許可將專利推向市場都沒有關系。
(一)銷售收入的確定
侵權人的銷售總收入來自于專利產品和專利方法。如果專利侵權產品并不是單獨地在市場上出售,而是承載于某個大機械設備上,此時銷售收入的計算應該考慮這臺機械設備的銷售總收入。另外,法院會考慮專利權人的銷售總收入來源于其他的設備、材料,不單來源于專利產品*參見RAINER SCHULTE ET AL., “Patentgesetz mit Europ?ischem Patentübereinkommen (Patent Act with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Sec. 139, No. 79 (8th ed., 2008).。這通常要求證明侵權人能夠單獨地出售這些設備、材料。比如,侵權人租給第三方一臺侵權機器,強制要求該第三方購買這臺機器上的任何部件(包括專利部件、其他設備、材料),這時專利權人可以要求把這些設備、材料的收益計入總收入*參見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No. 2 U 82/02, Nov. 20, 2008 (Papierpolster mit System), http://www.duesseldorfer-archiv.de/?q=node/1924, at II.B.4.a.。
(二)應扣除成本的確定
為了準確地計算侵權人的收益,德國法院會扣除收益的特定成本費用。這種扣除并不是無限制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費用只有被直接計入侵權產品中才能扣除,如果侵權人允許扣除所有與侵權產品有模糊聯系的成本,那么侵權人將人為地減少他的獲益數額,這將不符合專利損失計量的目的。管理費用是典型的發生于商事活動中但不能計入特定產品的費用。依據德國法,假定這些費用會因非專利產品和專利產品的銷售產生,比如,如果侵權產品并未生產,侵權人便不會因該侵權產品而雇傭職員,但是侵權人生產其他產品依然需要雇傭資源,因此扣除這些管理費用是沒有法律基礎的。相當于,侵權人承擔了舉證責任,要求他證明他考慮扣除的特定費用都可以直接歸于侵權產品*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 2001 GRUR 329, 331.。并且,專利權人不應當承擔這種不會發生于專利權人商事活動的費用。
一般而言,應扣除的成本涉及侵權人生產銷售的各個環節。首先,這一成本費用包括了侵權產品實際的材料、產品的實際費用,以及侵權產品的包裝和運輸費用。其次,應扣除的成本還包括了為生產和分發侵權產品而專門雇傭職員的費用,生產侵權產品而專門購入的生產設備的費用,為生產和存儲侵權產品而專門租賃的場所的費用。再次,應扣除的成本還包含了消耗物成本、貼現成本、保險支出、代理人傭金*參見RAINER SCHULTE ET AL., “Patentgesetz mit Europ?ischem Patentübereinkommen (Patent Act with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Sec. 139, No. 125(8th ed., 2008).。
當然,侵權人在生產侵權產品過程中,應扣除的成本并非扣除任何商務活動的費用,應扣除的成本并不包含一般的市場費用。這些費用不包括行政職員和管理層的薪水,不是專門為生產侵權產品而購入的機器和存儲的費用,創設和發展商務活動的支出(因為假想的專利權人在已經運行的商務活動中并不會支出這些費用)*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Steckverbindergeh?use), 2007 GRUR 431, 434.。此外,可扣除的成本還不包括并非為專門生產侵權產品而雇傭職員的支出。還不包括因為專利侵權糾紛發生的訴訟費用、消費者的索賠(除非消費者的索賠是基于專利權人因消費者轉售侵權產品而提出賠償要求),也不包括召回和銷毀侵權產品的支出(因為這并不會減少侵權人已經獲得的利益)。
(三)專利侵權而獲益占總收益的比重的確定
通常,專利發明的價值只構成侵權產品的一部分,一個產品的成功往往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參見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Schwerlastregal), 2007 NJOZ 4297, 4300.。舉例而言,一種復雜產品的利潤建立在多種專利發明的基礎之上,同時還有其他因素如產品的品質,信譽和服務等作支撐。例如一個產品侵犯了多個專利,很顯然,每個專利權人無法基于侵權人的全部利益要求賠償,而只能要求其專利部分的賠償。因此,德國最高法院明確規定,專利侵權人必須對其產品侵犯專利權的部分進行賠償*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 2001 GRUR 329, 332.。因此,在專利權和侵權人所得利益間必須存在因果聯系,在另一方面,專利權與侵權行為也需要存在因果聯系。配額比重的計算要求是:(1)識別影響消費者購買侵權產品的因素;(2)法院基于德國訴訟法典第287條的規定合理評估這些因素所占比重*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Steckverbindergeh?use), 2007 GRUR 431, 434.。
為了完成第一個步驟,通常情況下,德國法院會舉行聽證會,了解消費者決定購買特定商品的動機。當侵權產品只向一小部分消費者銷售時,這種方法非常有效,聽證將有助于法院確定影響消費者購買侵權產品的因素。并且,法官經常會將自己置身為目標消費者的一員,以試圖評估購買動機。可能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因素主要有:(1)專利產品包含的其他專利;(2)專利產品是由一個具有良好商譽的公司生產的;(3)專利產品的商標具有較強的顯著性;(4)侵權產品所體現的技術品質(這種先進技術并不單由侵權專利構成)*參見THOMAS KüHNEN & EVA 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in der Praxis (Th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in Practice)”, No. 1457(4th ed., 2010).;(5)產品的安全性。
在通過第一步確定影響消費者購買侵權產品的因素之后,法院會按照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的規定,確定專利侵權對侵權人利益的貢獻程度。一般來說,侵權人所獲的利益不可能完全源于專利侵權,因此德國法院不太可能認定100%的配額,除非在一種很極端的情況下,此時該專利適用于一種市面上從未出現過的新產品,這種產品的問世意味著一個新市場的誕生,并且這種新市場并不存在非法的替代品*參見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No. 2 U 39/03, June 2, 2005 (Lifter), http://www.duesseldorfer-archiv.de/?q=node/162, at II.4.a; KüHNEN & GESCHKE,supranote 10, No. 1459.。在大多數情況下,法院會尋求一個合適的比重以衡量因專利侵權而使侵權人獲得的利益。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也會影響德國法院對于侵權專利所占比重的確定。如果侵權人不使用涉案的專利,其產品無法受到市場的歡迎,那么侵權人的特殊技能或市場投入就是不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侵權人如果不侵犯專利權人的專利權,那么他將無法獲得任何利益回報。然而,假如侵權人生產不侵權的產品也有可能獲得同樣的利益,這意味著侵權人的特殊技能或市場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專利對侵權人產品的市場貢獻很小,或者根本沒有貢獻,比如,如果涉案專利只占到一個大型軟件項目中的一小部分,且該部分對整體來說并不重要,那么這時配額比重就會非常低。
(四)典型案件——“軟百葉窗”案*參見Düsseldorf District Court, No. 4a O 146/08, June 30, 2009 (Rolladen II), http://www.duesseldorfer-archiv.de/?q=node/2561.
“軟百葉窗”案是德國法院以侵權人獲得的利益計算來確定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典型案例。涉案的軟百葉窗專利*German Patent No.DE 40 06 212 C2.用于一個標準的梯形窗戶中。百葉窗在藝術品中為人所熟知,其生產要求非常高的牽引力,并且百葉窗很容易破碎。涉案的專利在百葉窗中增加了一種特殊物質,使得百葉窗的生產和安裝變得更加安全穩定。原告精通不規則窗戶的遮陽窗工藝,同時生產和銷售帶有涉案專利的軟百葉窗。被告則是一家很大的遮陽窗生產商。從2003年4月至2005年8月,被告一共生產和銷售了4 442塊侵權的軟百葉窗,總價值 3 857 993.35歐元。基于此,原告起訴被告并要求賠償專利侵權損失,原告選擇了侵權人獲得利益的方式對損失進行計量。
為了計算被告的獲益情況,法院考量了應從被告銷售收入中扣除的成本費用,它發現如果被告沒有生產和銷售侵權產品,那么產品原材料、市場營銷等費用就不會發生。這些成本費用共計897 603.13歐元,能夠直接計入侵權產品的成本,因此可以扣除。同時,有一部分被告的消費者還沒有付款(大約2 267歐元),法院也將這部分款項從侵權人的利益中扣除,此外,訴訟費用的支出和為有缺陷的產品支付擔保費也被一并扣除。
特定的機器和工具的費用支出需要特定的條件才可以扣除。首先,被告購買的機器必須是生產軟百葉窗所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是,被告使用這些機器只是為了生產侵權的百葉窗產品。在原告獲取針對被告的禁令后,被告調整了他的生產并在隨后使用原先生產侵權產品的機器生產不侵權的梯形百葉窗,原告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費用是不可扣除的。然而,法院認為這些機器在特定的時間里只用來生產侵權產品,因此這種費用可以扣除。當事人提供的證據顯示,涉案機器能夠使用20年,既然這臺機器為生產侵權產品已經使用了28個月,那么購買該機器可扣除的費用為11 165.34歐元(購買機器的花費 57 421.75歐元×28月/144月)。
再者,被告為生產侵權產品而購買了特定的工具(這些工具主要是為了生產百葉窗所需要的模具),原告認為在專利權人的一般商事活動中這些費用都不會支出,因為這些特殊的工具已經存在,并且這些費用不應該扣除。然而,如果這些工具的支出可以被直接計入侵權產品的費用,那么他們的費用通常可以扣除。也許是因為這些工具都是耐磨材料組成的,法院最后認定這些費用可以扣除,同時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法院估計這些工具的壽命為3年,并最終認定這些工具可扣除的數額為171 437.84歐元(購買工具的成本220 420歐元×28月/36月)。
被告同時還認為6.9%的采購、倉儲、后勤、托收的成本支出也應當被扣除,這些費用都花在了侵權產品上。此外,被告還認為特定的航運費應當被扣除,在計算侵權產品的航運費時,被告首先計算了每個集裝箱的航運支出,再計算了每個集裝箱中含有侵權產品的比重,最后得出侵權產品的航運支出。法院認為,這些類型的支出通常應當扣除,但是一個基于百分比計算后得到的支出并不能直接計入侵權產品成本中,這意味著被告未能證明若被告沒有生產侵權的軟百葉窗,則這些特定的費用支出便不會發生。
信封的費用通常可以扣除,因為如果與侵權有關的信件沒有寄出,那么信封的費用也便不會發生。然而,被告可能在每封信上只花費0.30歐元,該支出甚至還包括了郵寄費。法院認為這種郵寄費的支出不可扣除,因為被告沒法證明:若其不生產侵權產品,則郵寄費用就不再支出(除非解雇郵局的郵遞員)。被告沒法證明信件的花費中哪一部分屬于信封費,哪一部分屬于郵寄費,因此法院拒絕扣除信件的支出。德國法院的嚴謹可見一斑,幾歐元的信件花費都經過了嚴格考量。
此外,法院認為被告生產侵權產品、技術咨詢、售后服務、技術繪圖、研發軟件的勞務支出都無法扣除,因為法院發現沒有一個職員會專門從事生產和銷售侵權產品的工作,大量的職員花費了其部分工作時間投入到侵權產品的生產銷售中,而將其他工作時間投入到其他產品的生產銷售中。被告能夠通過合理的計算得到每個職員投入到侵權產品的工作時間,并基于此算出每個職員在侵權產品上的勞務成本。但是法院認為這些費用支出并不足以直接歸于侵權產品。法院發現被告只投入了很小比重的勞動力生產侵權產品(共占用生產部門0.123%的工作時間,加工部門11.18%的工作時間,程序部門1.54%的工作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下,法院發現,被告沒法證明,若侵權產品從來沒有生產,不會有任何職員會下崗,這些職員將會把多余的工作時間投入到其他的產品生產中。
研發投入也不能扣除(勞務支出和一些產品樣品的材料支出)。在專利權人的正常商事活動中,這些花費不會兩次發生。法院指出,將侵權人研發侵權產品的投入扣除對專利權人而言顯得不公平,而且,法院認為定制侵權產品的測量費用也是不可扣除的,因為沒有職員會專門測量使用侵權產品的梯形窗戶。尖角測量工具的花費也不能扣除,因為沒有一個這樣的工具會專門用于侵權產品的生產和安裝。被告還開設了針對消費者和職員的培訓課程,并將這些培訓費用計入了侵權產品。但這些費用是不可扣除的,因為被告無法證明,若他不生產涉案的軟百葉窗,那么他將不會開設培訓課程。
扣除上述費用后,法院計算出侵權人所獲利益總額為2 700 995.44歐元。然而,侵權人只需交出基于專利侵權而獲得的利益。法院因此需要根據專利對消費者購買動機的影響程度估算一個配額比重。被告提出的配額為0%或者單個數的比重,原告則要求該配額為75%。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法院最終認定侵權人所獲利益的40%應該歸于專利權人,這一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法院首先指出已有的一些因素增加了配額的比重。在被告進入相關市場前,原告是唯一能生產不規則軟百葉窗的產商。被告生產的百葉窗不單損害了專利權益,同時侵權產品存在明顯的質量缺陷,嚴重影響了原告的市場信譽,并導致原告失去了市場壟斷地位。此外,侵權人除使用原告的專利外,并沒有使用任何其他可能影響消費者決策的專利。另一個增加配額的事實是,即便原告已經提起了侵權訴訟,被告依舊持續使用原告的發明專利。
降低配額比重的因素有:第一,在之前的藝術界,這種梯形的軟百葉窗并不知名。第二,涉案專利的唯一新穎性特征是其特有的聯結。然而,法院認識到這個聯結的創造對百葉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提高了百葉窗的市場需求。第三,被告在原告提出禁令要求后,已經獨自研發了一個可替代的聯結,法院據此認為原告專利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會因此下降。
法院指出,專利對產品整體的影響值得考慮,但不應當考慮涉案專利的聯結占軟百葉窗的整體貨幣價值大小。被告抗辯稱,聯結的價值只占整個產品成本的1.68%,實際銷售價格的0.3%,因此侵權專利與被告的獲益是不存在關聯的。同樣,即便被告生產了一個不侵權的軟百葉窗并獲得了更高的回報,這與本案也沒有關系。法院認為,一個新商品的銷售往往比舊產品要好。最后,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1 080 398.18歐元(扣除各項費用后的侵權人獲得利益的40%)。
三、以合理的專利許可費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
除上述兩種方法之外,專利權人還可以要求侵權人提供合理的專利許可使用費,這個方法通常被稱為“類推授權”*參見GEORG BENKARD, “Patentgesetz (Patent Act),” Sec. 139, No. 61 (10th ed., 2006).,在德國該方法的使用最頻繁,并以此決定專利侵權賠償的數額。專利許可使用費的法理基礎在于,侵權人不應當比合法的專利被許可人處于更佳的地位*參見Federal Supreme Court (Dia-R?hmchen II), 1962 GRUR 509, 513.。這種方法的目的是為了便于計算專利權人的實際損失。
許可費數額的計算建立在合法的專利被許可人與專利權人協商一致的專利許可費用的基礎上,這種許可費假設侵權人會與專利權人達成許可協議,同時雙方約定了專利許可使用的期限*同上注。。因此,為了計算許可費,任何影響許可費數額的因素都應該被考慮。法院并不需要考慮專利權人是否真正會給予侵權人專利許可,同時也不需要考慮專利是否為消費者決定購買侵權產品的原因,或者產品可能在沒有專利的情況下依舊以相同的市場價格銷售*參見THOMAS KüHNEN & EVA 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in der Praxis (Th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in Practice)”, No. 1410(4th ed., 2010).。這種許可類推是一種抽象的計量專利侵權損失的方法。不論專利是否影響了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決策,假定的被許可人都需要支付許可費。
在實踐中,如果專利權人已經將專利許可給第三方,那么,專利權人與第三方達成的專利許可協議就成為了一個計算合理許可費的可靠依據。再者,倘若專利許可協議的數額足以證明專利權人已經在市場設立了一個使用專利的補償機制,這些專利許可的費用數額對于許可類推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此時,無需考慮專利許可協議的條款是否是商業上普遍存在的或者條款的細節是否恰當。如果專利權人在市場上可以要求和獲取這些條款,那么合理的被許可人只能同意依據這些條款交納許可費。
如果專利權人并未與第三方就涉案專利達成專利許可,那么法院就必須確定專利許可的合理使用費。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法院會以專利許可協議下的實際使用為基礎,著重考慮兩個要素:法院會決定許可費的計量基礎;法院會為該計量基礎選擇一個合理的許可費率。由此,合理使用費=計量基礎×合理的許可費率。
(一)計量基礎的確定
在德國的多數案件中,理性的雙方當事人會選擇以侵權人的銷售總收入作為合理使用費的計量基礎。然而在特定的情況下,適用銷售總收入作為合理使用費卻并不適宜,比如,侵權人的價格并不由市場決定(如他將侵權產品賣給關聯公司),在這種案例中,理性的雙方當事人會協議達成一個許可的計量基礎*參見THOMAS KüHNEN & EVA 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in der Praxis (The Enforcement of Patents in Practice)”, No. 1410-11(4th ed., 2010).。
相關的銷售總收入通常是以專利裝置進行計量的,比如,專利訴訟中的侵權產品。在案例中,往往專利只是產品的一個特定特征。比如,前文介紹的“軟百葉窗”案中,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包含了“軟百葉窗”,但是該專利的新穎特征僅僅是一種新類型的聯結點。而法院往往會將產品的整體銷售收入作為計量基礎,因為產品的整體而不是局部會因該專利而受益。此外,在很多專利案件中,涉案的產品在市場上被打包出售,因此獨立識別這種產品中的專利部分的價值會變得非常困難。理性的雙方當事人可能會選擇從日常商事活動中獲得計量基礎。比如,如果專利的新穎性特征只對整個產品的一小部分起到實際作用,那么一個較低的許可費率就是合適的。
在確定的情況下,理性的雙方當事人會選擇一個超過專利裝置的整體集合,特別是當侵權產品由不同部分構成時。比如,在下文介紹的“加蓋裝置”案中,涉案專利與一個蓋子裝置有關,法院發現相關的銷售收入是由整體產品的銷售而取得的,蓋子裝置只是整體產品的一個部分,無法單獨銷售。計量基礎的選擇是基于商事活動的普遍習慣和假定情況的方便性,無論該選擇是以專利裝置的銷售收入或是以整體產品的銷售收入為準*參見 GEORG BENKARD, “Patentgesetz (Patent Act),” Sec. 139, No. 69 (10th ed., 2006).。一般來說,涉案的產品被視為一個整體,包括專利裝置部分,無論該專利裝置部分可否單獨出售。事實上,計量基礎與許可費率之間互為影響。如果計量基礎是整體產品的銷售收入,那么許可費率通常會比較低,當使用專利裝置部分的銷售收入作為計量基礎時,許可費率往往會設得比較高。
(二)許可費率
為了衡量許可費率,法院第一步通常會查找市場上常用的許可費率,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的規定,法院接下來會決定是否有其他因素會增加或減少涉案許可費率。德國專利法院在大量的司法實踐中已經根據不同的行業形成了不同的許可費率*PETER MES, “Patentgesetz.Gebrauchsmustergesetz (Patent Act.Utility Models Act),” Sec. 139, No. 78 (2nd ed., 2005).。然而,當事人必須向法院展示市場上常用的許可費率。如果專利權人在案發前已將他的涉案專利許可給第三方,那么這個許可協議就為法院的判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依據。法院同樣會考慮與涉案專利類似的專利許可協議。此外,在行業中實際使用的許可費率可能來源于公開發行的許可費率匯編,這些匯編系統地分析了大量的法院決定、德國專利局下的仲裁委員會的決定以及行業調查等。當使用這些匯編時,考慮到匯編中有些許可費率是在多年前做出的,而目前行業中的許可費率通常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法院會下調特定的許可費率。同時,法院還會根據經驗形成某些特定的規則,比如“拇指規則”。該規則認為理性的被許可人愿意支付其產品收入的1/8~1/3給其產品使用全部專利的專利權人,數據證明,通常為25%~30%的產品收入*參見GEORG BENKARD, “Patentgesetz (Patent Act),”Sec. 139, No. 65a. (10th ed., 2006).。最后,法院可以獲得評估合理許可費的專業建議。
在前述的基礎上,法院會考慮相關的市場因素并評估得出一定范圍的專利許可費,隨后法院會依據這個范圍的專利許可費決定涉案專利的合理許可使用費。為了合理評估,法院會考慮案件的特定背景,特別是侵權行為。下面列舉部分典型的考慮因素,其中有些因素在任何專利侵權案件中都需要考慮,只是這些因素在不同案件中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另外一些因素則可能只在部分案例中出現。
可能導致許可費率升高的因素包括:(1)涉案專利不存在被無效的風險(許可費率的增加取決于專利被無效的可能性,如果專利已經在無效程序中,那么許可費率將不會有任何的提升);(2)侵權人為銷售侵權產品而持續不斷的市場投入;(3)涉案專利的價值,特別是當專利可能給專利權人帶來市場壟斷地位;(4)涉案專利的市場范圍,特別是當市場上不存在不侵權的替代品;(5)涉案專利能提升全國在特定行業的技術和商務能力;(6)侵權人預期的高額收益(特別是在不重要的商業領域的盈利);(7)專利實際的許可范圍(不單指專利帶來的技術,還包括專利權人已經擁有的知識、技能或者市場上較好的商譽);(8)侵權產品對專利權人的市場商譽所造成較大損害。
可能導致許可費率降低的因素包括:(1)專利權人可以在任何時間禁止侵權人的使用;(2)侵權損害賠償的訴求超過了合理使用費;(3)侵權行為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意味著侵權人還來不及收回他的投資);(4)因侵權人或第三方使用涉案專利而導致侵權產品的價值增加;(5)侵權產品的高收益來自于:① 行業發展的正常結果;② 侵權人良好的商譽(需要侵權人有較好的經濟實力、廣告投入、產品質量、銷售組織、消費者服務、商業關系);(6)在先使用的權利。
(三)典型案件——“加蓋裝置”案*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No. 2 U 38/08, July 17, 2009 (Kantenleimmaschine II), http://www.duesseldorfer-archiv.de/?q=node/2541.
“加蓋裝置”案是德國法院以合理的專利許可費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典型案件,這一專利案是關于一個加蓋裝置的,這個加蓋裝置是膠合機的一部分,用在家具行業中*European Patent No.EP 0 538 513 B1.。從1996年至2005年,被告一共賣了73臺帶有加蓋裝置的侵權膠合機,總價高達1 467 141.53歐元。原告基于合理使用費的方式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法院最終認定許可費率為2.5%,判決被告給予原告36 678.54歐元的賠償。上訴后法院改判,將賠償數額降低至14 671.41歐元。
法院首先尋找計算許可費的計量基礎。法院認為應將整臺膠合機的銷售收入作為計量基礎。加蓋裝置不是單獨出售,而是作為整臺機器的一部分出售。由于整臺膠合機的銷售收入數額容易獲取,同時很難獲取加蓋裝置的單獨收入,因此理性的許可方會選擇將整臺膠合機的銷售收入作為許可費的計量基礎。
隨后,法院開始探討許可費率。根據已經公開的標準許可費率信息和德國工程聯盟的行業調查,法院發現,在侵權持續期間(1996—2005年),機械制造產業的許可費率普遍保持在1%~5%,這些許可費率都將整體產品的銷售收入作為計量基礎。法院認定,在這個范圍內,涉案加蓋裝置的許可費率應該處在一個更低的限度。兩個方面的因素值得考量。第一,計量基礎和許可費率之間存在一種交互作用:計量基礎升高,許可費率就降低,反之亦然。據估算,加蓋裝置價值占到整臺膠合機價值的近11%,因此法院認定加蓋裝置的貢獻只占整臺機器收入的1/9。第二,法院發現市場上不存在本案加蓋裝置的替代裝置,使用涉案專利能帶來非常明顯的市場優勢,法院認為這些優勢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為被告已經使用這些侵權產品超過10年,并且在原告提起訴訟后仍持續使用。然而,法院認為,發明專利只對產品的價值創造貢獻了很小的比重,因此專利的技術和商業價值不應被過分高估。在這個基礎上,法院認為,許可費率不應當超過1%。
法院拒絕根據原告提出的理由提高許可費率,因為:第一,法院指出德國專利法不允許對侵權人征收懲罰性賠償金,這與專利損害賠償的“填平原則”相沖突;第二,法院認為專利許可費的增加需要建立在一個基礎上,即該專利不存在被無效的風險。許可費增加的幅度取決于專利被無效的風險大小。在本案中,專利無效的風險非常低,因為之前針對本專利的無效程序并沒有成功。
四、結語
德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在計算上共有三種方法,分別為專利權人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以及合理許可費,專利權人可以選擇性適用。與德國相似的是,我國現行《專利法》第六十五條也規定了這三種計算方法,但與德國不同的是,我國還規定了法定賠償計算方法,并且,我國沒有賦予專利權人以選擇計算方法的權利,而是對計算方法規定了適用的特定順序。不過,考慮到在實際確認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上,不論選取何種計量方法,都需要由專利權人進行舉證,我國可以參考德國,賦予專利權人對于計量侵權損害賠償方法的選擇權。如此一來,專利權人可以根據其已有證據確定一項可適用的計量方法,這也有利于法院的審理并確定具體的賠償額。在知識產權領域中,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草案送審稿已經采用了類似的規定,賦予著作權人以選擇侵權損害賠償計量方法。我國可以對現行《專利法》第六十五條進行修改,做出如下規定:“侵犯專利權的,在計算損害賠償數額時,權利人可以選擇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權利交易費用的合理倍數或者一百萬元以下數額請求賠償。”
在實踐中,我國法院主要使用的是法定賠償計算方法,這種計算方法減輕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也降低了法院在操作上的難度,有可取之處。但是,由于缺乏實證的數據支持,這種方法實質上降低了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準確性,不利于為當事人所接受,并且,這種方法賦予法官以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降低了法律的可預測性,不同法官根據類似案情得出的賠償額幾乎難以保持一致,這亦不利于維護法律的公正性。與我國不同的是,德國法院嚴格遵循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以及合理許可費這三種計算方法,通過當事人舉證、法院調查、聽證等多種方法確定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這些計算方法為專利權人尋求侵權救濟提供了解決之道。綜觀全球專利制度,除德國之外,美國、英國、日本等專利強國都沒有規定專利侵權的法定賠償計算方法。
法律雖然追求效率,但更強調公正,這就必須建立在厘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否則,“以事實為準繩”將成為一句空話。我國未來司法實踐可以借鑒德國法院,在專利侵權賠償損害賠償額的確定上,以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以及類推的合理許可費為核心,科學、準確地確定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而不是一味地采用法定賠償方法計算賠償額,這才是現今法院所應選取的方法。三種方法在具體運用上,實際損失計算方法最為直接,能夠直接確定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但該方法在操作上較為困難,專利權人較難對其實際損失進行舉證。后兩種方法并非為了補償實際發生的損失,而是尋求一種公平的解決方法,專利權人的舉證難度較小,實際使用頻率更高。總的來看,當發生專利侵權時,應由專利權人根據個案案情以及其所掌握的證據,自主選定專利侵權賠償計算方法。
[1] 張維.97%專利侵權案判決采取法定賠償[EB/OL].[2013-04-25].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4/id/948027.shtml.
[2] 陳協平.我國侵權責任法上的純粹經濟損失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4):87-93.
(責任編輯 馮 軍)
Research on Patent Infringement Damages Calculation in Germany
DAI Zhe1,2, ZHANG Yun-zhi3
(1.Intellectual Property Academ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2.School of Law, Aix Marseille University, Marseille 13100, France;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Orleans University, Orleans 45100, France)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patent law, the patentees can determine their damages in three ways: (1) the actual damages they suffered, (2) the profits the infringer made by infringing the patent, or (3) a fictitious reasonable royalty. The method of actual loss calculation is the most direct way in determining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damag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alculate and rarely used in practice. The method of profits calculation doesn’t aim to direct compensation for actual losses, but rather to seek a fair solution. The German court will first determine the infringer’s sales revenue, costs that should be deducted, and proportion. Later the German court could calculate the profits which the infringer has gained. The method of reasonable royalty calculation is the approach most often used to determine patent damages in Germany. After determining the basis of license fees and license rates, the court can calculate a reasonable license royalty.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methods of German patent infringement damages calculation. But China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statutory compensation calculation method, and should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damages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n using these three methods.
Germany; patent law; infringement; damage
2016-04-2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驅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職務發明制度研究”(16ZDA076)
戴哲(1989—),男,福建龍巖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識產權法;張蕓芝(1990—),女,廣西賀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觀經濟學。
戴哲,張蕓芝.德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啟示[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4):94-104.
format:DAI Zhe,ZHANG Yun-zhi.Research on Patent Infringement Damages Calculation in Germany[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4):94-104.
10.3969/j.issn.1674-8425(s).2017.04.014
D923.42;DF523.2
A
1674-8425(2017)04-00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