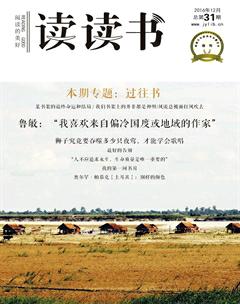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張瀅
一
準確來說,我對民國知識分子的最初印象來自于電視劇而非書本。2000年,以徐志摩感情生活為藍本的民國言情劇《人間四月天》熱播,劇中所描繪的年輕詩人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三位才女之間的感情糾葛,成為人們談論民國時經久不衰的話題。順著戲劇營造的浪漫氛圍,我開始閱讀以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詩人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月派詩選》是不錯的入門讀物。在這本詩集中,除了徐志摩、聞一多、卞之琳等以詩聞名者之外,學建筑的林徽因、寫小說的沈從文、研究莎翁的孫大雨都赫然在列。
除新月派詩歌外,以民國知名才子佳人的情感經歷和個人軼事為重點的傳記類作品擁有更為廣大的讀者群。與其說是傳記,實則更類似于披著民國外衣的現代青春言情讀物。這一類圖書的出版,臺灣早于大陸。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播出后不久,臺灣金牌編劇王蕙玲將劇本改編出版,名為《人間四月天之徐志摩的愛情故事》,一經付梓,便在港臺地區熱賣。一年后,我在香港書市上買到此書,又順帶回一本大孚書局印行的繁體版《徐志摩全集》,也是當年的暢銷書之一。
起源于港臺的民國言情風很快就吹到了大陸,并形成燎原之勢。以徐志摩為中心,紅顏知己如林徽因、陸小曼、凌叔華,師長同儕如梁啟超、梁思成、胡適,國際友人如泰戈爾、狄更生都被牽扯其中。這些人之中當屬林徽因被發散最多。大眾眼中的林徽因家世優良、才貌雙全,又有諸多才子愛慕,簡直是言情故事的天然素材。僅我所見的市面上關于林徽因的各類傳記作品就不下二十種,真實的印行數量只會更多。青春文學作家白落梅所寫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傳》是這類作品中的代表,遣詞優美、抒情真切是它們吸引普通讀者的一大原因,對主人公情愛經歷的細致描繪與渲染更是能引發女性讀者的情感共鳴。
二
隨著年歲增長,歷史讀得多了,對民國的觀感也日益復雜起來。在傳統的歷史教科書上,從1912年清王朝覆滅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期間的中華民國時代,其間布滿主權淪喪、列強橫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這才更像是普通人所面臨的真實生存狀態。沉重的歷史車輪輕而易舉地將大眾對民國時代一廂情愿的美好幻想碾得粉碎。事實上這樣的心態并非難以理解,就像喜愛武俠小說的人總幻想自己是武功蓋世的大俠而非被一招斃命的啰嗦一樣,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也總是更愿意看見那些光輝的幸存者。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對“才子佳人”情結的審美趨向,古典章回本中的癡男怨女總歸是離得遠了些,不比民國離得近了,還留下了諸多影像供人觀瞻,真實可感更便于想象。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歷史檔案逐步開放,歷史敘述范式愈發多元,在最初的港臺民國言情風吹過之后,學界和知識界開始嘗試挖掘民國知識分子的不同側面。
民國知識分子生活在國家危難深重的年代,絕大多數都存有艱苦卓絕、視死如歸的風骨。作家岳南的《南渡北歸》三部曲描繪了大批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火中流亡西南再回歸中原的歷史過程,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接近一個世紀,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從北平到長沙,從長沙到昆明,又從昆明到四川李莊。國難當頭,大師們舉全家之力保存現有的文化和資料,一次又一次的遷徙只是為了資料的安全和知識的傳播。過程雖然狼狽,但亦悲壯。為著知識分子的擔當,大師們考慮更多的始終是如何做學問,而非兒女情長。
三
大學時期是我受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影響最深的時期,每每讀史,總難滿足于對具體史實細節的了解,渴望站在更高的角度、更長的時間線上將歷史連貫起來,“從超過人生經驗的角度看去”,更能理解“我們生命旅途之原委”。
出于這樣的原因,我開始閱讀對民國知識分子群體進行研究的著作。謝泳是較早關注民國知識分子群體及其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之一,1998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了《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兩部作品。作者在九十年代早期開始做儲安平和《觀察》周刊的研究,在查考資料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了不少關于西南聯大的史料。在戰爭年代,大學校園相對和平和寬松的環境更有利于保存和傳承國民知識分子的思想傳統,而集合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頂尖高校的優秀師生的西南聯大,更是為學人們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研究土壤。西南聯大與抗戰共始末,成立八年以來,共有298名教授先后為這所大學服務,人校學校八千佘人,畢業3800余人,后成為兩院院士的共計172人,這樣的數據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中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奇跡。謝泳以大量史料為基礎,通過西南聯大師生的命運勾勒出了特殊年代里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發展及衰落的軌跡。他認為聯大精神之所以不朽,在于“民主傳統和寬容精神”。對于一所高校而言,這樣的傳統和精神首先體現在學術風格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學術繁榮的命脈,戰爭必然會在客觀條件上對學術產生深重的影響,但民國政府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卻是相對寬松的。在民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所享受到的人身、思想及學術的自由權利遠超過此前及此后的任何一個時期。民主寬容的學術風氣和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在民國三十七年歷史中得到繼承和弘揚,這種繼承和弘揚起自五四,于西南聯大達到最高峰,終于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國的學術界再無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識。
其次,民主與自由的思想也體現在了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與表達之上。西南聯大的教授學生各黨各派都有,比如馮友蘭、雷海宗是國民黨,聞一多是著名的左派人士,民主社會黨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無黨派有張奚若和陳序經。他們雖然持有不同政見,在關乎民族、國家的問題上思想途徑也不盡相同,但出發點都是一致的——為著一個更光明、更進步的中國。聯大寬松包容的環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天然地相信他們有言論的權利”,因而可以勇敢的投入到各類政治運動中去。謝泳將“一二·一”學潮運動視為這種政治自信與自覺的一個縮影,自1949年之后,知識分子身上再不見這樣的氣質。
四
大歷史讀多了,偶爾又覺民國的形象因為宏觀而渺遠模糊起來。上學時,曾聽過歷史系的先生說,史學的首要價值在于講一個好聽有趣的故事。這樣的總結也許過于淺顯,但確是大多數人熱愛歷史的原因。
我想世上最有趣的文章,一般都是不為任何現實目的而寫就的。日記和書信當屬這一類。舊時的文人除了紙筆沒有太多溝通和抒發感情的渠道,故而頗愛寫信與記日記。而他們書信與日記中的形象往往顛覆人們往常的認知。
譬如大師們在學業上也有偷懶的時候。胡適留學日記中的“打牌”、“打牌”、“打牌”一度引起學生們的共鳴,實際上他不僅對自己寬松,對后輩亦是如此。在寫給陶孟和女兒的信中就曾說:“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沒有進步。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體好,進步更快。”季羨林日記中罵北大教授的段落——“媽的,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氣,還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東西?”——也十分著名,常被備考的學生拿翻出來祭奠。
魯迅和許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也曾極大地改變了我對魯迅的看法。起初他稱許廣平為“廣平兄”,信里內容也盡是些關于人生、戰斗、國運的大話題。后來稱呼漸漸變了,“廣平兄”換成了“乖姑”和“小刺猬”,而自己的署名從“魯迅”簡略成“迅”,最后變成了“你的小白象”。信里講述的內容也都是些生活瑣事。比如“牙齒補好了,只花了五元”,或是“吃了一元半的夜飯,十一點睡覺,從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點鐘”。讀到這些才發現,閑散、松弛、溫柔等等詞匯也是可以用來形容魯迅的。此中的魯迅比任何文字中所見的都更加親切可感。我們看慣了他冰冷堅毅的形象,然而沒有人是生來就要作為旗幟、豐碑抑或精神符號的,那些被符號化的人也曾是活在這世上的血肉之軀。
除書信和日記之外,最不為現實目的而寫的文字大抵是遺書了。團結出版社出過一本民國名人遺囑的集子,名為《最后的聲音》。從紙質到編排再到內容都不是佳品,不過在選題上彌補了出版空白。從一個人的人生窺見一個時代的命運,再撥開歷史的煙霾凝視每一個脆弱的個體,從中體悟超乎時代局限的人生精義,這是歷史留給現世最溫情的觀照。
1967年,周作人在“紅衛兵”的暴打下身故。他在兩年前擬好的遺囑中說道:“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梁實秋的遺愿也是類似:“余故后,關于治喪之事,一切從簡。一、不設治喪委員會。二、不發訃聞,不登報。三、不舉行公祭,不收奠儀。”沈從文最為灑脫。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么要說,他只答:“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好說的。”
當然,遺言的風格也與臨終時的狀態相關。在極度痛苦中走到生命盡頭的,也就顧不得太多斯文。中國比較文學鼻祖吳宓先生在文革中受盡折磨,雖熬過了批斗卻無法恢復原有的精神,“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是他臨終前的囈語。瞿秋白似乎要從容一些。在監牢里,饑餓的他想念家鄉的吃食,在《多余的話》的結尾寫道:“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然而歷史的巨石還是迅速翻滾而下,碾過肉身。生命不過軟如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