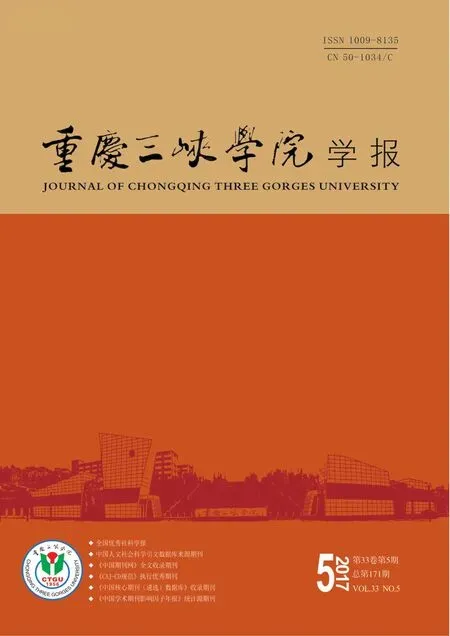魯迅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與其進化論知識的關系
許祖華
?
魯迅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與其進化論知識的關系
許祖華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魯迅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可以用魯迅自己的一段話來概括:“蓋科學者,以其知識,歷探自然見象之深微”。魯迅習得的進化論知識,在屬性上屬于一種關于自然的科學理論知識。魯迅對這種知識的整理,與其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都是基于自己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進行的整理。
魯迅;科學信念;進化論
在魯迅積累的與自然科學相關的理論知識中,特別重要的當屬醫學與進化論的知識。它們不僅是魯迅曾經系統地學習過的知識,也是對魯迅思想與文學創作的影響最為廣泛與深入的知識。而進化論的知識,無疑是魯迅整個知識系統中最重要的知識。因為魯迅雖然系統地習得過醫學,尤其是現代西醫學的知識,并且創造性地運用于小說、雜文的創作中,但他卻從來沒有以論文或著作的形式系統地整理過這類知識。與之相比,進化論的理論知識不僅是魯迅最早系統地汲取的關于自然科學的理論知識(比魯迅汲取醫學知識還早),也不僅是魯迅在從事精神生產活動中使用最多的一種理論知識,而且,他還有意識地系統整理過這類知識。所以,魯迅關于進化論的知識,是我們應該特別關注的對象,更是我們從知識學的角度研究魯迅習得的相關知識,特別是理論知識應該著重研究的對象。而魯迅對進化論知識的整理,與其關于科學的信念有密切的關系。
一、魯迅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
1908年,魯迅在《科學史教篇》一文中,曾經寫下過這樣一段話:
蓋科學者,以其知識,歷探自然見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會,繼復流衍,來濺遠東,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則尚浩蕩而未有止也。[1]25
理解魯迅這段話可以有兩個基本思路,一個是哲學本體論的思路,一個是狹義的哲學認識論,即知識學的思路。如果按照哲學本體論的思路理解,魯迅這段話所揭示的正是科學的本質與功能(影響),表達的是魯迅關于科學是什么的觀念;而如果從魯迅對“科學”是什么下判斷的句式(判斷句)和思路(基于既有“知識”與主體認知關系的思路)來理解,則可以說是魯迅對科學的一種心理認知狀態,表達的是魯迅關于科學的一種知識學的信念,并且不是原型信念,而是模型信念①,因為,魯迅關于科學的這種信念符合知識學所認可的模型信念的三個基本特征,即理性特征、邏輯推導特征和以知識為核心的特征。
理性特征,是模型信念最為顯然和基本的特征,模型信念“是在主體經驗觀察的基礎上,對經驗觀察得到的信息進行選擇、理性思考而形成的一種理性信念”[2]143。這種具有理性特征的信念,不僅因理性的作用具備了強勁的魅力,而且以自身特有的規范構成了與其他信念,如原型信念等之間的顯著區別。結合魯迅關于科學是什么的判斷話語,分別從信念形成的基礎、信念所包含的內容、形成信念的方式三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述,也許看得更為清楚。
信念,作為認知主體面對對象的認可或者不認可的心理傾向與狀況,無論是按照經驗主義知識學的觀點,還是按照理性主義,甚至先驗主義知識學的觀點來看,它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要基于一定的事實或現實,無論這些事實或現實是社會提供的,還是由書本等載體提供的,也不管是由事件構成的現實,還是由語言構成的“思想的現實”或者是由認知者懸定的諸如上帝、理念等的所謂現實,但不同類型的信念所基于的事實的特性與類別卻是不同的。一般說來,原型信念所基于的事實,往往是“在場”的事實,是個體所經驗的個別事實和可以被認識主體所感知的事實,即能夠被認知主體耳聞目睹和可以通過認知主體的感官感知的事實,這既是原型信念十分突出的特點,也是原型信念十分寶貴的品格,當然也是原型信念與其它信念區別的特征。而與原型信念相比,模型信念則不僅基于“在場”的事實,更基于“不在場”的事實;不僅基于可以被感知的事實,更基于無法感知的事實(如光速、分子結構等);不僅基于個體、個別的事實,更基于普遍與整體的事實。從魯迅關于科學是什么的判斷所表達的意思看,魯迅“相信”科學就是“歷探自然見象之深微”的學問,這樣的判斷及形成的信念,并不是基于“在場”的哪門科學如物理學、生物學、數學等所提供的事實,也不是基于魯迅自己曾經習得或者熟悉的哪幾門自然科學所提供的事實,而是基于“所有”的自然科學所提供的事實,即魯迅并不是僅僅相信個別科學項目,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探討自然現象的學問,而是相信“所有的自然科學”都是探討自然現象(無論這些自然現象在場還是不在場,能被感知還是無法感知)奧秘的學問(從語法學來說,魯迅這里使用的“科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集合”詞語)。所以,魯迅關于科學是什么的判斷,所表達的并不是他對一門或幾門自然科學的認知與信念,而是對“所有”自然科學的共同特征的認知與具有“模型”規范的信念。
從信念所包含的內容來看,原型信念,由于主要是在關注事實“現象”的過程中認知主體基于經驗形成的信念,因此,原型信念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是現象的內容。與之相比,模型信念不僅關注“事實”現象本身,更關注現象之中的本質與規律,尤其是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更是如此。達爾文曾指出:“科學就是整理事實,以便從中得出普遍的規律或結論。”[3]2模型信念中所包含的內容,不僅是關于現象的內容,更是關于現象深處的本質與規律的內容。從認識論的角度講,要把握對象的本質規律,認知主體不能僅僅依據自我的經驗,因為經驗只能感知與把握“在場”對象和“在場”對象所呈現的現象特征,而對象的本質規律由于不是以具象的形式存在的——它既不具體存在于某個時間段,更不具有可以被感知的空間形態,自然無法“在場”,因此,認識主體要把握對象的本質規律并使用相應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認知,只有通過理性的思考才有可能實現,而理性的思考,又恰恰是形成模型信念的基本依據,沒有理性思考這個依據,認識主體不僅不能將不在場的對象納入到自己的思考中,更不可能把握在場與不在場對象的本質規律,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主體要形成關于對象本質規律的模型信念,就如尋索“無源之水”與“無本之木”一樣不可能。以此考察魯迅關于科學的信念,這種信念所關注的不僅是科學的“現象性”特征,即科學總關乎“自然現象”(而不是其它現象,如社會現象),更揭示了科學的本質特征,即科學不僅探討自然現象是什么和怎么樣,更探討自然現象“深處”的“奧秘”,也就是規律。不可否定,原型信念,包括魯迅的原型信念并非只具有描述“現象”的功能,如魯迅關于中國人的原型信念,在這類信念中,魯迅也揭示了某些中國人的本質,如大眾的“看客”本質等等(參見筆者的有關拙文),但很明顯,魯迅對這些中國人本質的揭示是“通過現象”完成的,所形成的關于這些中國人的某種信念,如“看客”信念、無操守信念等,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可知可感的,可以驗證的現象看本質的結果。與之相比,魯迅關于科學本質的揭示,卻是完全“剔除”了各種豐富而生動的具體“現象”完成的,是通過理性抽象化的結果,這個結果中所包含的內容,雖然也包含了關于對象“現象”特征的內容,但主要成分則是關于對象的本質規律的內容。
從形成信念所采用的方式來看,原型信念主要采用直觀感知的方式形成,模型信念則主要采用邏輯推導的方式所形成。魯迅這段話所表達的關于科學的信念,不是依據自己的直觀“感受”形成的,而是經過理性思考,依據邏輯推導的方式條理分明地“概括”出來的。所謂邏輯推導的方式,人們認可的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歸納法,魯迅當年將其概述為“內籀之術”,一種是演繹法,魯迅當年將其概述為“外籀之術”。在表達關于科學的信念時,魯迅主要采用的是“內籀之術”,即歸納法,歸納了各種自然科學的基本特征而概括出這些自然科學的共同特征。這種由“概括”形成的模型信念,雖然不如由“經驗”形成的原型信念生動、直觀,卻具有由邏輯所規范的嚴謹與簡明,而嚴謹與簡明,正是模型信念的特征。
模型信念不僅具有理性思考與邏輯推導的特點,還有“這種信念以知識為內核”[2]144。如果說,原型信念主要是以“事實”為基礎和“內核”的話,那么,模型信念則主要以經過了驗證的“真”信念——知識為基礎和內核并由此而“為理性地整理各種經驗知識提供思維的準則,為把經驗知識構成理論體系提供一種基本框架,為把由外界輸入的信息知識變成科學理論提供變換規則。”[2]144魯迅明確表達了科學并不是以事實為基礎探索自然奧秘的學問,而是以“知識”(無論這種“知識”是來自經驗還是理性,也不管這種知識來自于實踐還是書本,更不管這種知識是常識還是人們并不熟悉的原理,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為準則來發掘自然奧秘的學問。英國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曾經指出:“科學永遠不會從零開始……今天的科學建立在昨天的科學之上(所以是昨天的探照燈起作用的結果);而昨天的科學又以前天的科學為基礎。”[4]386魯迅確切地“相信”:科學就是基于既有知識發現問題并努力解決問題的學問。雖然魯迅沒有進一步指出科學探索“自然深妙”的過程是一種什么過程,從其所指來看,只能是指“創造新知識的過程”,而創造新知識,正是模型信念最重要的功能。所以說魯迅關于科學的信念,是一種模型信念。
二、魯迅習得的進化論的知識屬性
關于進化論本身的知識屬性,中國學術界有人認為,在今天它已經不是一種理論知識了,而是一種經驗知識。有一位研究現代知識學的學者曾發表這樣的觀點:“就時空的角度相比較而言,在某個歷史階段上屬于理論的知識,在更前進了的歷史階段上又成為一種經驗知識。”因為這樣的理論知識“被大多數人接受時,轉變為人的常識。例如,阿基米德關于水的浮力的原理,達爾文的進化論,現在都已成了人的常識”。而“常識就是一種可以感知、直覺的,被人無疑問地接受并世代承襲的經驗知識”[2]52。列舉達爾文的進化論由理論知識轉變為經驗知識的例子,可見進化論在當下不僅在屬性上屬于經驗知識的范疇,在從理論知識轉變為經驗知識的過程中具有代表性和公信性。這位學者的觀點雖是一家之言,但經得起推敲與驗證,因為他揭示了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理論知識發展成為常識即經驗知識的規律,其認識也符合知識發展的相關事實。
一般說來,衡量一種知識,特別是關于自然的科學知識是否為理論知識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本體標準,即“理論知識的全部問題就在于說明的問題”[4]297。一個是“時空標準”,即上面那位學者所采用的標準。按照本體標準來看,達爾文的進化論是“說明問題”的理論知識,而且是論證與說明“生物物種會變化、生物的物種會分化”[5]6問題的理論知識;按照“時空標準”,站在今天社會與時代發展的層面回望,進化論已被多數人理解和接受,成為一種常識,一類經驗知識,但在魯迅接受它的時期,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是關于自然,尤其是關于生物發展、變化特征與規律的理論知識,還不是具有世界觀、價值觀等哲學屬性和社會科學屬性的理論知識。羅素在20世紀初曾經指出:“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考察的問題上,進化論并不是一種真正科學的哲學。”[6]7“進化論的主要興趣在于人類的命運問題,至少是關于生命的命運問題。”進化論,尤其是達爾文所創造的進化論對“關于生命的命運問題”的基本解答就是:“不同的種是由于適應環境而從一個未甚分化的祖先產生出來的。”[6]10-11羅素不僅否定了進化論具有哲學與社會科學屬性的觀點,而且用最簡潔的話語概括了這門科學理論關涉的主要問題,即生命在自然環境中的進化規律問題,指出了進化論屬于關于自然現象學說的知識。羅素的觀點符合事實并經受得起檢驗,因為進化論,尤其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在它誕生的時候,所探究的就是生物(生命)的“自然”變化、分化等進化的問題,“說來有些諷刺,達爾文并不認為他的理論適用于社會”[7]23。魯迅恰巧就是在羅素論述進化論知識屬性的時期開始接受進化論知識。由于文化背景、社會環境、生命體驗、認知角度的不同,魯迅接受進化論的興趣點與羅素很不相同,所接受的進化論,雖然屬于理論知識的范疇,但是以混合的狀態存在的,既包括了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進化的知識,也包括了一些非自然科學知識,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非自然科學知識,吸引了魯迅并促使他自覺地整理屬于自然科學知識的生物進化論。
魯迅最早接觸與進化論相關的知識是19世紀末在南京求學期間。1898年11月,魯迅因不滿江南水師學堂“烏煙瘴氣”的學習氛圍和自己所學的“管輪”專業而從該校退學,1899年1月下旬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在礦務鐵路學堂,魯迅不僅較為系統地學習了地質學的相關知識,而且由于礦務鐵路學堂地質學的課本使用的是英國地質學家賴爾撰寫的《地質淺學》(現通譯為《地質學原理》)這部“為生物進化主義奠定了基礎,深深地影響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7]31的著作而接觸到了關于生物進化的學說與理論。《地質淺學》早在魯迅來到這個世界之初,已被翻譯成中文引入了中國。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這篇雜文中就曾指出:“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這一闊得可怕的頭銜……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么,總而言之,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幣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于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赫歇爾)的《談天》,雷俠兒(賴爾)的《地學淺釋》,代那(達納)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里。”[8]325不過,在礦務鐵路學堂學習期間,魯迅雖然下了很大的功夫鉆研《地質淺學》,還“照樣抄訂成兩大本,并把書中精密的地質構造圖也都描摹下來”[9]33,但這部《地質淺學》中所闡述的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知識,并沒有引起魯迅特別的關注。魯迅真正關注生物進化理論并受到震撼,是20世紀初期。這一時期,魯迅讀到了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從這本書中,初步了解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接受了其中關于生物發展進化的唯物主義觀點”[9]40,心靈被深深震撼。魯迅曾在《瑣記》中回憶當時的情景:“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10]305-306從這個時期開始,魯迅不僅自覺地和較為系統地汲取進化論的知識,還以論文的形式整理了進化論的知識并開始頻繁地使用這類知識看待各種社會現象與問題、分析各種理論學說與問題,不斷地創造屬于自己并澤被他人的精神財富。
魯迅接觸與獲取進化論的途徑,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其他人的途徑完全一樣,最初是通過賴爾的《地質淺學》初步了解進化論,隨后通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這部“前半部著重解釋自然現象,宣傳物競天擇;后半部著重解釋社會現象,宣揚優勝劣敗的社會思想”②著作而對進化論的學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較為系統地了解進化論的知識,都不是直接通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接觸并了解進化論學說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1919年才由馬君武翻譯為中文并由中華書局出版,題為《達爾文物種原始》,正式被引進中國。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對進化論產生較為濃厚的興趣,不是因為這種知識是科學,“而是因為它與中國社會政治改革、歷史觀念和文化運動密切相聯,因為它具有了‘宇宙觀’、‘世界觀’(‘道’)的功能”[7]29。雖然,我們不能用當時中國知識界對待進化論的普遍傾向簡單地比附魯迅對進化論的認知,但也不能否認青年魯迅當時對進化論的青睞沒有受到學界這種傾向的影響,更何況,作為主要限于“生物”領域的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誕生之后,在西方知識界迅速擴展為“社會”進化論和進步論,“進化主義像一個腰纏萬貫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樣,資助著一切‘事業’。它具有無限的解釋力,它本身也在經歷著理論上的變遷,不斷衍生出新的理論”[7]25。青年魯迅,作為一位希望“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者和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學子,他不是從純粹自然科學的角度而是從為改造中國社會的角度認知和接受進化論,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不過,魯迅接觸進化論的途徑雖然與其他人一樣,對進化論的認知也與當時中國知識界有相近甚至相同的傾向,但魯迅在介紹、整理進化論時,仍是側重于這種知識的自然科學屬性的。
三、魯迅對進化論知識的介紹、整理與其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的關系
魯迅最早介紹和系統整理關于進化論的知識,都是在日本留學期間。其最早介紹進化論,是1903年撰寫的論文《中國地質略論》,而系統整理進化論則是1907年發表的論文《人之歷史》。魯迅側重的都是這種知識的自然科學屬性,都是依據自己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展開和進行的。
《中國地質略論》是魯迅系統整理關于中國地質狀況的一篇論文,也是魯迅介紹進化論的一篇論文。學界曾有人認為,這是魯迅運用進化論的知識分析中國地質狀況的一篇論文。此說是一種出于良好愿望的誤判,或者說,是一種不了解地質學與生物進化論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不了解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形成的基礎而形成的誤判。從地質學與生物進化論的關系來看,并不是生物進化的理論為地質學提供了思想方法,恰恰相反,是地質學為生物進化論學說提供了證據,特別是地質學所研究的“化石”,更是為生物進化學說提供了“最可靠的證據”。當代中國地質學家戎嘉余曾經指出:“化石是地球歷史的見證者,要了解生物的進化過程,最可靠的證據就是從地層中出土的古生物化石。”[5]8(“化石”這一地質學的概念,魯迅當年將其譯為“僵石”[11]8)。雖然,進化論的思想,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萌芽,后又經過文藝復興及18世紀有所發展,但都主要是以哲學的形式提出的進化學說。關于生物進化的自然科學的理論,是直到18世紀才在博物學家布豐和生物學家伊拉茲馬斯·達爾文、拉馬克等人那里得到了比較系統的發展,而布豐的生物進化的思想,也是從對地球的地質的研究中逐步生成的。“他(即布豐)對地質進行了具體的分期,并推測地球的年齡可能已經長達七萬多年,地球的生物可能在四萬年前就已經出現。這些看法,都有理由使人們把他看成是進化主義歷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如達爾文就稱他為‘近代第一個以科學精神對待物種起源問題的學者’。”[7]1219世紀的達爾文,無疑是生物進化論的集大成者。魯迅曾說:“進化之說……至達爾文而大定。”[12]8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無疑是關于生物進化論的最偉大的著作,而從這部著作的誕生及生物進化論產生的基礎來看,恰恰是賴爾的《地質淺學》給予了達爾文以思想與方法的啟示。“賴爾的地質學肯定地質年代的無限漫長,為物種的緩慢進化提供了時間保證;他根據巖層和化石而得出的地質漸變思想,實際上就等于肯定生物也有一個演變過程。帶著賴爾的《地質學原理》進行環球考察的達爾文,從賴爾那里得到了許多思想和方法上的啟示。”[7]15而從魯迅《中國地質略論》的內容來看,魯迅也不是在運用進化論的知識分析中國地質的狀況,而是一方面整理了關于中國地質狀況的既有知識,即“掇學者所發表關于中國地質之說,著為短篇”,另一方面介紹了既往學者們關于“地球之進化”的知識。“整理”既往學者們關于中國地質狀況的知識是其主要內容,而介紹進化論的知識則是小部分的內容。即使是小部分,魯迅介紹的不僅是關于自然科學的理論知識,與其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的關系也很直接。
在“緒言”中,魯迅說:“地質學者,地球之進化史也”[11]6,直接指出了地質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存在物——地球的進化歷史。這樣的觀點與其關于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現象”的模型信念完全一致。隨后,在第三節中,依據國外學者對地球進化的年代的劃分,陳述了“石類既自少而至多,生物亦由簡以進復”[11]10的發展過程以及國外科學家的各種觀點,包括這些科學家關于地球地質發展分期的觀點和各個時期地球的地質發展狀況的觀點等。這些陳述都是對既有知識的陳述與介紹,屬于關于地球進化的理論知識,如地球成型說、星云說、內部融體說、外部融體說等等。陳述完這些既有知識后,魯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是即造化自著之進化論,而達爾文剽竊之以成十九世紀之偉著者也”[11]10。這里使用“剽竊”一詞,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達爾文《物種起源》依據的各類化石所記載的巖石和生物變化、發展的狀況的“事實”是“造化自著之進化論”,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的理論,不過是直接將這些事實抄錄下來罷了;二是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與既往科學成果,即達爾文之前的其他科學家關于地質變化與生物變化的各種“學理”之間的關系。雖然這個詞語本身具有貶義,但魯迅使用這個詞語,不僅準確地指出了達爾文《物種起源》依據的自然進化的事實與關于自然進化的理論,勾畫出了達爾文的研究成果與既有知識,特別是既往科學家提供的關于地質變化的知識與生物變化的知識之間的承續關系,而且也在思路上連接了自己關于科學是“以其知識”歷探自然現象之奧秘的模型信念。
《人之歷史》作為魯迅系統整理關于進化論知識的論文,與其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的關系,更是密切。也許是因為對達爾文“剽竊”“造化自著之進化論”和其他科學家的進化論不滿,也許是因為魯迅自己接受進化論并受到震撼的著作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也許是因為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通過日本生物學家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和其他日本學者關于生物進化論的著作,如石川千代松的《進化新論》“這才懂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13]821等原因。總之,魯迅雖然肯定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是進化論學說發展的一座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高峰,但對進化論知識的整理,卻不是以達爾文的學說為中心展開的,而是以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的最新生物學理論“種族發生學”為中心展開的。
魯迅整理關于生物進化論知識的基本思路是:“敷張其義,先述此論造端,止于近世,而以黑氏(即海克爾)所張皇者終。”[12]8其使用的資料,據日本學者中島長文考證,主要來自赫胥黎《天演論》、海克爾《宇宙之謎》、石川千代松《進化新論》和丘淺次郎《進化論講話》。其中,取自《天演論》的資料最少,只有兩處;取自《宇宙之謎》的資料最多,占了所有資料的44%;其余的資料均取自日本學者石川千代松和丘淺次郎的著作③。整理的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關于生物個體進化理論的知識,集大成者是達爾文的學說。這部分內容,在生物學上稱為是生物“微進化”的內容,“微進化(又稱小進化)以生物個體為進化基本單位,其差異主要發生在‘種’以下的分類等級,包括基因層面的差異等,微進化是生物多樣性的來源”[5]6。一部分是關于生物種族進化的理論知識,其代表性學說是海克爾的“種族進化論”。這部分內容,在生物學上稱為“宏進化”,“宏進化(又稱大進化)以生物物種或生物類群為進化單位,反映物種的縱向演化,包括生物進化的趨勢,進化中發生的突然出現、輻射、滅絕等”[5]2。魯迅所關涉的進化論知識,都屬于自然科學的理論知識,其整理的準則,也都與魯迅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密切相關。
在整理關于生物個體進化的理論知識中,魯迅主要梳理了瑞典生物學家林奈,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居維葉,德國偉大詩人歌德,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等關于生物進化的學說;在整理關于生物種族進化的理論知識中,魯迅主要介紹并論述了海克爾種族進化理論的內容與意義。在整理這些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知識的過程中,魯迅不僅辨析了這些生物學家理論本身的豐富性、復雜性以及客觀存在的局限性(如林奈、歌德的生物進化的理論),也不僅注意了生物個體進化理論與生物種族進化理論之間的密切關系,而且也注意了生物種族進化理論自身的承續與發展的關系,如,海克爾的生物種族進化理論中具有創意且處于中心地位的觀點“形蛻論”。魯迅在整理中指出:“其律曰,凡個體發生,實為種族發生之反復,特期短而事迅者耳,至所以決定之者,遺傳及適應之生理作用也。黑氏(即海克爾)以此法治個體發生,知禽獸魚蟲,雖繁不可計,而逖推本原,咸歸于一;又以治種族發生,知一切生物,實肇自至簡之原官,由進化而繁變,以至于人。”[12]14魯迅的自述給我們提供了兩個依據,一個依據是,魯迅整理的生物進化論的知識,主要是關于自然,如禽獸魚蟲等發展進化的知識,這些知識都不是具有社會學屬性的知識,而是具有自然科學屬性的知識;另一個依據是,海克爾的“形蛻論”,包括他所提出的關于生物種族進化的理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學說,而是在既往關于生物進化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既往的生物進化理論,一是生物個體進化理論,一是歌德率先提出的生物“形蛻論”,海克爾的生物種族進化的理論,就是以這兩種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為前提與依據而建立的。海克爾生物種族進化理論的創新之處在于,一方面建立了種族發生的進化理論,與個體進化理論在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中形成并立局面,即魯迅在《人之歷史》一文中所說的“立種族發生學,使與個體發生學并,遠稽人類由來”[12]8,另一方面則是以歌德的生物“形蛻論”為中心并有效地完善了這種理論學說。魯迅如此的整理及論述,理順了生物個體進化論與生物種族進化論之間的密切關系,理清了生物種族進化理論本身的承續與發展關系及生物種族進化論在生物學方面的創造性意義,體現了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與其進化論知識的關系,或者說,如此的整理本身就是魯迅關于科學的模型信念的具體化、實踐化。
[1] 魯迅.科學史教篇[M]//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 鮑宗豪.知識與權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達爾文.達爾文的生活信件[M]//宋健.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北京:科學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4] 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M].舒煒光,卓如飛,周柏喬,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5] 戎嘉余.進化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科普大講壇——從進化論到能源未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6] 伯特蘭·羅素.我們關于外間世界的知識——哲學上科學方法應用的一個領域[M].陳啟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7] 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一個新的全能式世界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8]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M]//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9] 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范《魯迅年譜》編寫組.魯迅年譜:上冊[G].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
[10] 魯迅.瑣記[M]//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1] 魯迅.中國地質略論[M]//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2] 魯迅.人之歷史[M]//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3] 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代[M]//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中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鄭宗榮)
① 關于“原型信念”與“模型信念”,請參閱拙文《魯迅的信念系統與知識系統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②參見《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頁注釋30。
③參見日本學者中島長文《藍本〈人之歷史〉》(上、下),滋賀大國文會《滋賀大國文》第16、17號,1978年、1979年。
Lu Xun’s Beliefs About Science Model and Its Evolution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XU Zuhua
Lu Xun’s beliefs on science model can be summed up in his own words, “In speaking of science, it explores the depth and the micro scenes of nature with knowledge.” His knowledge on evolution was a kind of theoret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nature.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se knowledge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modeled beliefs about science, or so far as to say, it was his own ideas on modeled beliefs about science.
Lu Xun; scientific belief; theory of evolution
I210.97
A
1009-8135(2017)05-0076-07
2017-07-05
許祖華(1955—),男,湖北仙桃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魯迅的知識結構及信念的個性特征研究”(14BZW10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