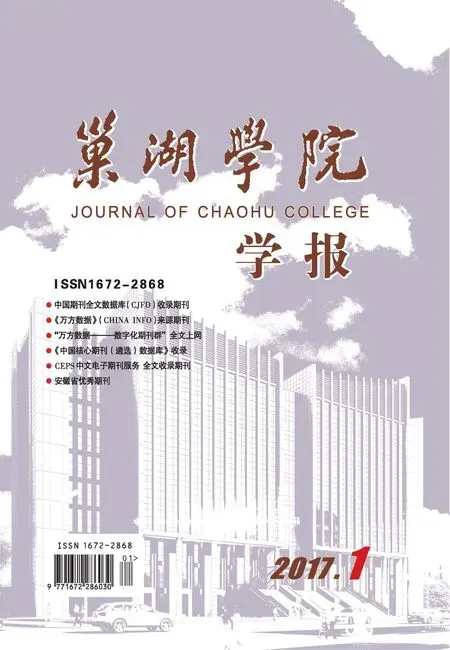史思明父子殺“胡”與政權失敗
陶繼雙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5)
史思明父子殺“胡”與政權失敗
陶繼雙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5)
史思明殺害安慶緒時,連帶屠殺與安慶緒同種族的胡人,史朝義弒父后,同樣有殺害胡人的經歷,這歸根于史思明與安祿山不同種族之故。安祿山是落居東北的西域胡人,故能曲意遷就和拉攏當地各民族,反唐聲勢最為浩大。史氏父子則不同,更強調其突厥及土著的身份,導致種族聯合的破裂,進而促使史朝義徹底覆滅。此鞏固的種族團結的破壞,除一定程度上由政治形勢變化所迫,史氏父子失策當屬主要原因。
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史朝義;種族
安史之亂的失敗,表面上是史朝義殺史思明引起的內訌所致,但深層次的卻是內部種族之間的矛盾。史氏父子殺胡是為清除與安慶緒同種的嫡系,突出自己的突厥種以獲得支持。然而史思明離不開胡人的經濟支持,對胡政策又表現得有些猶豫,但史朝義因儲位爭奪,在殺害胡人方面則走向極端,以胡人和突厥為主干的多民族混同難以維持,整體實力大為削弱,因唐軍施壓和內部反叛的雙重打擊,安史之亂最終走向覆滅。但它的余燼,則生成最終葬送唐朝的藩鎮。
1 安、史種族辨析
史書把史氏父子殺胡作為異種屠殺而突出記載,換言之,如果史氏父子與安祿山同種,也屬胡人,則不會殺胡。然而安、史是否同種一直存有爭議。學界對安祿山族屬的討論發起較早,當從1925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首倡安祿山為康國粟特人起[1],到2005年鐘焓在肯定安祿山為粟特人的前提下更傾向于安祿山已經有較為顯著的內亞化特征止[2],期間八十年,論著不勝枚舉。雖然在安祿山的族屬問題上研究者的意見越來越趨同,但對史思明的族屬爭論仍然激烈。本文就對此問題研究較有影響的兩篇文章,即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和宗教信仰》[3]和上舉鐘焓文,附之以早前較有影響的成果,談談筆者的看法。
榮、鐘二文在談及安祿山時,榮氏強調粟特文化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而鐘焓則認為突厥化對安祿山的影響更為深刻;在對史思明的種族闡釋上,榮氏則確言史思明是粟特人,而鐘焓則捍衛舊說,力主史思明是突厥人。榮氏根據安祿山與史思明同鄉出生的記載認為,“所謂‘同鄉’,實即同出于一個部落的意思。”“史思明從出生到成長都和安祿山有共同之處,‘解六蕃語,同為牙郎’說明他也是個地道的粟特人”[3]。粟特人以經商為長,他們在徙居過程中往往聚集于一處,與他族相隔,因而確實存在“鄉”等同部落的現象,但這能否適用于長期胡化與種族雜居的營州地區,恐難以定論。史載安祿山父為粟特胡種,母為突厥種;史思明與其相反,父為突厥種,母為粟特胡種,安、史二人俱是雜種胡。除史思明的父親入贅妻族外,安姓的“鄉”肯定是種族雜居的地帶,不會是純胡人聚集的地區。史載安祿山繼父安延偃在“族落破”后離開突厥,他的轉移只帶寥寥幾個家庭成員[4],可見這樣的“族”更多與家族同義,難與“種族”甚而“鄉”等同。如果安、史屬同部落,史思明也難免轉移,但史料中未見有史思明轉移的記載,或許正好反映史思明有突厥身份的保護。如此似也可說明安氏部落只是眾多部落雜處的“鄉”中一小部而已。另外,此地的雜種胡甚多,本身即已反映粟特種族隔居的模式在不斷地弱化,種族錯居雜居越發普遍,因此,“雜種胡”的“雜”才能體現出它的應有之義。故而把“鄉”等同部落,并進而得出他們就是同一個種族,在營州地域恐不具有普遍性。至于史思明“解六蕃語”,能否作為其屬粟特人的重要佐證,恐也需依人而論。史思明生于此粟特人較多的雜居地,母親又是粟特人,很容易為粟特人接受和容納,從他和安祿山交好即可為證。對于聰慧的史思明,在此環境熏習之下,掌握這種語言技能實屬可能。陳寅恪論此說:“觀于史思明與安祿山俱以通六蕃語為互市郎,正是具有中亞胡種血統之特征。至其以史為姓者,蓋從父系突厥姓阿史德或阿史那之省稱,不必為母系昭武九姓之史也。”[5]甚為審當。然魏義天說史思明刻有“昭武皇帝”字樣的謚冊已被發現[6],這對史思明的粟特身份似乎更具說服力,后文將涉及之。
安祿山因其母改嫁之后,跟隨安延偃輾轉到嵐州,就此脫離突厥環境而生活在純粟特人家族中,其后與粟特人關系最密當與此有關。《安祿山事跡》載安祿山“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這一心態與其為人繼子恐不無關系,從另一面則反映出他對粟特文化的體察與接受。但一直生活在營州的史思明卻未見其與粟特胡人親密接觸的材料,相反卻有他后來對胡人殺害的記載,而后又被其子錯誤地承繼。另外,鐘焓根據史思明“姿瘦,少須發,鳶肩傴背,廞目側鼻”的長相,比對人種學,認為史思明是更多含有突厥血統成分的雜種人。不過鐘焓在論述安祿山時以為,“至于其后來采用的‘祿山’一名則是來華粟特人常取的漢名,安氏以之為名當有增強麾下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對他的親近感以更好地聯絡感情從而取得他們信任及擁護的政治意圖。”[2]認為“祿山”之名是安祿山為其政治目的特意更改,這實出無據。安祿山之名,是其十余歲時到嵐州后所稱名,必乃父母所改。因而安祿山既不可能自己“以之為名”,也不可能預測到數十年后會成為一個反叛首領,而特地在兒時就給自己起此具有政治意圖的名字。
我們從“胡”“羯”“羯胡”“柘羯”等稱謂上也可發現安、史二人種族的區別。陳寅恪在其論著中認為“羯”“羯胡”“柘羯”等是昭武九姓的專稱;黃永年則認為:“‘羯’已和‘胡’一樣,成為少數民族至少是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7]黃氏無疑是繼承和發揮呂思勉的某些觀點。呂氏《胡考》一文,贊成王國維“西域遂專胡號”的說法,但對王氏的西域人和匈奴人相貌相似一說則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胡之名,初本指匈奴,后乃貤為北族統稱,更后,則凡高鼻多須,行貌與東方人異者,舉以是稱焉。……惟西域人則始終蒙是稱焉。”[8]西域人相貌的獨特才是其始終專此稱謂的原因。巧合的是陳寅恪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在復陳述的信中說道:“赭羯、石羯本為西域民族中一族,實是專名。玄奘作《西域記》是,其義為戰士(《新唐書·西域傳》即用《西域記》文),蓋先由專名而變為公名者。”[9]陳氏是否吸收了王、呂二氏的成果而有此一說不得而知,他緣何未將此說融入其論著中亦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對于黃氏指責的問題,陳氏早有思考。雖然二氏在專名和泛稱之間有某些切合點,但二者分歧仍巨。對于陳氏來說,“羯”本是西域某一民族的稱謂,由于其戰士勇武而逐漸成為西域戰士的泛稱,正好符合其“羯胡”善戰為安祿山所利用的思路。黃氏則不同,把“羯”的泛稱擴大到整個北方少數民族。黃氏可補之處在于,以“羯”或“胡”來指稱北方少數民族的乃漢人或中原人之專用,北方少數民族則絕不會以“羯”或“胡”自稱,在涉及種族之爭時,尤會說清楚。如:
(安)祿山謂(哥舒)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 ”[10]
史思明“因罵曹將軍:‘此胡殺我,我負汝何事,而行此悖逆乎!’”[4]
史思明屠戮胡人后,姚汝能感嘆道:“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4]。于茲三處可知,安祿山自稱為胡人,史思明自認為突厥人,清清楚楚,不容混淆。可見突厥與粟特胡種族界限是分明的。由此推之,北方其他少數民族對自己族類的認識也當如此分明。故陳寅恪目“羯”“羯胡”“柘羯”為昭武九姓專稱,同時將東北地區視為一個胡化地區,后又在其中區分出“雜種胡”的思路,是比較謹慎的。筆者則進一步以為,“羯胡”或“雜種胡”是被泛稱的胡中之“胡”,與被泛稱為胡的其他少數民族是有區別的。
2 史氏父子殺胡考辨
史思明殺安慶緒時,對其部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4]目的是削弱安氏殘余的忠實力量。無獨有偶,史朝義在弒父后,派人回范陽密殺對自己帝位最有威脅的弟弟史朝清,范陽城因此幾度陷入互相殺閥的混亂,所謂“城中相攻殺凡四五,死者數千,戰斗皆在坊市閭巷間。”最后一場激烈的火拼發生在以阿史那承慶和高鞫仁為首的兩派之間。“承慶入東軍,與偽尚書康孝忠招集蕃、羯。”主要以突厥和昭武九姓胡為主;而“鞫仁兵皆城傍少年,驍勇勁捷,馳射如飛;承慶兵雖多,不敵,大敗,殺傷甚眾,積尸成丘。”[11]此“城傍少年”,“應由奚、契丹、高麗、靺鞨、室韋等部落組成”[12]。可見這次內訌已由一般性權利之爭進而演變成不同種族間的仇殺。正因此,“鞫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於是羯、胡盡殪,小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4]軍隊種族的沖突,致使發生屠殺“胡”屬少數民族無辜平民的慘劇:
阿史那從經略軍領諸蕃部落及漢兵三萬人至宴設樓前與如震會戰。如震不利,乃使輕兵二千人于子城東出,直至經略軍南街腹背而擊之,并招漢軍萬余人。阿史那軍敗走于武清縣界野營,后朝義使招之,盡歸東都,應是胡面,不擇少長盡誅之。于是朝義偽授李懷仙幽州節度。[11]
黃永年認為此殺胡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是“從《晉書》卷一○七《石季龍載記》里套來的”,屬于《史通》所說的“貌同心異”論,并引《薊門紀亂》“兩敵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蓋家家自有軍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婦人小童,皆閑習弓矢,以此無虞”為證[7]。黃氏之論難以釋疑以下二點:一,《薊門紀亂》《河洛春秋》《安祿山事跡》都是唐人作品,俱提及此事,不排除作者有相互因襲的可能。但從《通鑒》引《薊門紀亂》《河洛春秋》的文章來看,二書不乏抵牾之處,應該屬于兩個系統。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則在謀篇布局和行文之間都比較縝密,可能反映此書為后起之作,借鑒了前兩部作品,或因此書的價值好過前兩部,促使了前者的湮滅。退一步說,如果三書確實承襲一個版本,三位作者會否同時不假思索一味因襲?姚汝能在談到安祿山和安慶緒的墓志說:“其墓志敘述兇逆,語非典實,所記亦無可取,故略也。”[4]可見姚本人在寫作時是經過審慎考察的。黃氏本人也說姚書 “實是研究安史之亂的第一手文獻”[13],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因而可以否定上面完全因襲的揣測。二,黃氏所引《薊門紀亂》的材料,反映的是城內以前爭斗時對居民的態度,彼時火拼集中在上層,與下層百姓干系不大。但此次則屬于民族間的沖突,連及殺戮對立民族無辜百姓則不致毫無根據。又,《薊門紀亂》時而言屠戮百姓,時而又言與民無涉,這兩條矛盾的記錄同時出現在此篇短文中,作者再無條理恐亦不會疏忽至此。還有,榮新江在《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一文中,對安史亂后河北三鎮的粟特人進行了爬梳,但奇怪的是,從幽州、盧龍二鎮找不出可靠的粟特人存跡的證據,而在魏博、成德這兩個相對南邊的地方卻有很多粟特人在亂后生活的跡象[14]。按常理揆之,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因為之前幽州、盧龍是粟特人聚集較多的地帶,較魏博、成德為多,突然之間痕跡鮮存,實屬可疑。筆者認為,原因主要在于范陽城中對胡人的屠殺和之后史朝義對阿史那承慶部隊中殘余胡人的清理所致。大體情況可能如此,隨著安史勢力南向不斷擴張,營州等原范陽東北地帶的胡人不斷隨之南下,以范陽為中心聚集在幽州治下,經過史氏父子幾次屠殺,此地已不宜胡人繼續定居,遂南下之魏博、成德二鎮或靠近成德的幽州管轄地帶定居。故而,《薊門紀亂》關于殺胡記載大體是可信的。
另外,我們通過對安史軍隊主力構成的考察,也能看出史思明父子殺胡的可能性。關于此問題,討論者也較多。大體有兩種觀點,一是胡人為主力說;二是東北當地少數民族為主力說。從安慶緒失敗,身邊只有“六千”多胡人可見,相比近20萬大軍,胡人在人數上絕非主力,即使由于戰爭消耗亦不當少至如此,所以主力當是東北本地少數民族人民。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忽視胡人的地位:
(安祿山)潛與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寶,計百數萬。每商胡至,則祿山胡服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諸胡于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為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4]。
胡人不僅為安祿山提供經濟支持,在戰場上發揮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兩《唐書》很多時候都用“羯胡”指代安史部隊,正見其作用之大。由此我們不難推想,胡人人數雖少,但由于其與安祿山同種,有著共同的信仰,并為安祿山提供經濟支持,其自身又善戰,無疑是安祿山的心腹嫡系。呂思勉說,“文明人入野蠻部落中,往往為所尊奉。”[8]粟特胡人素質較高也是他們被安祿山倚重的重要因素。正因為粟特人是安祿山的嫡系,人數不多卻享有較高地位,對史思明也多有不服,史氏父子之殺害粟特人則不至子虛烏有了。
3 安、史“帝”位統序與其政權失敗
所謂帝位統序即安氏父子、安史、史氏父子帝位繼承序列的正統性。透過對此問題的考察,可以看到史氏取代安氏的政策措置,及其最終覆滅的原因。
關于安氏父子、史氏父子帝位繼承的紊亂,舊史認為是由安祿山、史思明二人性格暴烈,溺愛他子引起長子不滿造成。鐘焓另辟新說,對史朝義兄弟殘殺事件認為是“史氏家庭內部‘以少子為尊’才引起其兄朝義的疾視,從而招來殺身之禍。 ”其俗與后來的蒙古同,以“幼子守產”[1]。“幼子守產”是蒙古習俗,一般來說是以長妻或嫡妻的幼子繼承大部分遺產。細讀史料,發現鐘焓所論或不符合實情。史載史朝清是史思明的次子,按文意當指第二子,史思明中期降唐的時候,史載其“子七人皆除顯官”[11],可以斷定史朝清并非幼子。《安祿山事跡》記載史思明在回范陽后封妻辛氏為皇后、史朝清為太子。辛氏是否只有史朝清一子難以確定,如果有,肯定比史朝清小,那史朝清作為“幼子守產”將不符合條件,而其被立反是以皇后嫡長子的身份。不過《資治通鑒》卻認為史思明回范陽并未冊封太子,由于對長子史朝義失望,才暗自欲立史朝清。消息不慎泄露,引起史朝義及其黨羽的不滿,導致政變[11]。另外,史朝義發動政變時,史思明的宿衛將領曹將軍向史朝義倒戈投誠,從另一側面反映其集團對史朝義嫡長子合法性的認同。
我們也可以安慶緒殺父作為一個例證。安祿山在稱帝時也未立太子,此時的長子正作為人質被困在長安,后為唐廷所殺,安祿山因此幾得瘋病,不排除安祿山有打下長安立長子的想法。作為次子的安慶緒此時登上了長子的位置,殺父也是由于安祿山對其不滿而屬意他子造成的。如此來說,“幼子守產”在安史集團內并未成為共識。有則著名故事說安祿山在玄宗前沒給當時身為儲君的肅宗行禮,并說不知儲君之意,這似乎符合蒙古不立儲而讓“幼子守產”的說法。相反,史家把這則故事當作安祿山詭譎的一個典型來描寫。換言之,安祿山對儲君、太子之意的認識了如指掌。
相對安慶緒及史朝義,史思明承繼安慶緒遭受挑戰尤巨。史思明在火并安慶緒直至其死,一直努力團結內部不同派別。史載史朝義殺了史思明后,“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征召不至。”[15]除史朝義能力不濟,此事遠因當推至史思明殺安慶緒之際。“思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慶緒,蓋懷祿山舊恩。事臨發,情緒降,眾皆恨之。”[4]對安慶緒剩下的“官健六千余人”,史思明令“令安太清等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史思明只殺其中一半左右,是安氏的嫡系和核心力量。之所以沒有殺完,主要還是出于籠絡胡人的考慮,胡人經濟支持是史思明不可或缺的。故上文所提史思明“昭武皇帝”身份可能即于殺胡后不久樹立的,從他身上有粟特血統來說,于情無不可;安慶緒殺安祿山后,賜史思明安姓,改名為安榮國,故于理亦可。這兩點優勢不僅為其爭取統序的合法性所用,也透露出史思明被迫籠絡胡人的隱情。為此,史思明殺安慶緒后,并未迅速進攻唐軍,而是回范陽老巢休整,前后達七八個月之久。《通鑒》說:“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11]
還有一事值得推敲,即史思明在殺安慶緒后“復稱大燕,以祿山為偽燕”[4],史思明以打著為安祿山報仇的旗號登上帝位,因而他是以安祿山的繼承人自居,而非革命者,那為何稱安祿山所創燕國為“偽燕”,對其進行徹底否定?恐意指安祿山不是“燕”的正宗代表,潛在的意思即暗示安祿山不是突厥人,或更進一步說,安不是東北土著人。如果這個推論成立,恰可以證明史思明與安祿山相反,他是東北人土著的突厥人,是大“燕”國的真正代表,目的是樹立自己土著正統,爭取東北的團結和支持。這可以引一例為證,據《新唐書》卷二一二《盧龍鎮》記載,唐文、武宗年間,盧龍接連發生內亂,后外籍人陳行泰和張絳相繼掌權,吳仲舒說:“行泰、絳皆游客,人心不附。”意指外籍人在此地站立不住。結果如其所料,陳行泰不久被張絳所殺,而張絳旋即又被部下趕走。而作為土著的張仲武接手幽州之后,卻有效地控制了幽州直到他死去。這就是說,土著比“游客”更具控制地方的優勢。史思明恐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才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他在臨死時對史朝義說,“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15]雖然是出于對史朝義個人能力不振的估計,但更透露出對史朝義統緒威望不足,無法掌御大局的隱憂。正如史思明所料,史朝義恰是在統緒方面不自信,終由殺其弟史朝清而導致覆亡。
前已論之,范陽城內發生種族屠殺之事,是以突厥、粟特胡為一派與“奚、契丹、高麗、靺鞨、室韋”為一派的屠殺。最終,失敗的突厥與粟特胡退至城外,沒能出逃的全部死于屠刀之下,城內完全被東北本地勢力控制。原來兩派互相鉗制,現在一派獨大,這對他們選擇降唐或繼續支持史朝義無疑再無掣肘之憂。在妥協之下,城內同意讓史朝義派遣的李懷仙作統帥。然李懷仙乃“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雖為雜種胡,經過幾代,已然本土化了,所以能夠統一城內各本土派系,混成一體。在史朝義逃亡之際,李懷仙選擇降唐而叛之,導致其徹底失敗。若史朝義不屠殺從城內逃逸的胡人,采取其他方式奪回范陽,恢復以前多族共存、相互鉗制的狀態,其敗局恐不至如是。
[1]桑原騭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C]//羽田亨.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東京:京都弘文堂,1926:624-626.
[2]鐘焓.安祿山等雜胡的內亞文化背景——兼談粟特人的“內亞化”問題[J].中國史研究,2005,(1):67-84.
[3]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和宗教信仰[C]//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萃·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762-769.
[4]姚汝能.安祿山事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41-44、12、41-44.
[5]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上海:三聯書店,2001:216.
[6]魏義天.粟特枳羯軍在中國[C]//《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語言、考古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235-240.
[7]黃永年.文史探微[M].北京:中華書局,2000:313-314.
[8]呂思勉.讀史札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177-1179、1191-1194.
[9]將天樞.師門往事雜錄[C]//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13.
[10]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4571.
[11]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7110-7111、7112、7048、7106-7108.
[12]李錦繡.“城傍”與大唐帝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81.
[13]黃永年.唐史史料學[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135.
[14]榮新江.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J].暨南史學,2003,(12):102-123.
[15]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6:5382、5381.
THE DISCUSSION ON SHI SIMING AND HIS SON KILLING THE BARBARIAN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IR FAILURE OF REGIME
TAO Ji-shuang
(Shen扎hen Technological College,Shen扎hen Guangdong 518055)
When Shi Siming killed An Qingxu,he also killed a large number of barbarians who came from the same race with An Qingxu.Shi Chaoyi had the same behavior after he murdered his father,because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belong to different ethnic tribes.An Lushan is the western barbarian in the the northeast of China,and he accommodated himself to won over the local nationalities,so the momentum against Tang governmen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while Shi Siming and his son always emphasi扎ed their Turks and indigenous identity,resulting in large cracks appearing in ethnic joint,thus causing complete failure of Shi Chaoyi.The destruction of consolidation of the ethnic unity mainly results from Shi and his son’s misjudgment in addition to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to some extent.
Anshi Rebellion;An Lushan;Shi Siming;Shi Chaoyi;Race
K242
:A
:1672-2868(2017)01-0100-05
責任編輯:楊松水
2016-10-25
陶繼雙(1981-),男,安徽明光人。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博士后在讀,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