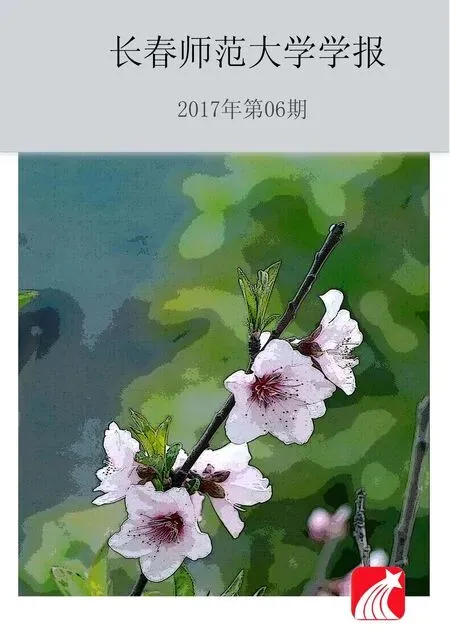論張元濟古籍校勘實踐與成就
顧文杰(長春師范大學圖書館,吉林長春 130032)
論張元濟古籍校勘實踐與成就
顧文杰
(長春師范大學圖書館,吉林長春 130032)
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校勘學家,致力于保護和傳播傳統文化,創辦涵芬樓,廣求善本,并對古籍進行校勘、輯印,付出了畢生心血。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其親自校勘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叢書,為校勘古籍而設置的涵芬樓后來發展成東方圖書館,其對文獻典籍傳承以及中國早期圖書館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張元濟;校勘;古籍整理;成就
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近現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光緒進士,后任職總理衙門,創辦通藝學堂。甲午戰爭后,他積極參與戊戌變法,變法失敗,被清廷革職,至此宦海生涯結束。1902年,他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在主持商務的幾十年時間里,編印教科書、翻譯西方書籍,培養人才,并憑借其深厚的國學根底,編印古籍文獻,大都親力親為,從而形成了獨到的校勘方法,成績斐然,《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代表了張元濟整理校勘古籍的最高成就。張元濟注重圖書文獻的流通利用,設立涵芬樓,其收藏的文獻典籍為商務印書館古籍影印提供了重要版本,是整理校勘古籍的依憑。而后在商務印書館的支持下,涵芬樓發展成規模巨大的東方圖書館,為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開風氣之先。
1 廣求善本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名目各異的公私藏書樓,保存大量藏書。近代以來,戰火頻仍,古籍散佚,商務印書館主要業務之一是古籍影印出版,同一種書在流傳過程中會有多種版本產生,脫、訛、衍、倒的現象也在所難免,給后世讀者的研讀帶來諸多不便。校勘也伴隨著書籍的傳抄逐步開展,校勘圖書的要求很多,校勘者本人的功底是先決條件,而校勘所用母本則是重中之重。所謂“書囊無底,善本難求”,版本是整理古籍的基礎,“初刻”的古籍因錯漏較少、面貌最真而尤為珍貴,但藏書家所藏珍本大都附之秘府,外人難以得見。為了保證編印圖書的質量,張元濟四處訪求善本,這也是設立涵芬樓的初衷。
張元濟出身藏書世家,在版本學上有極深的造詣,自加入商務印書館以后,幾乎不間斷地為編譯所搜尋購買古籍,“先后收買了會稽徐氏镕經鑄史齋、北京盛氏意園、廣東丁氏持靜齋的部分藏書,以及太倉顧氏、浭陽端氏、江陰繆氏、巴陵方氏、荊川田氏、南海孔氏、海寧孫氏、烏程蔣氏、揚州何氏藏書,其中包蘊了不少宋元舊槧和名貴秘籍”[1],辟專室收藏,取名“涵芬樓”。據粗略統計,涵芬樓當時藏有宋元珍本308種,稿本、抄本分別為79種、460種,其中不乏宋刊《六臣注文選》《史記》《南華真經》等珍貴刊本,涵芬樓藏書成為日后校印古籍重要的母本。
為使影印的古籍精準,張元濟以嚴謹的態度對待校勘所用的底本,貴初刻又不拘泥于宋元舊槧,但求所選版本最優,一旦發現更早更好的底本,擇善而從,及時抽換配補。因此除涵芬樓藏本外,還向公私藏書家借書攝照,如影印瞿氏鐵琴銅劍樓、丁氏八千卷樓的典籍,并遠赴東瀛訪書,“飽覽靜嘉堂文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東洋文庫等處收藏的中國珍本秘笈”[2],逐頁拍照,回國后影印成本。不僅如此,散落民間的珍本也在搜羅范圍之內,“張元濟到北京,又從書市收購了一批好書。使《四部叢刊》的母本‘基本上網羅了當時現存的珍本秘笈’”。[3]
張元濟為收集古籍可謂是傾注了極大的精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4],“每至京師,必捆載而歸,估人求售,茍未有者,輒留之”[5],這些努力為《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尋訪到了最佳母本,為接下來的校勘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使校勘質量有了保證。
2 精心校勘
張元濟的國學造詣很深,十分注重讀史,古書流傳已久,訛衍缺脫現象嚴重,故認為“古書非校不可讀”,為使世人更好地閱讀古典文獻,決心重校出版古籍,憑借在商務印書館數十年所聚財力以及涵芬樓逐年收藏的善本古籍,加之影印的各種珍本,張元濟對古籍進行整理精校將近四十年。其對《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輯印和校勘,歷來評價甚高,張舜徽認為《衲史》的出版“從此全史出現了最標準的本子”。
張元濟為校訂《四部叢刊》幾上廬山,以求全神貫注地投入校書工作,如校訂《文始真經》不僅僅采用鐵琴銅劍樓藏本作為母本,而是兼選明萬歷刊本、《道藏》本等六種版本同時對校,并寫下了詳細的校勘記。退休后他更是將全部精力用于《衲史》的校勘,此時的校書工作更加繁重,“終日伏案,尚覺不給,真有愈做愈難之勢,人謂我過于求精,我則見他人之退步。然既已擔任,不能不拼命為之”[5],可見張元濟事必躬親,絲毫不敢懈怠,校書之勤勉,非常人所能及。張元濟校書善從整體把握,考訂精審,并會寫題跋予以記錄。他寫信給傅增湘說到:“承假《南齊書》,去臘校讀一過,撰有后跋。又校閱《魏書》《宋書》《陳書》《齊書》均已竣事,亦各撰有后跋。”[5]張元濟校勘古書功力細密,要求精益求精,一般校過之書還會反復校閱,少則二三遍,多則五六遍,“南齊書兩葉誤記,重勞檢取,不勝慚悚。魏書尚有改照之葉,異日仍須上瀆也”[1]。他不但自己對選定的底本逐頁校訂,同時要求參與校勘的人員將每日的校勘文字和工作日記交給他驗看,由他總校。除商務總廠和東方圖書館被毀的一小段時間外,張元濟幾乎不停頓地校勘各史。胡文楷在《張菊生校書瑣記》中寫道:“菊老校《百衲本二十四史》,逐頁簽名,填注年月日;復樣時,逐頁批可印,然后付印。全史無一頁漏去。”這樣精密的校勘成果便于讀者定是非、辯異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大量的校勘實踐中,張元濟不僅出版了優秀典籍,而且形成了自己獨到的校勘方法。他從各版本中擇選最優,將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方法結合在一起,旁征博引,精審詳校,如《后漢書·郭太傳》末尾有“初,太始至南州”一段共七十四字,錢大昕在《考廿二史異》中認為這是章懷作的注解,是注文并入正文的錯誤。張元濟采取他校的方法,運用紹興本進行校訂考證,得出確是注文而不是正文的結論,不僅證明了前人見解的正確,也訂正了錯亂,對古籍保護和傳播貢獻巨大。
近代學者張舜徽先生將張元濟的校勘方法總結為六例:(一)根據文體結構,以明訛體由形似而誤;(二)參證本書多篇,以明訛體由音近而誤;(三)按之情理,訂正字形之誤;(四)稽之雅話,訂正字形之誤;(五)驗以時制,而知形近之訛;(六)核以經訓,而知形近之訛[7]。其后王紹曾先生對張元濟校勘方法進行細致研究,概括為十五種:“重缺疑、補缺脫、訂錯亂、厘卷第、校衍奪、料臆改、證遺文、辨誤讀、勘異同、存古字、正俗字、明體式、決聚訟、揭竄改、匡前修。”[8]正是對古籍善本的充分利用,對前代校勘學家阮元、黃丕烈等校書經驗的吸取,不斷反復校勘對比,校書的廣度和精準都遠超前代,解決了古籍中大量舛誤,“無論從《衲史》校勘的規模,或者從校勘認真的程度來考察,都是明清以來匯刻全史所未有過的。從校勘成果來說,張先生不僅是王(鳴盛)、錢(大昕)的功臣,他的作用還遠在王、錢之上”[3]。
3 作校勘記
校勘記是古籍校勘成果的表現形式,在廣求善本、找出異文、辨別是非后,將重要內容寫成文字,以求起到“專家以其所得嘉惠學者,則一人之功力可供無窮人之用”的功效。《四部叢刊》的版本價值極高,亦得益于張元濟等人寫下的詳盡的校勘記,其注明了采用何種版本進行對校,并將各版本一一列出,方便了研究工作者。《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價值和學術價值歷來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隨同《衲史》誕生的還有一部鮮為人知的校勘巨著《衲史校勘記》。張元濟學貫中西,博通古今,以其后半生的精力,精校二十四史,在校史的過程中“隨讀隨校,有可疑者,輒存之。每畢一史,即摘要以書于后”[8],遂成校勘記一百余冊,是史部校勘的巨制,由于種種原因,《衲史校勘記》尚未完全出版,張元濟從中摘取164條,單獨排印,名《校史隨筆》,從中可以窺見整部校勘記的重要價值。
《衲史校勘記》的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傅增湘曾說:“君自刊印伊始,獨任校勘之役。每一史成,輒綴跋文于后,臚版刻之源流,舉文字之同異,恒與前賢相發明,或引今時之創獲。其致力之精能,記問之賅博,海內人士,披觀而服之久矣。”張元濟在校勘過程中憑借對古籍各種版本的掌握、小心謹慎的態度,靈活運用各種校勘方法,將現有版本與前人校勘成果相對比,探明源流,并用系統簡明扼要的語言記載述了校書成果,包括對古籍目錄、篇卷、刊刻、版本流傳、文字、內容錯漏、辨偽等多方面進行整理,為后世研究者探究古籍文獻提供了依據。校訂古籍時所用版本幾番斟酌審訂,同一本書選取最佳版本作為校勘時使用的母本,這一過程記錄很多版本學內容,包括古籍版本流傳、體例、避諱、版式、用紙、風格、前人研究成果等情況,以及識別宋元刻本及抄本的方法和經驗,在校勘記中都有所體現。
《衲史》于1937年出齊,而校勘記文字浩繁,尚未整理,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商務印書館再次遭受沉重打擊,無力組織校勘記的出版。令眾多學者扼腕嘆息的是《衲史校勘記》至今尚未出版,有人認為校勘記價值有限,見過這部校勘記的古籍專家顧廷龍先生對此種觀點做出批評:“我認為它還是一部有用的校記,值得印出來。因為當時花很大的人力詳校各本,后人欲知某本作某,一索即得,可節省研究工作的很多時間,亦可考察一字致誤之由。”[8]期待《衲史校勘記》可以早日問世,以備更多讀者研究學習。
4 卓越成就
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幾十年里,使其成為出版界執牛耳者,其中最重要的貢獻莫過于“續古代文化之命,續民族文化之命”,眾多珍本古籍的輯印使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珍得以流傳。“從一九一六年影印《涵芬樓秘笈》(其中有些是排印本)開始,連續輯印了《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道藏》《續道藏》《道藏舉要》《學津討原》《選影宛委別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等大部書。除《學津討原》據清張氏刊本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據文淵閣本影印外,其余諸種,都是精選宋元明舊槧;沒有舊刊本的,也都是經過精選的影鈔、傳鈔、精校精刊的本子。”[1]輯印的這些古籍皆為張元濟親自篩選底本、精心校勘,耗畢生心血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四部叢刊》是在張元濟主持下刊印的大部頭叢書。1920年商務初次影印,收錄古籍323種,2100冊;1934年《續編》印成,收書75種,500冊;1936年《三編》問世,收書71種,不乏宋、元、明善本,價值極高。刊印這部叢書時搜羅了當時所能看到的最佳版本,并且張元濟等人對每種書做了詳細的校勘,續編和三編書后大都附有詳細的校勘記,同時將原本凌亂散失的古籍殘本整理出版,搶救了許多孤本古籍,對文化傳承起了重要作用。
與《四部叢刊》同時進行的是《續古逸叢書》的出版,自1919年出版第一種《宋槧大字本孟子》到1957年《宋本杜工部集》的問世,《續古逸叢書》成為商務印書館歷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一部叢書。該書極其重視版本,全書僅有兩種不是用宋本作為底本,紙墨裝幀頗為精美,是古籍出版史上的佳作。
張元濟耗時最長、貢獻最大的一部書當屬《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其精善的版本、精詳的校勘、精美的印刷受到高度評價。從1930年第一種《漢書》出版,到1937年《宋書》問世,歷時七年全書告竣,共3301卷,820冊。由于每一史都采用不同版本的古書集成,類似于僧人的百納衣,故稱“百衲本”。前文提到張元濟為衲史尋求各種古籍善本作為底本,并精審細校,做兩篇序言,每史后面撰有跋文,隨書而成的校勘記更是精華所在,《衲史》可謂是張元濟一生校勘整理古籍的巔峰之作。
校勘出版古籍文獻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保護。張元濟為校印古籍文獻嘔心瀝血、奉獻一生,既是杰出的出版家,也是校勘學家。王紹曾稱“他是繼清代學者王鳴盛、錢大昕之后,一百二十余年間惟一校過全史,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人”[6]。《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叢書的問世是張元濟用盡畢生精力而獲得的結晶,文獻學奠基人張舜徽先生亦評價道:“過去從乾嘉以來的清代學者們,想做而沒有做,并且不可能做到的工作,他都做到了。在他堅持工作五六十年的漫長歲月里,無論是訪書、校書、印書的工作,都作出了卓著的成績。對于發揚我國文化,開展研究風氣,貢獻至為巨大,影響至為深遠。”[1]張元濟辛勞一生校勘整理古籍的實踐活動極大地方便了后世學者,對學術的貢獻永載史冊。
[1]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鄭州: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
[2]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
[3]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録[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4]張元濟.中華民族的人格[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6]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
[7]中國出版工作協會.中國出版年鑒[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8]王紹曾.張元濟校史十五例[J].文獻,1990(2):162-175.
2017-02-12
顧文杰(1990- ),女,助理館員,碩士,從事圖書館學、文獻學研究。
G270.7
A
2095-7602(2017)06-01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