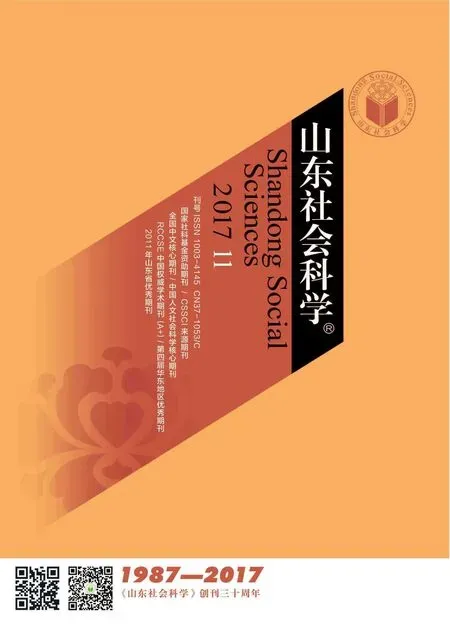再論魯迅的憂患、求索和文學(xué)努力
鄭 春
(山東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再論魯迅的憂患、求索和文學(xué)努力
鄭 春
(山東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魯迅先生離開這個世界80年后,我們益發(fā)感受到他的深邃和可貴,感受到他所獨有的特殊價值和意義,比如濃郁的憂患意識、強烈的開放呼喚以及“拿來主義”的倡導(dǎo)和闡釋等等。魯迅早年留學(xué)日本,為的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七年的海外求索和錘煉,使他最終成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種“別樣的人們”。魯迅以一種超乎世人的眼光和胸懷進行了艱難的文學(xué)探索和創(chuàng)新,他在白話文創(chuàng)作中嶄新的語言實踐,具有極為可貴的示范和引導(dǎo)作用,為中國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
魯迅;憂患意識;開放呼喚;世界眼光;留學(xué)背景
今天我們紀(jì)念魯迅,不僅是因為深深懷念這位為中國文化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偉人,還有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今天的社會建設(shè)依然迫切地需要他,需要他的思想和智慧。在魯迅先生離開這個世界80年后,我們益發(fā)感受到他的特殊和可貴,感受到他的深邃和遠見,感受到他與我們民族命運的息息相關(guān)和血肉相連。我們贊成這樣一個看法,那就是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中確實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以及蘊含在這些著作中的諸多思想,將伴隨我們民族建設(shè)現(xiàn)代文明的全過程。
在紀(jì)念魯迅的日子里,許多學(xué)者一再強調(diào),最好的紀(jì)念還是閱讀,也就是要讀魯迅,讀他的著作,甚至明確提出要通讀原著,我們以為這些聲音都是極有見地、極為重要的。魯迅的作品確實經(jīng)得起歲月的侵蝕和時間的考驗,只要你認真地閱讀,總會常讀常新,并且常常產(chǎn)生新的收獲。在我們民族開啟復(fù)興征程的今天,重讀魯迅,特別是重溫其具有重要啟迪意義的系列思考,感慨良多,收獲益深。我們深切地感到,魯迅先生的許多重要思想穿越歲月的風(fēng)云,在今日益發(fā)顯示出獨特價值和意義,值得高度重視,比如極為濃郁的憂患意識、極為強烈的開放呼喚以及極為堅定的具有引導(dǎo)和示范作用的文學(xué)建設(shè)實踐等等。
一、“我也有大恐懼”
在魯迅對外國作家作品的引進和介紹中,我以為他對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文章翻譯,以及圍繞這些翻譯的有關(guān)思考值得高度重視。1925年前后,魯迅陸續(xù)翻譯了廚川白村的系列文藝評論文章,并將其中大部分發(fā)表于當(dāng)時的《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上。這一年的冬天,他將翻譯文集《出了象牙之塔》結(jié)集出版,對這本不算太厚的小書,魯迅表現(xiàn)出很大的興趣,多次予以高度的評價。
是什么引起魯迅的特別關(guān)注和重視呢?我們發(fā)現(xiàn),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這本書的作者“主旨是專在指摘他最愛的母國——日本——的缺陷的”①魯迅:《〈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譯者附記》,載《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頁。,文章中有諸多揭示日本不足和缺失的尖銳文字,給魯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甚至是引起某種震動。特別是作者敢于正視本民族陰暗面的目光和勇氣,他大為贊賞,認為“作者對于他的本國的缺點的猛烈的攻擊法,真是一個霹靂手”②魯迅:《〈觀照享樂的生活〉譯者附記》,載《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另外,從異國作家對待本民族缺陷時所展現(xiàn)出來的強烈自省意識中,魯迅不由自主地聯(lián)想到自己的祖國,并說“大約因為同是立國于亞東,情形大抵想象之故吧,他所狙擊的要害,我覺得往往也就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指出“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xié),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tài),簡直可以疑心是說著中國。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沒有底力;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著幽魂生活這些話。”*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載《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頁。進而魯迅由此及彼,再次深入中國人的精神天地,并在系列對比中發(fā)掘出中國人精神世界最為缺乏的某些東西。正因為以上這些原因,魯迅在該書由北京未名社正式出版時,特意寫了一篇不短的“后記”。其中就這部譯著的翻譯目的說了一段極為誠懇和痛切的話,表達出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某種苦衷,以及建立在這種苦衷之上的強烈渴望:
我譯這書,也并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中國現(xiàn)在并無“取亂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覺得有刺探別國弱點的使命,所以正無須致力于此。但當(dāng)我旁觀他鞭責(zé)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良藥。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將來要得內(nèi)務(wù)部褒揚的,大抵總覺得一種腫痛,有如生著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大概都不會知道;否則,就明白一割的創(chuàng)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借此先將那腫痛提醒,而后將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
結(jié)合著作品的翻譯和介紹,魯迅指出,廚川白村在書中一再指責(zé)自己的國家沒有獨創(chuàng)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也許是正確的。但公正地看,在植物學(xué)、地震學(xué)、醫(yī)學(xué)等方面,他們還是取得了相當(dāng)?shù)某删偷模苍S是著者為了集中針砭“自大病”的緣故,故意把這些長處抹殺了。說到這里,魯迅筆鋒一轉(zhuǎn),談了一段更為深刻的思考。他說,沒有獨創(chuàng)的文明和卓絕的人物固然是問題,“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zhí)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并不比為新發(fā)戶生存,發(fā)達者更光彩。”*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載《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頁。
語氣蒼涼,意境深邃,從這番清晰的話語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魯迅那顆痛苦的靈魂,一顆對家鄉(xiāng)故國魂牽夢繞、憂心如焚的靈魂,有人稱之為現(xiàn)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正像他本人一再強調(diào)的,自己從事翻譯工作的目的,是用別國的火,來煮自己的肉,他最重要的期待是要驚醒故國那些還在沉睡的人們。他渴望自己的同胞不再昏昏然地自欺欺人,不再盲目地自囚于歷史悠久的自高自大中,不再輕易地嘲笑別人,聊快一時之心。魯迅痛切地指出他從別人鞭責(zé)自己的勇敢中,感到了徹骨的痛。他說,廚川白村所指出的種種膿腫,我們其實也有,甚或更嚴(yán)重。而能夠清醒和明確地指出來,則是徹底割除它的第一步。正因為如此,魯迅極為看重廚川白村的系列作品,不僅親自翻譯了他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這兩本文藝論集,而且一再著文介紹評論,還在中學(xué)的演講中把他的書推薦給學(xué)生們,作為研究文學(xué)可以閱讀的新的三種書籍之一。*魯迅:《讀書雜談》,載《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頁。我們常常驚嘆于魯迅目光的深邃和銳利,這深邃而銳利的目光常常使他的思想能夠立于一個更高的位置,超越世人,看得更深更遠,看到別人難以看到的許多東西,進而產(chǎn)生了深深的憂慮。我們以為,這種憂患意識是魯迅思想最重要的基礎(chǔ),也是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重要的底色,在他的系列文章和小說中經(jīng)常顯現(xiàn)出來。魯迅努力用自己的文字和創(chuàng)作,表達內(nèi)心深處對故土、對同胞最為痛切的追問和最為深情的憂慮。
魯迅多次說過,在自己的內(nèi)心深處,對自己的同胞、對民族的未來有著諸多的擔(dān)心和憂慮,有時甚至是恐懼,某種深深的恐懼。1918年底,魯迅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發(fā)表了《隨感錄三十五》,影響巨大,其中主要談了自己的“大恐懼”:
現(xiàn)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只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但是想在現(xiàn)今的世界上,協(xié)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dāng)?shù)倪M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xié)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為中國人!”于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于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魯迅:《隨感錄三十六》,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頁。
這段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常常被人們一再提及和反復(fù)引用。在這里,敏銳的魯迅作出了怎樣的預(yù)言和判斷呢?他深切感覺到并明確指出了我們民族現(xiàn)實存在的一種危險,那就是中國與世界關(guān)系有可能出現(xiàn)的再度脫軌,因為強調(diào)“特別生長”,進而造成中國與世界的再次隔離,這種狀況當(dāng)然有現(xiàn)實層面的,也有許多是精神層面的。魯迅特別用了“擠出”二字,也就是使中國再次與外部世界對立起來,再次陷入閉關(guān)鎖國、脫離外界、自恃特別、自我陶醉的境地之中,因此而“失了世界”。魯迅認為,這種狀況和導(dǎo)致這種狀況的種種說法、做法、宣傳,以及可能的發(fā)展趨勢,無論以何種旗號、何種面目、何種形式出現(xiàn),都是十分值得警惕的。而且,縱觀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百年以來的歷史,魯迅有一種清醒的認識,那就是這種現(xiàn)象在我們的生存和文化環(huán)境中不僅頗有市場,而且根深蒂固,所以總是能夠以不同的旗號改頭換面一再出現(xiàn),有時遇到適宜的氣候甚至?xí)等怀娠L(fēng),形成可怕的社會潮流。魯迅尖銳地指出,這種現(xiàn)象對我們民族未來的發(fā)展十分有害、十分危險,后果將會十分可怕,所以是最可恐懼的,他稱之為“大恐懼”。閱讀魯迅,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一觀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魯迅思想中值得認真研究的一條重要線索,而且魯迅本人也極為看重。其實,在其苦苦探索的一生中,魯迅始終以堅定的、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清醒面對這種“大恐懼”,與可能導(dǎo)致這種狀況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作堅決的斗爭。他的思想啟蒙、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以及外文翻譯始終圍繞著這樣一個總的目標(biāo),他對國民性的尖銳剖析,對傳統(tǒng)文化糟粕的深度批判,對外國先進文化的大力宣傳、倡導(dǎo)和引進,無不體現(xiàn)著這種抗?fàn)幍膽B(tài)度和艱辛的努力。再讀魯迅,我們發(fā)現(xiàn)魯迅的思想世界有一個核心點,那就是始終不渝的開放呼喚。面對洶涌澎湃的世界潮流,魯迅一再強調(diào),我們一定和首先要做的,是開放,是學(xué)習(xí),是與世界潮流密切相隨、共同進步。我們以為,這是魯迅先生為他的祖國開出的抵御那些“大恐懼”的一劑重要藥方。
當(dāng)然,對于開放,魯迅不僅是熱切呼吁,還有建立在現(xiàn)實基礎(chǔ)上的一系列的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比如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和條件下應(yīng)當(dāng)怎樣開放、應(yīng)當(dāng)以什么樣的心態(tài)開放、開放的步驟與階段,以及在開放運行中應(yīng)當(dāng)力避怎樣的心理和行為等等。尤為可貴的是,他還放眼漫長的中國歷史,充分運用自己豐富的知識積累,為世人描述出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怎樣的開放舉措、開放心態(tài)和開放歷史等等,以為重要的借鑒和例證。魯迅曾經(jīng)用生動形象的文字對比過漢唐兩代以及近代前后的中外交流狀況,然后明確表達出強烈的開放呼喚和熱切期待。他不僅充分肯定了引進民主科學(xué)思潮的歷史合理性和現(xiàn)實必要性,而且強調(diào)繼承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大力弘揚那種可貴的開放精神,并且能夠有謀劃、有力量,把長期以來由于民族危亡的壓力而造成的扭曲的、不平等的被迫開放,轉(zhuǎn)換成主動的進取的,并且富有獨立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開放。魯迅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對一個古老的背負著沉重包袱艱難行進的民族而言,如果重回閉關(guān)鎖國的老路是極容易的,那條老路甚至有著不小的誘惑,但那樣走是絕對沒有出路的。進一步而言,如果只滿足于消極被動的開放,滿足于別人的介紹和輸入,而不能積極主動地去選擇、吸取,不能以自由開放的心態(tài)去參與世界范圍內(nèi)的對話和交流,同樣也是沒有出路的。開放引進,應(yīng)該以更為寬闊博大的胸懷,“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進而培植出自身的創(chuàng)造機能。這就是魯迅的“開放”之夢,是他對于自己祖國和民族未來發(fā)展的期待和建言。
重讀魯迅,我們看到魯迅的開放意識是強烈的,也是一貫、堅定和遞進的。求學(xué)時期,他大聲疾呼沖破一切障礙,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xué)技術(shù)和社會科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五四”前后,走向了激烈的反傳統(tǒng)以及西化的文化選擇;晚年在經(jīng)歷了更多的風(fēng)雨之后,魯迅的思想再次發(fā)生了重大的修正。這種修正不僅超越了留學(xué)年代屈辱心境下的憤激沖動,也超越了“五四”時期徘徊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迷茫,在開放思考及其具體舉措上也產(chǎn)生了一個重要的飛躍,其結(jié)果就是形成了著名的“拿來主義”,這一重要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魯迅強調(diào)對待西方文化,一定要分清“送來”和“拿來”的區(qū)別,因為這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東西,同時也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開放態(tài)度。魯迅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被動地接受“送來”的貨色,而要學(xué)會“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他這樣描繪理想中的“拿來主義”者,他說“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要有力量放手拿來,拿來之后最重要的是會“挑選”,即區(qū)別不同性質(zhì)的東西,采取不同的態(tài)度,然后再根據(jù)不同情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魯迅說:“總之,我們要拿來。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魯迅:《拿來主義》,載《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頁。魯迅的“拿來主義”是20世紀(jì)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思想收獲之一,一方面它是近代以來激蕩中國大地的開放意識的最終結(jié)晶;另一方面,又在相當(dāng)長的時期內(nèi)切實指導(dǎo)著中國現(xiàn)代的開放實踐。直到新世紀(jì)的今天,面對種種新的困難和挑戰(zhàn),當(dāng)需要應(yīng)對更加復(fù)雜的國際環(huán)境時,我們感到魯迅的“拿來主義”及其種種論述,依然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吳組緗先生在論述中國現(xiàn)代作家時,曾經(jīng)專門研究并分析過趙樹理與魯迅的區(qū)別。他說:兩人都寫鄉(xiāng)村,但趙樹理是通過村莊看世界,而魯迅是通過世界看村莊,所以立意高下有別。*參見蕭三匝:《我是劉震云》,《中國企業(yè)家》2012年第19期。我們以為,這番話十分深刻地指明了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史和文學(xué)史上的特殊價值所在,并且認為,是“拿來主義”的開放情懷,使魯迅具有了如此廣闊深邃的世界眼光;而魯迅所擁有的世界眼光,又使他全力倡導(dǎo)的開放呼喚顯示出異乎尋常的特殊意義。
二、“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重讀魯迅,我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是那一代人極為濃郁的憂患意識、開放意識和學(xué)習(xí)意識。我們認為,這一特點的形成與他們的生活和成長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與他長期的海外生活息息相關(guān),也就是說,與他們的留學(xué)背景密不可分。對魯迅而言,海外留學(xué)的特殊經(jīng)歷使他漸漸萌生了對故國現(xiàn)狀的諸多不滿,并開啟了對使命、力量、方法、途徑等大問題的苦苦追尋。換句話說,海外生活的七年,使這樣一位有志向的中國青年,完成了我是誰、我想干什么、我應(yīng)該怎么辦的歷史選擇和跨越。
勃蘭兌斯告訴我們:“有一種要素,外國人比本國人更易于覺察,那就是種族標(biāo)志,也就是德國作家身上使他成其為德國人的那種標(biāo)志。德國人的觀察太容易把德國人和人類視為同義詞,因為他但凡和一個人打交道,心中總免不了有一個德國人。許多令外國人驚詫的特征,本國人往往熟視無睹,因為他早已司空見慣,特別就因為他本人就具備著這種特征,或者就是那個本色。”*[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主流》第2分冊,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3頁。這段話的重要性在于,它講明了現(xiàn)實生活中確實存在的一種現(xiàn)象,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更容易發(fā)現(xiàn)彼此間那種容易被自己所忽視的、帶有民族性特質(zhì)的某些東西。我們以為,留學(xué)生走向世界,其重要意義不僅在于開眼界;還有十分明顯的一點是在不同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在異國文化的啟迪下對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有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認識。尤為可貴的是,他們往往沖破許多長期禁錮自己的意識和觀念,從“古已有之”、向來熟視無睹的東西身上看出了丑陋和黑暗,從過去司空見慣、“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中發(fā)現(xiàn)了落后、局限和種種不合理。魯迅在東京求學(xué)時,“因為身在異國,刺激多端”,和好友的交談往往集中在“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苦苦探討以后的結(jié)論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好聽,標(biāo)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深究其原因,他們認為“當(dāng)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兩次奴于異族,認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9頁。坦率地說,這些觀點并不特別的新穎、深刻或者銳利,也沒有超出那個時代成千上萬留日學(xué)生中流行思潮的范圍。但魯迅的可貴在于,他是以此為基礎(chǔ),開始了更深層次和更有價值的思考,而魯迅最為可貴的啟蒙主義的心路歷程,便由這樣的思考而起步,最后達到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境界。其實,不只是魯迅這樣做,那些年代幾乎絕大多數(shù)的留學(xué)人員,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時刻,都會遇到同樣的情況并且大多在或深或淺地思考著相似或相近的命題,那就是與別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究竟在哪里?為什么別人能夠做到的事情而祖國卻不行?如何才能改變中國,使它擺脫苦難、黑暗、落后的境地?如何才能使我們中華民族成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員?這是留學(xué)生們最為關(guān)注的問題,是他們最為熱切的期待,是那一代人不可逾越的宿命,同時也是留學(xué)生活最深刻的背景所在。許多人之所以歷盡艱辛,留學(xué)國外,就是要尋找這樣一種存在,那種可以真正改變中國的存在,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頁。。
眾所周知,魯迅立志學(xué)醫(yī)與其家庭變故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因而是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的。他后來這樣回憶:“我的夢很美滿,預(yù)備卒業(yè)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dāng)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維新的信仰。”這無疑是一個美好的夢想,青年人的夢想,其核心是為國家、為民眾,也為自己的家人做點什么。然而,在日本留學(xué)的所見所聞,很快淹沒了這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一次課堂上幻燈片的強烈刺激。魯迅曾經(jīng)一再講到那個痛心疾首的畫面,他在海外課堂的畫片上看到“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那是怎樣的一幅圖景啊——一個將要被槍斃的犯人和一堆莫名其妙的看客,“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jù)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頁。那些看客的神態(tài)形象深深地烙在了青年魯迅的心中,“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魯迅:《藥》,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頁。,這是他心靈深處永遠的痛,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這些創(chuàng)痛無疑是促進魯迅思想巨變最重要的因素,他痛苦地認識到,要實現(xiàn)一代人的理想,也就是要救亡圖存、拯救民族擺脫絕境,需要流血犧牲的政治,也需要扎扎實實的科學(xué),但所有這一切有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需要具體的人來做,而且只能和必須依靠頭腦清醒的人去做。因此首要的問題是使中國人去除愚昧、擺脫麻木,也就是說,當(dāng)務(wù)之急是使自己的同胞頭腦清醒起來,也就是要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進行重塑。
立足于這樣的思想變化,魯迅感到從長遠和大局來看,“看病救人”盡管十分實用,但并不是一件十分緊要的事。單純的醫(yī)學(xué)或科學(xué),實際上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中國社會和民眾思想的改革,因此所謂“醫(yī)學(xué)救國”“科學(xué)救國”之類的想法或許只是膚淺簡單、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最起碼不像原來想象的那樣關(guān)鍵、神圣和立竿見影。他深切地意識到,科學(xué)是人的社會行為與理性行為的一種高級活動,重要的不僅是科學(xué)理論本身,而是從事科學(xué)活動的人的素質(zhì),以及造就科學(xué)產(chǎn)生的文化氛圍。救國要先救人,救國必先救人,靈魂畢竟重于軀殼,當(dāng)務(wù)之急是徹底改造人們的奴隸根性,必須找到一條比科學(xué)啟蒙更有效、更可行的途徑。那么,什么是更有效、更可行的途徑呢?魯迅經(jīng)過慎重思考,選擇了文學(xué),他覺得在改造國民精神方面,沒有什么比文學(xué)更有力量了。在隨后發(fā)表的著名論文《摩羅詩力說》中,他用一個形象的“冰之喻”,極為精彩地區(qū)分了“科學(xué)”(學(xué)術(shù)、學(xué)說)和“文學(xué)”(文章、詩)的不同功能,字里行間蘊涵著自己對文學(xué)的獨特理解和熱切期望。魯迅認為,文學(xué)(藝術(shù))離心近,科學(xué)(學(xué)說)離心遠,文學(xué)與學(xué)說不同,“學(xué)說所以啟人思,文學(xué)所以增人感”*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頁。,魯迅認定,要更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文學(xué)是最好的手段。他后來一再回憶道:“我們在日本留學(xué)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的”*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載《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頁。;“善于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dāng)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頁。。他要以文學(xué)之筆來驚醒人、教育人、啟迪人、改造人。至此,魯迅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zhuǎn)折,并且終生對這一根本性的轉(zhuǎn)變矢志不渝,他始終堅信以文學(xué)救人必將有益于他的故國,必將“大補”于中國。
道路的選擇是一個艱難痛苦的過程,但一旦選擇了道路,并明確了自己肩負的使命,魯迅便開始了認真、充分和極具個性特色、傾向性的知識儲備。魯迅在日本留學(xué)七年,除了最初幾年在學(xué)校讀書以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自學(xué)和思考,特別是下定決心棄醫(yī)從文之后,他更是以極大的努力為今后的文學(xué)事業(yè)進行著充分的準(zhǔn)備。據(jù)許壽裳回憶,在魯迅的抽屜里,珍藏著他心愛的書籍,除了唯一一本日本印行的線裝《離騷》外,其余的全都是洋書。這種強烈的外文閱讀傾向,正是他理想目標(biāo)的清晰表達和苦苦求索的真實寫照,而他的數(shù)篇文言論文《人之歷史》《科學(xué)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則是這種努力的總結(jié)和展現(xiàn)。在這些文章中,魯迅尖銳地指出故國所有問題的關(guān)鍵癥結(jié)及突出表現(xiàn)集中于默如荒原,浩蕩華夏沒有聲音,特別是民眾不能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因為沒有外部環(huán)境,沒有內(nèi)在條件,甚至作為個體的存在基本沒有了這種能力。多年以后,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無聲的中國》,依然號召“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那么,如何打破這無聲的中國,他明確提出一個做法,就是要“別求新聲于異邦”,也就是從異國他鄉(xiāng)尋找到新的先進的聲音,并且特別舉例說,“新聲之別,不可究詳;至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隨后他以極大的熱情介紹了這一詩派的諸位重要人物,諸如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等。隨后,他把目光轉(zhuǎn)回自己的祖國,如此設(shè)問:“求之華土,孰比之哉?”“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魯迅:《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頁。最后,魯迅用詩一般的語言描繪出他心目中的“戰(zhàn)士”及其“理想”:“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quán)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fù)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具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魯迅:《文化偏至論》,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從以上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逐漸以一種開放胸懷和世界眼光,審視時代潮流和歷史發(fā)展趨勢,有選擇地吸取異質(zhì)文化的優(yōu)秀成分,重建一種“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現(xiàn)代文化的“新宗”,以達到啟蒙救國的目的,這是魯迅留學(xué)歲月深思熟慮之后提出的理想目標(biāo)和建設(shè)途徑。從這些頗具遠見卓識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魯迅此時的思想已經(jīng)大大超越了同代人,從而率先進入了現(xiàn)代文學(xué)和文化批評的嶄新視野。這些論文涉及面極為廣泛,深深淺淺地包含了諸多文化領(lǐng)域和學(xué)科范圍,充分反映了青年魯迅求學(xué)階段艱苦的努力和廣博的學(xué)識,其知識面之寬、視野之廣,足以見出外國文化思潮對他多方面的影響。正因為有這種超前的充分的思想準(zhǔn)備,才能使他在后來參與“五四”文學(xué)革命的創(chuàng)作中,出手不凡,幾為絕唱;也使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強大的思想力量,先聲奪人,對整個文壇產(chǎn)生極為強烈的震撼。
總之,“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是魯迅的求學(xué)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軌跡,更是使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在日本留學(xué)的七年,他學(xué)到了許多終生受益的東西,更為關(guān)鍵的是,他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了重要的知識吸收和儲備,在選擇、吸收、錘煉和提升的基礎(chǔ)上,最終形成了自己極為可貴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底色。令人感嘆的是,早年魯迅留學(xué)日本,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尋找“別樣的人們”;而經(jīng)過七年的海外求索和錘煉之后,他自己最終成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這樣一種“別樣的人們”,其突出標(biāo)志便是貫穿其一生的憂患意識、開放呼喚和學(xué)習(xí)渴望。
三、“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重讀魯迅,我們還想特別強調(diào)一點,魯迅的重要性,或者進一步說,魯迅之于今天的重要價值,不僅在于他的思想高度和敏銳,諸如站在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發(fā)出系列震撼人心的思考和論斷,更在于他基于這種思考之上的堅定實踐和切實行動,在于以一種開放的姿態(tài)和胸懷進行的不屈不撓的艱難探索。在這些探索和嘗試所取得的珍貴成果中,我們以為,許多方面直至今天依然有著重要啟迪意義,比如思想探索領(lǐng)域極為深刻的民族反省、文學(xué)建設(shè)領(lǐng)域重要的規(guī)范性和引進性的探索實驗,再比如對新文學(xué)開創(chuàng)時期諸多問題和弊病的發(fā)現(xiàn)與指正以及文學(xué)翻譯方面“硬譯”的嘗試等等。本文想重點談一下魯迅在白話文創(chuàng)作方面嶄新的語言創(chuàng)新和實踐。
魯迅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建設(shè)的突出貢獻,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在文學(xué)語言方面,也就是在文學(xué)語言的創(chuàng)新實踐方面。當(dāng)年,胡適在舉起“文學(xué)革命”的旗幟、大力倡導(dǎo)白話文運動時,一個重要原因是認定文言死了。他曾說過一段具有標(biāo)志意義的話:“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不能產(chǎn)生活文學(xué)。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xué),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chǎn)生了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xué)的工具的。”*胡適:《逼上梁山》,載《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建設(shè)理論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9頁。胡適的想法是明確的,為了發(fā)起一場希望的運動,話也說得很強勢、肯定和斬釘截鐵,但白話能否真的擔(dān)當(dāng)起這個責(zé)任呢?許多人卻是懷疑的,包括胡適自己。所以盡管他一再呼吁新的作家應(yīng)當(dāng)盡力運用手頭一切可能獲得的白話去創(chuàng)作,盡管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殫思極慮、努力為之,卻也不敢對這項事業(yè)的前景抱有太大的期望,他甚至把寫一手“純粹的白話文”的希望,寄寓給了未來的人們,他原以為至少“要在三五十年內(nèi)替中國創(chuàng)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xué)來”。但實際上,白話文的崛起和興旺遠超人們的預(yù)期,前后大約只用了四五年的時間,白話文已在國內(nèi)普及開去,而且一批優(yōu)秀的帶有示范性的文學(xué)作品也以嶄新的姿態(tài)登上文壇,這其中魯迅的創(chuàng)作無疑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
魯迅對白話文有著很深的感情,他曾經(jīng)用極為形象的語言,生動表達過白話文的極端重要性。他說,白話文以前的中國,由于文言的僵死,中國人長期處于既聾且啞的悲慘的文化狀態(tài),故稱為“無聲的中國”。而胡適等人大力提倡的白話文運動,重要的意義之一是使一個“無聲的中國”逐漸變?yōu)橐粋€“有聲的中國”,將一個“瀕臨死境”的文化“復(fù)活”了過來。因為這個原因,魯迅曾發(fā)誓要傾盡全力,捍衛(wèi)白話。他在《二十四孝圖》一文中,曾以決絕的口氣兩次重復(fù)這樣的話:“只要對于白話加以謀害者,都應(yīng)該滅亡!”他將反對白話文的人稱為是“現(xiàn)在的屠殺者”:“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xiàn)代人,吸著現(xiàn)代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誣蔑盡現(xiàn)在,這都是‘現(xiàn)在的屠殺者’。殺了‘現(xiàn)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魯迅:《隨感錄五十七·現(xiàn)在的屠殺者》,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頁。正是懷著這樣的情感,為了“有聲的中國”和“中國的聲音”,魯迅和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一起,不僅是舉旗幟、喊口號,而且艱苦地進行著新文學(xué)語言文字的規(guī)范、提高和錘煉工作。他們一方面要倡導(dǎo)白話文,捍衛(wèi)白話文;另一方面要身體力行,盡全力提升白話文學(xué)的整體水平,進而為其真正立足并走向興盛奠定重要的基礎(chǔ)。面對種種的懷疑和指責(zé),他們相信,脫離了古文的大眾口語,不僅會,而且能夠創(chuàng)造出不亞于文言的別一類的優(yōu)美的文字世界。
理想明確,信念堅定,但具體究竟應(yīng)該如何去做呢?“死文字不能產(chǎn)生活文學(xué)”,但活文學(xué)怎樣才能真正產(chǎn)生和創(chuàng)造出來呢?面對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和重重的困難,魯迅等一代學(xué)人進行了艱難困苦然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和探索。比如充分地向口語和方言學(xué)習(xí),高度重視“活著的白話”。魯迅曾經(jīng)借用高爾基的比喻,說大眾語是毛坯,加了工是文學(xué),并認為這種說法是非常中肯的。*魯迅:《做文章》,載《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頁。他明確表示:“我們要說現(xiàn)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魯迅:《無聲的中國》, 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頁。他說“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里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魯迅:《寫在〈墳〉后面》,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頁。在《門外雜談》一文中,他舉例說:“方言土語里,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里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們發(fā)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與文學(xué),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魯迅:《門外文談》,載《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頁。他特別舉出傳統(tǒng)文學(xué)作品中那些生動鮮活的例子,強調(diào)從舊小說、民歌、故事以及戲劇中吸取剛健、清新的表達方式。他認為,“《水滸傳》里一句‘那雪正下得緊’,就是接近現(xiàn)代的大眾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魯迅:《“大雪紛飛”》, 載《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頁。在《門外文談》中,他進一步指出:“大眾并無舊文學(xué)的修養(yǎng),比起士大夫文學(xué)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xué)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xué)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xué)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jīng)說過了。現(xiàn)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里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zé)罰,從此不再寬縱了──‘那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xué)家做得出來么?”*魯迅:《門外文談》,載《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頁。再比如對域外詞語、外國語法的引進學(xué)習(xí),有學(xué)者曾專門分析研究了《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的兩篇文章: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和周作人的翻譯《貞操論》。發(fā)現(xiàn)不僅有域外文法規(guī)范的影響,如“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等等;而且外來詞的吸收也是驚人的,《貞操論》總共3000多字,運用外來詞語竟達70多次,其中包括社會、精神、權(quán)威、人格、關(guān)系、批判等。對此,魯迅自己有這樣一段闡釋:“竭力將白語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yīng)支持,因為講話尚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眾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魯迅:《答曹聚仁先生信》,載《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頁。應(yīng)當(dāng)看到,魯迅所倡導(dǎo)的對“新字眼、新語法”的借鑒和應(yīng)用,意義是巨大的,這種對國外詞匯語法的充分吸收,不僅帶來了新鮮的文化信息,而且極大地提高和增強了新文學(xué)語言的表達能力。
總之,向口語學(xué)習(xí),向方言學(xué)習(xí),向民間文學(xué)學(xué)習(xí),也向域外詞語、外國語法學(xué)習(xí),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吸收和應(yīng)用,為了形成一種屬于自己也屬于中國的嶄新的語言表達方式。對于自己的語言創(chuàng)造和實踐,魯迅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概括和評論,他說:“沒有法子,現(xiàn)在只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的,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里去。”*魯迅:《關(guān)于翻譯的通信》,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頁。魯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小說語言基本上就是以活的民眾口語為基礎(chǔ),博取古今,兼收中外,融會雅俗,創(chuàng)新升華而成的。正因為如此,閱讀魯迅作品,讀者往往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的語言不僅具有一種鮮明的特色,而且在寫人狀物時顯示出一種白話文中難得的精確、凝練和靈秀。它完全有別于同一時期的許多新文學(xué)作品,不僅沒有當(dāng)時常見的那些為人詬病的毛病,而且?guī)缀跬耆饤壛肆餍杏谛挛膶W(xué)作品中的所謂的文藝腔調(diào),因而令人耳目一新,并逐漸發(fā)展形成了一種個性鮮明的魯迅風(fēng)格,接近和達到一種難得的自由奔放的藝術(shù)境界。正因為這一特色,我們說,魯迅的努力不僅為現(xiàn)代小說語言持續(xù)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而且用實際例證昭示了這種發(fā)展可能具有的廣闊美好的前景。歷史告訴我們,盡管魯迅沒有最早發(fā)起和倡導(dǎo)白話文寫作,但他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和作品有力捍衛(wèi)和弘揚了這一影響深遠的運動。魯迅后來總結(jié)這段歷史時也說過,真正顯示了文學(xué)實績的,是自己的小說。當(dāng)胡適還在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理論學(xué)術(shù)的層面,為白話文的生存和意義苦苦證明的時候,魯迅已用自己絕美的文字證實了它動人的存在。胡適所期待和呼喚的那種新式文學(xué),是在魯迅的筆下變成現(xiàn)實的,并最終結(jié)出了頗為豐碩的果實。
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作家,在西風(fēng)東漸、文化交融的大環(huán)境中,將東西方不同的敘述方式,較為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努力實踐和創(chuàng)造出一種具有獨特風(fēng)格的新的語言風(fēng)格和新的表達方式。這一嶄新的語言實踐,不僅為現(xiàn)代漢語的創(chuàng)新進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在相當(dāng)程度上為其規(guī)范化和現(xiàn)代化顯示出某種示范意義,而且對此后相當(dāng)長的時期內(nèi)我們民族文學(xué)語言的發(fā)展建設(shè),產(chǎn)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響。極具藝術(shù)感悟力的學(xué)者李長之,在當(dāng)時就敏銳地把握到魯迅創(chuàng)作的特殊意義,真切體會到了魯迅作品中的這種獨特的美,他一再撰文指出“魯迅的筆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別好”,“他的文字本身也表現(xiàn)出一種閑散、從容,而帶有節(jié)奏的韻致……這是多么美的散文!文字的本文從容,有種從容的美,不必是敘述的事情從容”。*郜元寶等編:《李長之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讓我們摘取一段魯迅的文字,具體了解一下李長之所說的這種從容,并欣賞和品味一下魯迅作品所獨有的文字之美。在其著名小說《故鄉(xiāng)》中,結(jié)尾有這樣一段,作者抒發(fā)了再別故鄉(xiāng)時的情思和期待:“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故鄉(xiāng)》,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頁。這段文字流傳甚廣、影響較大,而且也極具代表性。無論是寫景還是抒情,無論是描述還是議論都達到了相當(dāng)?shù)母叨龋瑢懢凹兠溃h論精粹,文風(fēng)自然,意蘊深長,充分顯示出這種新型語言風(fēng)格的美麗、靈性及其令人神往的藝術(shù)魅力。能形成這樣一種極具魅力的文學(xué)語言,無疑是現(xiàn)代文學(xué)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所以文學(xué)史家有這樣的公論:中國現(xiàn)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如果說中國新文學(xué)的先驅(qū)努力掀起“文學(xué)革命”,是大聲呼喚一個新時代的話;那么,這種極具魅力的新的文學(xué)語言的初步成熟和廣泛應(yīng)用,則標(biāo)志著新的文學(xué)時代已經(jīng)來臨。“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我們以為,魯迅的這種倡導(dǎo)和實踐,對今天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實踐,依然有著重要的啟迪和指導(dǎo)意義。
2017-04-12
鄭 春,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xiàn)代作家留學(xué)背景再研究”(項目編號:11BZW090)的階段性成果。
I206.6
A
1003-4145[2017]11-0039-08
(責(zé)任編輯:陸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