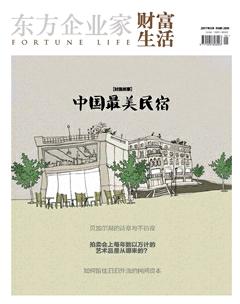約翰·伯格:最好的藝術寫作者
亂石小熊
剛邁進2017年,著名的英國藝術史學者、藝術批評家、作家,約翰·伯格便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享年90歲。作家珍妮特·溫特森在推特上惋惜而沉痛的表示:“約翰·伯格走了,他是這個日漸枯竭世界的能量源泉。”伯格的去世,引起了英國藝術界、文學界的集體追思。《每日電訊報》曾經這樣問,“今日,還有誰能如約翰·伯格一般,這樣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看待藝術,看待藝術與時間、與景觀、與社會生活呢?”
璀璨的一生
璀璨約翰·伯格1926年出生于英國倫敦,而后進入牛津的圣愛德華學校念書。他父親在一戰時候做過步兵軍官,他則于1944至1946年在英國軍隊服役。退役后入切爾西藝術學院和倫敦中央藝術學院學習。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畫家身份開始其個人生涯,于倫敦多個畫廊舉辦展覽。1948年至1955年,他開始為倫敦著名雜志《新政治家》撰稿。他的左翼人道主義傾向,以及大膽而犀利的論斷,使其迅速成為英國頗具爭議性的藝術批評家。而在當時的西方世界,他更因“疑似信奉馬克思主義”被視為異類。
除了藝術批評領域外,伯格在寫作、繪畫、電影方面也頗有建樹。
1958年,伯格發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我們時代的畫家》,講述一個匈牙利流亡畫家的故事。此書揭露的政治秘聞,以及對繪畫過程細節的刻畫讓他的名聲更勝。緊接著伯格發表《克萊夫的腳》和《科克的自由》兩部小說,展示英國都市生活的疏離和憂郁。1972年,他的電視系列片《觀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時出版配套的圖文冊,遂成藝術批評的經典之作;同年,小說《G.》,一部背景設定于1898年的歐洲的浪漫傳奇,為他贏得了布克獎及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
在70年代,伯格與瑞典導演阿蘭·坦納合作了幾部電影。由他編劇或合作編劇的電影包括《蠑螈》、《世界的中央》等。進入80年代,伯格創作了《不勞而獲》三部曲,包括《豬玀的大地》、《歐羅巴往事》、《丁香花與旗幟》,展示出歐洲農民在今日經濟政治轉換過程中所承受的失根狀態與經歷的城市貧困。
伯格還撰寫了大量有關攝影、藝術、政治與回憶的散文,展示出寬廣的視野和卓越的洞識。這些文章收錄于多部文集,較有影響力者包括:《看》、《約定》、《抵抗的群體》等。
切下維納斯頭的人
約翰·伯格走進一家畫廊,用刀割破了波提切利的油畫:“過去的藝術已不復存在了。”
這位頭發蓬亂,眼眸閃爍的評論家說,“它喪失了自己的權威。代替它的是一種新的圖像語言,而今,重要的是如何運用這種語言,為何而用。”
以上這個畫面,出自于1972年,約翰·伯格在BBC播出的電視系列片《觀看之道》,它改變了整整西方一代人觀看藝術的方式。
在同一年出版的《觀看之道》一書中,約翰·伯格初步建構了一整套現代人的觀看體系。全書由四篇主題不同的文字組成:“藝術和政治”、“女性作為觀看的對象”、“油畫自身的矛盾”以及“廣告與資本主義白日夢”。從藝術作品呈現給觀者的視覺感受入手,深入分析了藝術與性別、政治、經濟等緊密的聯系。此書問世40年來,激起的爭論歷久不衰,其觀點影響了幾代人,成為這一領域的常識。
約翰·伯格認為,“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原作的價值是市場價格,而現在的復制手段也摧毀了藝術的權威性,給了人們利用的機會,藝術作品出現在不同的領域,作用都是不同的,而“任何時代的藝術都是以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服務的”,政治竊取了藝術本身的意義,也改變了歷史的真實。
在油畫中,繪畫不僅表現了階級斗爭的歷史,它也揭露了男女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女性是用來觀賞的,并被視為物品。她們被男人欣賞,同時也要習慣于自我欣賞——總是要注意她們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外表。女性在畫中被作為一個被觀看的景觀而存在,而觀看者則是畫的擁有者。畫中的女性總是面朝著觀看者,并以其姿態取悅其收藏者,并引起他的欲望以及幻想。
在《觀看之道》中,伯格教導人們,油畫是對階級地位的認可,風景畫是為領土擁有者創作的,“你畫一個裸體的女性,因為你喜歡這樣看著她”。同名平裝書隨后出版,其中對藝術和社會關系直截了當的陳述、對古代大師油畫朦朧的復制品,以及當代的攝影作品集結于這本書中,使該書很快成為暢銷讀物,風靡全球。以及當代的攝影作品集結于一本書中,該書很快成為暢銷讀物,風靡全球。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很多學生通過牛津和劍橋的藝術、文學小冊子認識這個世界的文藝傳統,而伯格的出現仿佛是“真理的大爆炸”。《金融時報》的Jackie Wullschlager認為,伯格解開了高雅藝術的神秘外衣,代之以平凡生活的包裝,證實一幅偉大的作品并不需要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也可以與公共的價值觀并存。而今,在我們閱讀一幅繪畫時,也不會忘卻考察其社會和政治背景,而在那個年代,伯格的立場卻是革命性的。從羅伯特·休斯到溫蒂修女,此后的藝術評論家無不受到伯格的影響。
由于系列片中出現了數百幅繪畫和廣告,因為這些作品的版權限制,伯格的系列片無法制成DVD發行。而今,英國電影學院在《觀看之道》播出40周年之際完整播放4集30分鐘的系列劇,同時還將舉行相關會談,重新審視他帶給人們的新思路。
從藝術到廣告,同樣需要觀看之道
已故知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曾說:“在當代英語作家中,我奉他為翹楚;自勞倫斯以來,再無人像伯格這般關注感覺世界,并賦之以良心的緊迫性。他是一位杰出的藝術家與思想者”。因而,他的觀看之道并不局限于藝術,更是對引導大眾消費的廣告有著非同一般的見解。
今天,我們對這些影像的訴求,已經習以為常,因為甚少注意到其整體的影響。一個人,出于特別的興趣,或許會注意到一個獨特的影響或信息。可是我們接受廣告影響的整個體系,卻猶如接受其厚重的某個因素。“譬如,這些影像屬于瞬間卻指向未來,因而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效果,我們十分熟悉這種效果,也就變得視若無睹。通常正是我們與影像擦肩而過——在步行、旅途、看書之時;在電視熒屏上,情況則有所不同,但即使在那時,理論上,主動權仍操在我們手中——我們可以挪移目光,調低音量,煮杯咖啡。然而,我們人有這種印象:廣告影響不斷在我們身邊掠過,好像馳向遠方終點的特快列車。我們是靜態的,廣告卻是活動的——直至報紙離手、電視節目繼續播放或舊海報被覆蓋。”
在伯格看來,廣告關注的是人際關系,而不是物品。它許諾的并非“享樂”,而是“快樂”——由外界判斷的快樂。這種被人羨慕的快樂就是魅力。因而,在談論廣告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回過頭去想,廣告和油畫都是某一階段精神生活的衍生物,有沒有異同點。
然而,油畫和廣告之間的延續關系遠比“引用”具體畫作的歷史深遠。廣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油畫語言。廣告用同一種腔調描述相同的東西。有時候,兩者看上去確是難分彼此,簡直好像在玩“障眼法”游戲,把酷肖的圖像或圖像細節排列在一起。然而,這種延續關系的重要性,不在圖畫精確對立的層面上,而在運用的各套符號層面上。把本書的廣告和油畫形象作一比較,或拿起一本畫報,或步入一條繁華的購物街去觀看櫥窗中的陳列品,然后翻閱一本有插圖的博物館目錄,并注意這兩種媒體所傳達的信息何其相似。理應對這一現象進行一個有系統的研究。在此,我們只能指出兩者的設計和目的有一些極為相似之處。
伯格這樣寫道:廣告形象往往借助雕塑或者繪畫,以增強廣告信息的吸引力或權威性。鑲上畫框的繪畫,市場掛在商店的櫥窗里,成為展品的一部分。藝術是富裕的標志:它屬于美好的生活也是世界賜予富人的裝飾品。可是藝術品也隱含著一種文化權威,一種尊貴乃至智慧的形式,凌駕于任何粗俗的物質利益之上。
批評主義的獨特藝術
伯格的藝術批評理論的獨特,因為它是一針見血和詩歌的混合體。他的《觀看之道》是克拉克《文明》的左翼、民粹主義版本。這兩部系列片盡管相隔只有3年時間,但它道出了英國文化一個巨大轉變、擴展。克拉克是英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史學家,他是既有審美規范的忠實捍衛者。1933年時30歲的克拉克成為英國國家畫廊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館長。1968年全球青年人群情激昂之時,克拉克輾轉于莊園、圖書館厚厚的牛皮案卷中搜尋拍攝線索。《文明》是歐洲中心主義、個人主義的,它對現代性視而不見。
如果說,克拉克是花園最后的看門人,那么伯格就是那個砸爛籬笆、破壞草坪的人。克拉克在“裸體”章節中討論了古典主義的理想形式,伯格則通過魯本斯筆下《帕里斯的審判》探討了男性看待裸體女子的深層想法。“男子重行動而女子重外觀。男性觀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別人觀察。”當克拉克在“藝術中的風景”中在托馬斯·庚斯博羅的《安德魯夫婦》營造的細致美景中流連,伯格看到的是“領主對于環繞他們土地的態度在他們的姿態和表情中清晰可見”。而今我們對這樣的評論已經習以為常,但在1972年,這是非常先進的思想了。
在八十歲高齡的時候,伯格仍在孜孜不倦地寫作,他說:我認為一個寫作的人,應該勤于見證身邊正在發生的重要事情;即使書寫所立即產生的力量,可能看似微不足道、或一時被人忽略,但不要顧慮這些,還是要寫。“書寫”有著一種非常潛沉的生命,它蓄積著能量,在某個時刻,會對讀者產生一些微小或不小的改變。
一個在文學史、繪畫評論史上留下精彩一筆的人物,無論他是離開與否,他的精神和思想會繼續影響更多的人,也許這也是約翰·伯格本人樂于看到的場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