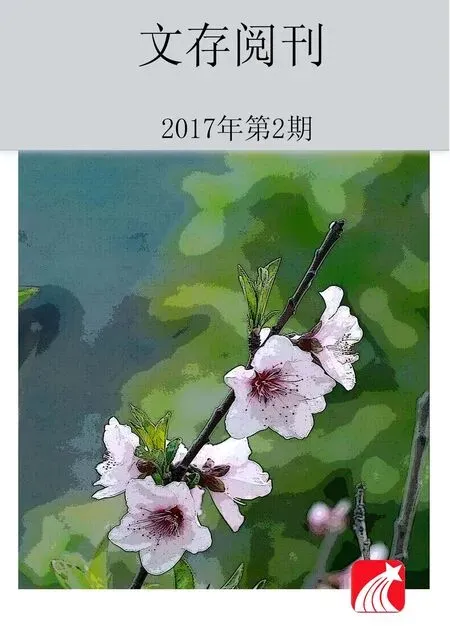1938年 依然行走的沈毅
汪國華
1938年 依然行走的沈毅
汪國華

1938年沈毅踏實的腳印
1938年,艱難中的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的第二年。這一年,在經歷了南京失守的苦難后,中國軍民浴血奮戰,取得了臺兒莊戰役最后的勝利,進行了凇滬會戰、武漢會戰,張揚了中國軍民不怕犧牲,保衛祖國的民族精神,而廣州保衛戰的失利,使中國的戰略物資只能假道第三國運來。但總體局面向著抗戰的相持階段邁進。
1938年,對于沈毅來說,是她更加奮發的一年。終身不嫁的沈毅,自1913年回到老家定海擔任定海縣立第一女子學校的校長開始,就把自己交給了定海的教育事業。這一年,她根據前些年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及日本、菲律賓等地考察學習,繼續著對教育方法和學制進行改革,創辦桑蠶、工藝美術班和三年制的師范講習所;開辦民眾夜校,使不少無力上學的青少年得到就學機會。她啟動了編寫學校本教學綱要和教材的教學革新。
1938年3月8日,為紀念國際婦女節,定海縣婦女聯合會在民教館舉行熱烈的紀念活動,一百余人參加。作為婦聯會主席的沈毅主持紀念活動,并作了婦女節歷史介紹,然后請陳縣長等作了抗戰的演講。1938年3月16日,定海抗日自衛會召開成立大會,她被選為抗衛會的委員,并為抗衛會財務委員會委員,同時兼任抗衛會救護工作隊隊長。5月22日,在定海縣戰時文化推進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沈毅又被推定為輔導組主任……每一個職務都是一項工作。她帶領定海婦女界、教育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她為定海的發展繁榮,全身心投入到各項事業中,廢寢忘食,奮不顧身,深受定海社會各界的崇敬。
1938年,沈毅走過了一個甲子,邁過了生命的第60個春秋。3月28日,是她的生辰,學生和親朋紛紛前來,要為她開辦祝壽慶宴,她以“時事多艱,海氛未靖”堅決推辭,把那些壽禮禮金捐給了學校建造學校大禮堂。學校師生和親朋堅持要給她搞個慶祝儀式,舉行游藝大會,沈毅見師生之意不可拒絕,于是她便借此機會,籌劃抗日宣傳。3月28日下午1時開始到晚上,學校的禮堂擠滿了群眾,而經沈毅指導的游藝大會上演出《姐妹從軍》《在烽火中》《再上前線》《中華民族的母親》等節目,把她的慶生日游藝會開成鼓舞人心、激勵斗志的抗日救亡大會。她對學校抗日宣傳活動抓得很緊,學校的學生宣傳隊每個月總有兩三次下鄉去宣傳,常帶了一批觸目驚心的宣傳畫,采用家訪式方法,激起人們對日寇的痛恨,效果很好。并經常向民眾演出抗日救亡歌和短劇,很受民眾歡迎。
7月初,抗敵會宣傳隊用戲劇演出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沈毅就醞釀在縣前小學成立星期歌劇社,以開展抗戰宣傳。
對她來說沒有暑假,1938年更是這樣。假期依然有學生們在校學習。依然組織學生向社會進行抗日宣傳和募捐活動,持續開展。民眾夜校,她時常親自施教。7月10日開始,她安排學校舉行為期一個月的暑期訓練班,有一百多民眾參加培訓。培訓班除了補習日常學科外,特別注重戰時常識的講授,以適應戰時環境。她也常常前來授課。7月22日,舉行了全校歌詠大會。
這位60歲的沈毅,心裝家國大事、教育大事,為人師表,身先士卒,奔忙不息。
獲各界人士稱贊
1938年的七八月暑期,舟山的天氣也有點失常。8月初,在繁忙之中勞累的沈毅,忽覺肚痛,后又腹瀉不止。被送到臨時時疫醫院醫治,診斷為患阿米巴痢疾癥。臨時醫院是根據警局為防止夏季時疫,于6月15日開始經營的。沈毅在醫院治療幾天,腹瀉止住,看似基本好轉,沈毅就待不住了。是啊,她怎么能夠在醫院里躺得住呢?新學期的開學工作要準備,學校自編教學綱要與新教材的最后階段工作要加緊完成(1938年10月編成付審付印);7月31日抗衛會財務委員會擬定的工作任務要去落實;星期歌劇社組織工作要實施起來(與王烈鈞老師做過研究,離去前,把此工作交托給了王烈鈞老師。1938年10月這一遺愿變成了現實,星期歌劇社正式成立,并經常在火神殿、都神殿向社會公演《誰是仇敵》《屠夫》《黃帝魂》《血奠平倭碑》《偵探》等精短的抗日救亡短劇)……一向繁忙的她,一向生活簡樸的她,不習慣這樣的清閑和養尊處優的生活。于是,病情稍愈,她就堅決出院來到城北自己的家里。然而病根未除,積勞成疾,虛弱的身體經不起這么多天疾病的折磨,8月21日晚上7時30分溘然辭世。臨終之時,她竭力叮囑,一定要簡單節儉辦喪事。親友們在整理她留下的生活用品時發現,這個平時慷慨捐款的女豪,只有幾件平時常穿的舊衣服。原來她把自己工資收入,除了最低標準的生活費外,幾乎全部捐給了公益事業和補貼為學校的辦公用費。親友們不禁潸然淚下。
師生們聽說敬愛的校長離世,都淚流滿面。他們舉行各種哀悼活動。老師們趕寫沈毅傳略印發。學生們連夜制作沈毅大幅遺像,為了讓他們的敬愛之情,悲痛之心充分表達,想在遺像下寫上一段概括沈校長一生和他們心情的精煉話語。大家商量,想請當時舟山最有學識的人來撰寫,有同學提出請孫爾瓚來題寫這話語時,大家一致說好。孫爾瓚(1873—1948年),字釐卿,是舟山定海晚清舉人,民國社會名流。這位定海歷史上最后一位舉人;這位棄官不做,奉獻教育的書生;這位在日本侵占舟山時,殺頭也不出任漢奸會長的義士;這個輕易不為人題字的名流一聽學生們的請求,朗然應道:好!這個我寫!他提筆在手,稍作深思,便寫下了精短的《沈銳涓先生像贊》:
其身則獨,其學則群,有須眉之氣,亦何礙夫釵裙。興女學,辦救護,任財委……凡社會之事業,終不憚其辛勤。周甲子而壽終兮,人爭致夫誄文,悲門徒致拜遺掛兮,落珠淚之繽紛。
短短80個字,把沈毅一生業績與聲譽盡概,把學生的悲痛盡言。學生就把題寫著這段文字的遺像高掛在禮堂供大家守護哀悼。
舟山各界人士紛紛表示哀悼,有的登門致哀,有的誄文。《定海民報》報道說:
本縣婦女界先進沈校長毅,與本月初突患阿米巴痢疾癥,經送臨時時疫醫院醫治,始略告痊愈,乃遷至城北私寓療養,然終因年高體力不濟,卒于前晚七時卅分病歿,享年六十有一。——沈校長生平熱心教育事業,頗為各界所崇敬,而致力本縣婦運。尤著賢勞。本縣各界聞訊莫不深表哀悼。聞沈校長臨終,曾遺囑家屬力事節約,故一切喪事均行從簡。
1938年8月24日上午各界人士前來送別定海“女學之始祖”,舟山婦女運動引領者沈毅校長。雖然她終身未嫁,沒有兒孫,然而,她的學生就是她的兒孫,她愛護他們,而他們敬愛她。1938年8月25日《定海民報》以“素車白馬備極哀榮”為引題,以“各界前往祭哭者七百余人”為副題,報道了“沈校長毅昨安葬北郊”這一消息。
這七百多人的吊哀隊伍,這路旁肅立致敬的民眾……確稱得上備極哀榮。這種哀榮,是她一生投入到教育事業,盡力于婦女運動,專注于愛國實踐,身體力行,為民辦事,為抗日救亡奔走的必然效應。
此后每逢清明,都有很多人前去她的墓前憑吊致敬,很多人一直懷念著她。曾經是沈家花園第二代管門人的盧國忠,90多歲了還念叨著沈校長說,因家里窮,自己10歲了還無錢上學,沈毅校長說,到我的學校來念書吧,學費全免。盧國忠才得以入學。
永垂不朽的精神感召
沈毅雖然離去了,然而她卻還活著,她的精神感召著當時的人們。近日從1938年8月25日《定海民報》第二版讀到一篇署名“林介中”的來評文章《悼沈毅先生》。那篇刊發在頭條的充滿激情的評論,對沈毅的業績作了概述和評介,特別是對她的精神作了高度的評價,感覺至今還很有現實意義,特抄錄于下,以饗諸位:
獨身不嫁,以畢生精力從事教育事業之沈毅先生,昨以逝世聞矣!沉勇不撓之精神,堅毅果敢之勇氣,端的不輸男兒,遺音猶在,痛悼彌深,吾人謹代表各界同胞致無限之哀敬焉!
沈氏生于清季末葉,當時社會習俗之陳腐,風氣之蔽塞,無以復加;而沈氏獨能卓絕超群,遠歷異地,考察教育,學成之后,為桑梓服務,啟迪后人,不遺余力,歷數十年光陰與心血,培植數千余之子弟,造就數千余之人才。吾定得有今日之繁榮與進步者,沈氏之教育功業未可湮沒也。
……
沈氏自率之儉樸,捐款慈善之慷慨,待人接物之平和,及其彌留之際,且猶以簡禮薄葬為訓誡。死者不能復生,吾人為定海教育界失一人才惜,為定海后學者失一導師悲。而其昭示定海社會以良模范,則永垂不朽焉!
文中的“征齋先生”是沈毅的姐姐沈渭清的號。作者對她們兩姐妹的精神作了極高的評價:“此種偉人之思想,艱苦之精神”在當時舟山是無人可比的佼佼者,與歐美國家的杰出女性相比也不會遜色。并指出她們的意義就是為舟山樹立了優良的模范,有著昭示后人的作用,因此沈毅永垂不朽,沈毅的精神長流于世。
是的,我看到,1938年離去的沈毅,依然向著今天走著,依然昭示著今天。沈毅的博愛之心,敬業之行,創新之氣,和藹之風,實在是今天我們精神與行動的示范、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