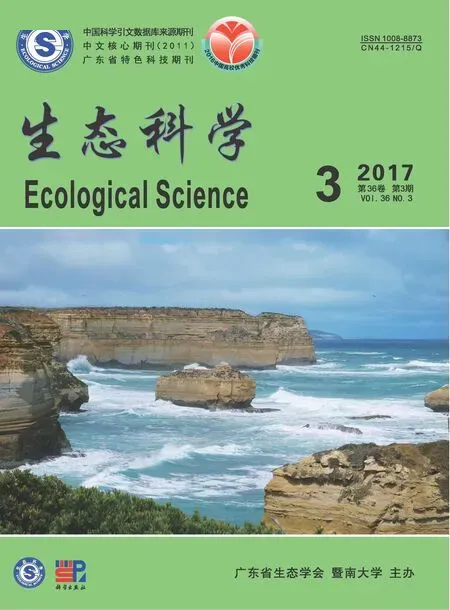海洋微藻響應重金屬復合脅迫的生理生態學機制
蔡卓平, 吳皓 劉偉杰 刁盼盼 駱育敏 段舜山
1. 廣東省生態學會, 廣州 510600 2. 暨南大學水生生物研究中心, 廣州 510632
海洋微藻響應重金屬復合脅迫的生理生態學機制
蔡卓平1,2,*, 吳皓1,2, 劉偉杰1,2, 刁盼盼1,2, 駱育敏1,2, 段舜山1,2,*
1. 廣東省生態學會, 廣州 510600 2. 暨南大學水生生物研究中心, 廣州 510632
重金屬污染物進入海洋環境會破壞海洋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海洋微藻構成了海洋食物鏈的基礎, 是海洋生態系統主要的初級生產者。重金屬復合脅迫對海洋微藻產生毒性效應, 會阻礙藻細胞分裂、破壞DNA結構、抑制光合作用、減少細胞色素合成、導致藻細胞畸變以及改變浮游植物種類組成等。海洋微藻在長期種系進化或個體發育過程中, 形成了一系列響應重金屬復合脅迫的特殊生理生態機制。它們可以利用由酶類和非酶類組成的抗逆保護系統, 減輕重金屬復合脅迫導致的生物毒害作用; 還可以通過調節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 MT)等相關蛋白基因表達以維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探究海洋微藻響應重金屬復合脅迫的生理生態學機制, 有利于為海洋重金屬污染的生物修復提供依據, 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海洋微藻; 重金屬; 復合脅迫; 生理生態學機制
1 前言
海洋環境中濃度較高且生物毒性顯著的重金屬元素包括鎘(Cd)、鉛(Pb)、銅(Cu)、鋅(Zn)、汞(Hg)、鉻(Cr)等, 它們通常具有環境殘留時間長、難以降解、并可沿著食物鏈傳遞富集、危害不可逆性等特點[1]。它們在海洋中累積到一定限度就會對海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產生嚴重的危害, 并可通過食物鏈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類健康[2]。重金屬對人體產生巨大的危害, 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汞污染而引起的“水俁病”以及由鎘污染引起的“神經骨痛”事件。其中“神經骨痛”病就是因人體攝入鎘后, 骨骼弱化甚至骨折, 疼痛難忍而得名[3-4]。重金屬 Pb能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損壞, 也能引起腎臟、肝臟和大腦功能的衰竭; Cr通過食物鏈積累而影響人體生理功能,甚至導致一系列皮膚問題或肺癌。重金屬Cd也被認為是 IA級致癌物, 對人類產生“三致性”危害(致癌、致畸、致突變)[5]。重金屬的污染往往是復合存在, 單一重金屬污染的狀況比較少見[6]。作為海洋生態系統主要的初級生產者, 海洋微藻響應重金屬復合污染脅迫的生理生態特征對重金屬的累積和遷移都起到關鍵的作用。研究表明海洋微藻的酶類和非酶類物質可以一定程度上調節重金屬復合脅迫的毒害效應。金屬硫蛋白是一種廣泛存在于動物、植物以及微生物體內的低分子量、富含半胱氨酸的蛋白質, 可對非必需重金屬(如鎘和鉛)進行脫毒[7]。認識海洋微藻對重金屬復合脅迫的解毒機制, 有利于豐富海洋微藻的抗逆分子生態學理論, 同時也有利于海洋重金屬污染的生物修復研究工作。
2 海洋環境的重金屬復合污染
各種重金屬污染物從排放源排出進入環境水體后, 難以被水體自身凈化, 不斷發生沉降作用而進入沉積物中, 使得海洋沉積物成為重金屬的主要蓄集庫。水—沉積物界面是水相和沉積物相之間的轉換區, 也是水生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沉積物中的各種重金屬元素在一定條件下可重新釋放并進入上覆水, 對海洋環境造成二次污染。海洋沉積物中的重金屬含量也能間接地反映出該區域的環境質量現狀[8]。通過對南黃海海域表層沉積物中的重金屬含量進行測定, 分析重金屬元素的分布特征, 采用地累積指數法和生態風險指數法評價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污染水平及其對環境的潛在生態危害程度,發現 Cu、Pb、Cd、Zn、Hg、As 的平均含量分別為17.1×10-6、19.6×10-6、0.092×10-6、77.3×10-6、0.021×10-6、6.97×10-6,空間分布特征整體表現為重金屬高值區主要分布在南黃海中部及偏東北部區域[9]。測定湛江港表層沉積物和海洋生物中Hg、Cu、Zn、Pb、Cd 等5種重金屬元素的含量, 分析評價沉積物和海洋生物中重金屬的含量分布及富集特征,結果表明, 除 Cd 外, 其他重金屬元素在沉積物中的含量均高于其在海洋生物體中的含量; 湛江港海域 Cu、Zn、Cd在生物體內積累較嚴重[10]。分析2005—2015 年其中 4 年東碇臨時海洋傾倒區及鄰近海域表層沉積物中Cu、Pb、Zn、Cd、Hg、As 等6種重金屬的含量及時空分布特征, 并采用潛在生態風險指數對重金屬污染現狀及潛在生態風險進行評價,結果表明Cd、Cu 的空間分布不均勻, 其余4 種重金屬指標空間分布差異不大, 在表層沉積物中, As、Pb、Zn 富集程度相對較高, 而Cu、Hg、Cd 較低, 其中 As、Pb 和 Hg 為主要潛在生態風險因子[11]。
3 海洋微藻對重金屬的生物吸附降解
海洋微藻吸附金屬的作用方式根據是否需要能量可分為被動作用方式和主動作用方式。前者主要是指通過物理、化學作用來吸附金屬的方式, 即金屬離子通過絡合、螯合、離子交換、物理吸附、氧化還原及微沉淀等作用結合至藻細胞表面, 其作用特點是吸附速度快、時間短、可逆、不依賴于細胞的能量代謝; 后者則是有代謝活性的細胞完成金屬轉移或細胞與金屬之間的反應, 即金屬離子主要是依賴擴散作用進行胞內運輸, 此過程常伴隨有能量的消耗, 其特點是吸附速度慢, 作用持續時間長,一般是不可逆過程, 并可能被能量代謝抑制劑所抑制。許多學者認為微藻吸附金屬的作用主要是前一種方式, 即被動作用方式。藻類對于重金屬離子的吸附性能主要由其細胞壁的結構和組成決定。海洋微藻的細胞壁主要由多聚糖、蛋白質和脂類組成,帶有一定的負電荷, 且具有較大的表面積和粘性。這些組分含有大量可以同金屬離子結合的基團, 有些基團可以靠靜電引力吸附金屬離子, 有的帶有孤對電子, 可以和金屬離子形成配位鍵而絡合吸附金屬, 有的基團表面吸附的離子可以與金屬離子發生離子交換作用。細胞膜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半透過性膜, 這些特點也決定了海洋微藻可以富集許多離子[12]。
一般來說, 微藻吸附重金屬過程主要涉及到以下幾種機理。第一種是表面絡合機理: 微藻置于金屬溶液中時, 首先與金屬離子接觸的是細胞壁, 因此細胞壁的化學組成和結構決定著金屬離子與它的相互作用特性。微藻細胞壁官能團所含的N、O、P、S 等原子可以提供孤對電子與金屬離子配位, 通過絡合作用吸附金屬離子, 絡合的方式可以是離子鍵或共價鍵。第二種是離子交換機理: 金屬離子除了能與藻細胞壁上的負電性官能團絡合而被吸附外,還能以離子交換的形式被吸附。此指的離子交換是藻細胞物質結合的金屬離子被另一些結合能力更強的金屬離子替代的過程。第三種是氧化還原機理:變價金屬離子在具有還原能力的生物體上吸附, 有可能發生氧化還原反應。一般來說, 氧化還原反應需要有代謝活性的細胞參與, 但也有研究報道, 非活細胞也能吸附金屬離子并將其還原為元素態。第四種是無機微沉淀機理: 無機微沉淀是易水解金屬常見的吸附機理之一。易水解而形成聚合水解產物的金屬離子在細胞表面易形成無機沉淀物, 它們以磷鹽、硫酸鹽、碳酸鹽或氫氧化物等形式通過晶核作用在細胞壁上或細胞內沉淀下來[13]。
4 海洋微藻應對重金屬毒害的保護物質
海洋微藻在長期種系進化或個體發育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耐受環境重金屬復合脅迫的特殊生理響應體系。海洋微藻體內存在著一個由酶類和非酶類組成的抗逆保護系統, 以防御環境脅迫帶來的傷害。主要酶類物質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過氧化氫酶、過氧化物酶、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等; 非酶類物質包括還原型谷胱甘肽、還原型抗壞血酸等。海洋微藻受到重金屬復合脅迫時, 體內會產生過多的活性氧物質, 使得活性氧的產生與清除處于一種非平衡狀態, 此時海洋微藻體內的抗氧化系統就可能增強,以清除多余的活性氧, 從而減輕由活性氧積累產生的氧化傷害[14]。在重金屬復合脅迫下, 海洋微藻還可能通過調節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MT)等相關蛋白基因表達以維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15]。
金屬硫蛋白是一種富含半胱氨酸、熱穩定性、可誘導型非酶低分子量金屬結合蛋白。研究發現大多數生物體內的金屬硫蛋白分子結構是由兩個大小相近的結構域構成啞鈴型, 兩個結構域通過賴氨酸殘基相連。金屬硫蛋白鉸鏈區的存在使得兩個結構域具有較大的柔性和可變性, 為調節生物體內重金屬離子代謝提供了結構基礎。金屬硫蛋白在必需金屬元素的調節和非必需金屬元素的解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SH能強烈螯合有毒的游離金屬離子, 減弱重金屬離子毒性, 并可將之排出體外, 從而實現解毒功能[16]。近年, 金屬硫蛋白作為監測水環境重金屬污染的一個重要標志物, 已經得到廣泛關注。隨著分子生物學等技術手段在海洋環境領域的應用, 不同生物的金屬硫蛋白基因序列被相繼克隆, 這為從基因表達水平上反映海洋環境重金屬的污染狀況提供了可靠技術手段[7].
5 展望
在自然環境中, 重金屬之間以及它們與其他污染物之間會聯合作用而構成復合污染, 因此重金屬污染常呈現復合性和多樣性[17]。重金屬之間的相互作用通常分為拮抗、加和或協同作用, 當多種重金屬共同暴露于生物體時, 其作用效應與單一重金屬暴露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開展重金屬復合污染研究更能客觀體現環境中重金屬污染物與生物有機體之間的相互作用規律和機理[18]。此外, 不同的海洋藻類之間對重金屬脅迫也存在不同的生長響應特征, 而重金屬對藻類生長的脅迫作用還會受到光照、溫度、營養鹽、pH等環境因子的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一般情況下, 重金屬的毒性與溫度高低成正相關; 水中的氧化還原電位與 pH是影響水中重金屬遷移轉化的兩個重要理化因素, 而重金屬在水中及海洋微藻內的遷移轉化速率, 也一定程度決定了重金屬的生物毒性[19]。此外,由于金屬硫蛋白含大量巰基, 在空氣中極不穩定, 在自然狀態下較難分離純化[20], 特別是在海洋微藻上的研究遠遠不足,今后有待進一步加強相關方面的研究工作。
[1] LI R Y, LI R L, CHAI M, et al.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in Futian mangrove forest sediment in Shenzhen Bay, South China[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2015, 101(1): 448–456.
[2] WOJTKOWSKA M, BOGACKI J, WITESKA A.Assessment of the hazard posed by metal forms in water and sediment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15(551/552): 387–392.
[3] 徐艷東, 魏瀟, 楊建敏, 等. 山東近岸海域表層沉積物 7種重金屬污染特性和生態風險評估研究[J]. 海洋與湖沼,2015, 46(3): 651–658.
[4] SJAHRUL M. Phytoremediation of Cd2+by marine phytoplanktons, Tetracelmis chuii and Chaetoceros calcitera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emistry, 2012, 4(1):69–74.
[5] 冉小飛, 劉瑞, 白芳, 等. 微囊藻生長及光合系統Ⅱ對重金屬鎘的響應[J]. 水生生物學報, 2015, 39(3): 627–632.
[6] LI Y H, LIU H, ZHOU H L, et al.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tential health risk of heavy metals in Mactra veneriformis from Bohai Bay, China[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5, 97(1/2): 528–534.
[7] 安立會, 鄭丙輝, 付青, 等. 以梭魚金屬硫蛋白基因表達監測海洋重金屬污染[J].中國環境科學, 2011, 31(8):1383–1389.
[8] 陳勇, 溫澤民, 尹增強, 等. 遼寧大長山海洋牧場擬建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的評價[J]. 大連海洋大學學報, 2015, 30(1): 89–95.
[9] 佘運勇, 王劍, 王艷華, 等. 南黃海海洋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的分布特征及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海洋環境科學,2011, 30(5): 631–635.
[10] 孫妮, 黃蔚霞, 于紅兵. 湛江港海區沉積物和海洋生物中重金屬的富集特征分析與評價[J]. 海洋環境科學,2015, 34(5): 669–672.
[11] 黃央央, 李少偉, 藍虹, 等. 東碇臨時海洋傾倒區及鄰近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及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漁業研究, 2017, 39(1): 63–71.
[12] 蔡卓平, 段舜山. 微藻對污水中重金屬的生物吸附(英文) [J]. 生態科學, 2008, 27(6): 499–505.
[13] OMAR H H. Adsorption of zinc ions by Scenedesmus oblipuus and S. quadricauda and its effect on growth and metabolism[J]. Biologia Plantarum, 2002, 45(2): 261–266.
[14] MANIMARAN K, KARTHIKEYAN P, ASHOKKUMAR S, et al. Effect of copper on growth and enzyme activities of marine diatom, Odontella mobiliensis[J].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2012, 88(1):30–37.
[15] LIU Y M, WU H H, YU Z T, ET AL.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of two metallothionein genes (OcMT1 and OcMT2) and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Oxya chinensis(Orthoptera: Acridoidea) exposed to three trace metals.Chemosphere, 2015, 139: 310–317.
[16] LE T T, ZIMMERMANN S, SURES B. How does the metallothionein induction in bivalves meet the criteria for biomarkers of metal exposure?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6, 212: 257–268
[17] KIM B S, SALAROLI A B, FERREIRA P A,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nrichment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Baixada Santista, Southeastern Brazil[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6, 103(1/2): 333–338.
[18] GUAN Q Y, WANG L, PAN B T, et 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controls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the riverbed of the Ningxia-Inner Mongolian reaches,Yellow River, China[J]. Chemosphere, 2016, 144: 29–42.
[19] BRUNO J F, CARR L A, O'CONNOR M I. Exploring the role of temperature in the ocean through metabolic scaling[J]. Ecology, 2015, 96(12): 3126–3140.
[20] OSOBOVA M, URBAN V, JEDELSKY P L, et al. Three metallothionein isoforms and sequestration of intracellular silver in the hyperaccumulator Amanita strobiliformis[J].New Phytologist, 2011, 190(4): 916–926..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marine microalgae responding to heavy metal complex stress
CAI Zhuoping1,2, WU Hao1,2, LIU Weijie1,2, DIAO Panpan1,2, LUO Yumin1,2, DUAN Shunshan1,2,*
1. Ecological Socie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65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Hydrobiolog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heavy metals may ente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hence destroy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arine ecosystem.Marine microalgae are the primary producers of marine ecosystem and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food chain in sea. The heavy metals are harmful to marine microalgae, which may hinder the algal cell division, destroy the DNA structure, inhibit the photosynthesis, reduce the cytochrome synthesis, cause cell distortion and even change phytoplankton species composition.During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marine microalgae, a series of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mechanisms in response to heavy metal complex stress have been formed. They can start the protective system composed of enzymes and non enzymes to alleviate the toxic effect of heavy metals; they may als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etallothionein and other related protein gen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normal physiological function. Exploring the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marine microalgae in response to heavy metal complex stress is beneficial to the bioremediation of marine heavy metal pollution, which i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arine microalgae; heavy metal; complex stress;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mechanism
10.14108/j.cnki.1008-8873.2017.03.031
X173
A
1008-8873(2017)03-216-04
蔡卓平, 吳皓, 劉偉杰, 等. 海洋微藻響應重金屬復合脅迫的生理生態學機制[J]. 生態科學, 2017, 36(3): 216-219.
CAI Zhuoping, WU Hao, LIU Weijie, et al.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marine microalgae responding to heavy metal complex stress[J]. Ecological Science, 2017, 36(3): 216-219.
2016-03-08;
2017-01-12
廣東省省級科技計劃項目(2015A070709013, 2016A070708011); 水體富營養化與赤潮防治廣東普通高校重點實驗室(暨南大學)(KLGHEI KLB07007); 廣州市科技計劃項目(201707010481, 201609010091)
蔡卓平(1980—), 男, 博士, 主要從事生態學研究工作, E-mail: zpcai@scau.edu.cn
*通信作者:段舜山, 男, 博士, 教授, E-mail: tssduan@jnu.edu.cn